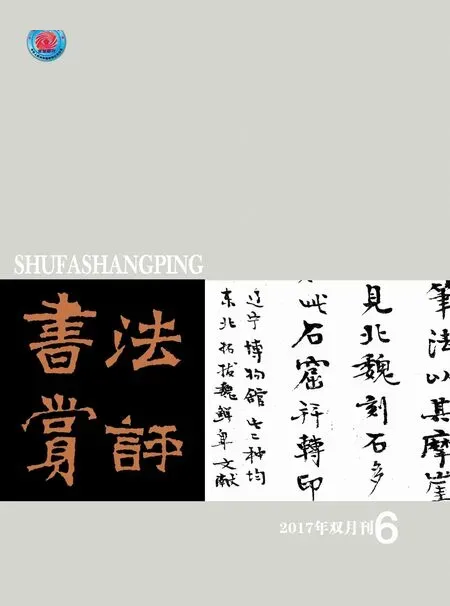齊陶文初論
■莊浩田
齊國陶文,相傳多出土于山東臨淄市的齊臨淄古城,并在臨淄古城以西的歷城和以東的掖縣等地也有發現。①解放后的出土發現證明,確實是以臨淄古城附近最為集中,但實際的出土地點并不僅限于一處,傳播范圍大體與齊邊境吻合,北面與燕國的陶文,南面的邾國、滕的陶文在傳播范圍上都有重疊。
1.齊陶文研究資料
對于齊國陶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陶文字的隸定與考釋、文字形體,陶文分期以及對齊地地名、制陶手工業、度量衡等方面。在這些領域,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以后進一步研究齊國陶文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陶文文字的考釋
在這一方面,學者們做了很多的工作,如唐蘭 《陳常陶釜考》,朱德熙 《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 “者”字》,裘錫圭 《戰國文字中的 “市”》,吳振武 《戰國 “廩”字考察》,馬良民、言家信 《山東鄒平縣苑城村出土陶文考釋》等。
(2)齊國陶文的比較與分期研究
孫敬明在 《齊陶文比較研究》②中,運用考古斷代和標型學的研究手段,對齊陶文進行縱、橫向以及青銅銘文的比較,來探討齊國文化的特點以及周邊地區的交流。在 《齊陶文比較研究 (續)》中指出,齊國陶器上的印文種類多、數量豐富,形式繁多而且內容更豐富,官私并存。齊陶文字具備法律詔令式的性質,而且對秦統一六國后統一度量衡在器皿上鑄勒詔令有著很大的影響等等。
(3)利用齊國陶文對國別及地名的考釋
王恩田 《齊國地名陶文考》③一文,從陶文中的陶鄉、左南郭鄉、內郭、華門等八個部分進行研究,對齊國地名進行了考釋。
(4)通過齊國陶文對齊國度量衡的研究
王恩田在 《“右里”二量真偽辨》④中,利用滕國故城文公臺附近出土的一件齊國時代的殘片陶文,即 “陳口立事歲口釜”七字作為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 “右里”二量并非是偽作的參考因素之一。
(5)通過齊國陶文對齊國手工業經濟的研究
陳家寧《從齊國文獻看戰國時齊國的社會經濟——戰國齊陶文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⑤一文中,將齊陶文與出土文獻相互佐證,對齊國的生產者分工、生產者居住地劃分制度、齊國官制量器制度及換算關系等各方面進行了考證,科學地分析了戰國時期齊國的社會經濟。
2.齊國陶文的分類
根據內容形式,齊國陶文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類:官方營制陶業、民營制陶業和為數不多的 “市”字類。⑥
(1)官方營制陶業
齊國官方營制陶業產品以量器為主要,飲食器皿較少。而作為樂器的陶塤則極為罕見。官方營制陶業產品制作工藝精湛,銘文規范典雅。量器陶文格式分為繁式和簡式兩種。繁式內容包括地名 (或身份)+人名+立事歲+左里故+亳+量名等六項,個別的還在量名后加 “銘”字。銘文最多者達十四字,量名后另有四字:“”為工師名,最后二字疑為 “所為”,似屬工勒其名的性質。可以省去其中的一項或某幾項,最簡的格式只有人名。
(2)民營制陶業
齊國陶文中占絕大多數的是民營制陶業的產品,其中以飲食器為大宗,飲食器中最為常見的是豆、、。齊國瓦上不使用陶文,是齊陶文與燕、秦陶文的顯著區別之一。齊國民營制陶業陶文的基本格式是地名+人名。少數陶文的人名后面再加器物名。地名中常見的是 “XX里”有時在 “里”的前面還有一個常見字,以往釋 “遷”“鄙” “廛” 等。
(3)為數不多的 “市”字類
裘錫圭先生辨認出了齊國文字中從止得聲的 “市”字,這對于陶文的研究是一個巨大的貢獻。這一類陶文沒有特定的格式,所以我們將其稱為 “市”字類。
3 .齊國陶文與別國陶文之比較
(1)文在器類
齊國陶文的載體種類,主要是泥質灰陶,以及小量的夾砂紅陶,且都為實用性陶器,約有日用、建筑和量器三種,見者多為豆、罐、鼎、盆、盂、杯、壺和板瓦、井圈,以及區、釜等。秦國的陶文所在器物主要是陶俑、陶馬、墓志和磚瓦,其他日用器主要是盆、罐、缶、壺等,在載體類別上明顯少于前列。燕國的陶文主要存在于罐、盆和豆等,趙國形式基本同于燕國,邾國的則以豆、罐、盆、翁、器座和磚瓦者多見。
由此可見,齊國的陶文種類之多,且講求實用,與秦國偏重于隨葬器,崇尚冥冥世界的做法,大異其趣。陶文中量器的比重最大,是齊國的應用陶器陶文統一國內量制的見證,在這一點上,趙、燕等國則大為遜色。
在各類陶器中,以陶豆出現帶有文字的頻率最高,這也是齊與邾國共同的特點。春秋晚齊貴族墓葬⑦中和戰國時期之甲士墓中,⑧已出現陶俑、陶馬,按其時代明顯比秦國要早,所以說陶俑和陶馬上戳印或者刻劃文字則當由秦國開始,而量器上鈐印文字,以標明其具備法定性質,當是由齊國開風氣之先河。秦國統一度量衡于全國量器上鑄勒具有法律性質的銘文,均是借鑒的齊國。
(2)文印形式
齊國的陶文主要是用戳印按壓在陶器上,并且迄今為止發現的許多璽印恰巧和陶文印文析符相合,印有銅質也有陶質者。刻劃的陶文所見較少,但覯者大都體勢寬博、狂放恣肆。印文的形式花樣新奇,不下方 (長方、正方),圓 (圓、橢圓)、凹、凸、曲尺和三角形八種。一般官營制陶器陶文多見長方而大,也有作正方形者。民營制陶器陶文則形式多樣。字數多著逾十,少者僅一。行款以縱橫左右間行者為多,橫豎交錯跳躍而行者偶見。

而秦國陶文同樣也是以戳印者為主,但其刻劃的為數亦不少,印面主要為方形,以四、二、一字者最為常見。燕國的陶文見者多屬于戳印,極少刻劃,其印面為長條形,獨具風格;邾國的陶文戳印多作方形,字數亦少。
比較而言,齊國的陶器文字戳印形式和文字較他國的多而豐富,并且戳印工穩,每器一印,不再刻劃,說明其有較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戒律。在東周時期,最早而又最普遍使用璽印以事制陶者,自以齊為首當其沖。同時,齊國繁富多樣的印面形式,即對當時各國的文字形式予以影響,也為后世璽印所宗法。
(3)文字內容
齊國陶文的內容,可分為兩大類,依其屬性,別為官、私;視其應用,一則明示詔令,再則 “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其官營制陶文內容形式大致可以分為五種形式:
王卒某鄙某邑里人某 例如:王卒左鄙城陽邑平丘里人曰得
王卒某(軌)某邑某里某 例如:王卒左(軌)昌陽邑營里口
某立事歲某里(軌)毫某 例如:王孫陳棱立事歲左里毫區
某(省、鄙)某邑某里(軌)毫某 例如:昌齊 (鄙)陳固南左里(軌) 毫區
王(軌)某里某 例如:王(軌) 營里得

私營陶文主要者可分九種形式:
某鄙某邑某里某 例如:鄙陽邑南里口
某鄙某里某 例如:鄙大陶里鄭
某邑某里某 例如:陽邑南里口
某邑某里人某 例如:陽邑南里人鄭
某邑某里陶者某 例如:陽南陶者心
某邑某里 例如:陽邑楊里
某里某 例如:關里口
某鄙 例如:曼丘鄙
某例如:得

秦國陶文多記里名人名和市亭名,均屬物勒工名的性質;燕國有的陶文內容與齊之官營者頗相似,其亦實行齊國的 “” (軌)制,趙國陶文簡約只記人名,但其兵器銘文見有 “立事”辭例。齊國陶文其應用于量器,旨在標明是由國家統一制造,合法行用的,并且還記上監制者的名字,有的還有紀年。只不過這種 “立事”記年的形式,于其當時是很清楚的,然至今日卻頗費考索。文稱 “立事”是齊國東周金文、陶文的突出特點,其它六國唯趙武靈王實行改革,因受齊之影響,而于兵器上刻記某王立事以紀年,頗具新意,見者有趙武靈王和惠文王兩代。燕國陶文反映出其實行與齊相當的 “”制,其明顯是本源于齊文化的。齊量陶文和金文,均具詔令性質,后為秦量所宗法。齊陶文之左、右,亦對秦左、右司空予以影響。齊國陶文內容之豐富,其多補葺歷史文獻記載之不足,創證于齊史,影響于他國,這亦是其為六國所不及之處。
4.齊陶文與齊國其他形式文字之比較
關于古文字,依其載體的質料和用途,可分為甲骨、金文、陶、石、璽、化、竹簡、帛書等八種。齊地雖然發現時代最早的史前陶文和數量最多的東周陶文,其余的文字資料,除璽印一種外,或數量較少,或尚未發現。迄今所知,在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壽光古城紀國銅器窯藏,濟陽劉臺子西周墓地,以及安丘郎君莊西周遺址等處,所發現的經過修整,鉆或鑿或灼的卜骨,有的保存比較完整,然迄未發現上面有帶文字者。石刻文字亦甚罕見,據載在鄒縣峰山洞中有一處,上刻二十字,據王獻唐先生等認為,這些石刻文字的時代為戰國或更早。從發現的資料拓本看,似為春秋時期。再即臨淄齊故城內出土的石磬上的文字,其時代不會晚到漢代。臨沂銀雀山出土了震驚世界的漢簡,但是漢代以前簡冊于齊故地則未發現,帛書資料亦未得覯。因為本文第一節已從縱橫的關系,與相關資料做過比較,故此節僅與齊地的其他文字作一比勘從中發現陶文在齊文字中的特點。
(1)較之鐘鼎
齊國的金文資料,目前發現的數量仍為較少,這與之泱泱大國的氣勢不相適應,其他秦、燕、晉與楚以及一些小的諸侯國的金文資料,都比齊國的發現得多,其中原因,令人頗費斟酌。
據陳簠齋先生于光緒庚辰六年,自作聯語稱 “陶文齊魯四千種,印篆周秦一萬方”。當時,還有其他人變輾轉收集齊、邾陶文,約計舊所著錄和今所散存于青島博物館、諸城博物館、青州博物館、齊國故城博物館、山東省博物館和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以及國內外其他公私所藏的齊國陶文,其數量可謂最多。這比本地出土的其他文字資料,不知要多多少倍,較之秦、燕、韓、趙亦是如此。
齊國陶文的形體與金文璽印均相一致,大都是豐欣修美,在這東周文字分域中,是典型東方齊系文字的風采。因此,無論它們于何時何地出土,只要據其形體和辭例,即可斷之屬齊。

(2)比之兵器
在列國兵器銘刻中,齊國者以其簡要而為明顯特點。而秦、燕、三晉者與齊相比較,則顯得他們屬為繁文縛式,制度復雜。然而再比之陶文,則情景者又相近,以齊官營陶文為例,其比秦和三晉的都要字數多而內容豐富,比之于燕,也大致如此。
兵器銘文均是鑄出,這亦是齊之特點,并且銘范上的文字不少是用璽印鈴制的,這只要細察原器和拓本都不難看出。陶文和兵器銘文的形體一致,如高、陳、陵、平等字均從 “土”作,如城從 “墉”作,共同構成明顯的地域和時代特色。
甚至有的陶文與兵器銘文的人名相同,并且都是 “立事”者,如 “陳得立事歲”戈,和 “平陵陳得立事歲”陶器等。雖然制陶與冶鑄兵器工藝相去甚遠,但由精治陶坯和制造兵器銘范,則兩者工藝卻是頗相近似的,兩種工藝之間,必有互為影響之關系。

(3)斟兌貨幣
齊國的貨幣無論其種類、型式,還是銘文內容,較之秦、燕、楚和三晉,都顯得數量少而文字簡要,有其明顯的特點,表現出齊于貨幣鑄造和管理方面,有著比其他各國更強為有力的管理制度和統一措施。其面文字數多者有六,少者僅三字,這比一般的陶文字數都少。其中齊刀幣面文 “齊”字,與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有頗多相似處,與同時代金文、陶文之形體則相去甚遠。這說明齊幣面文相沿保留了古代形體,這種現象,在其它同時期的文字中較為少見。

錢文字形體無甚變化,陶文之形體則有數種,但即便屬同時同地的文字,其不論是存在何種載體上,它們之間的關系自應是密切的,形體的變化和字意的釋解應該互為關聯的。故在考釋時就得全面和系統地占有資料,如是抓住一體,而不解其余,望文生義,科學性何存焉。
5.齊陶文的分期斷代
王國維在 《桐鄉徐氏印譜序》中提到過陶文的時代。⑨孫敬明 《齊國陶文分期芻議》則根據新的發現和以往的成果對齊國陶文進行了初步的斷代分期,意義比較深遠。
現在,對齊國陶文的年代,學術界基本達成共識,即上自春秋晚期,下迄田齊亡國。然而,齊國陶文的分期卻還存在問題。
過去有學者從陶文內容主要是立事者的名字入手,與文獻記載人名相比附,從文獻記載人名的時代考證出陶文立事者的時代,從而確定陶文的分期。但是,一是文獻記載的人名可與陶文人名相比者甚少;二是即使有少數可以比附,但常常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此不能進行下去。
也有學者力圖從器物類型、層位學入手來進行分期,但齊國陶文完整器物發現不多,即使有完整器,也難以作出比較準確的排比。出土材料大多是調查采集品,有明確層位的陶文資料又多未發表。這樣,即使與其他周圍地區能作對比,也不能準確斷代。因此,陶文分期問題遠沒有解決。⑩
6.齊國陶文的書法藝術價值
(1)從刻劃角度來看
齊國陶文整體風貌分為陶坯刻字、成陶刻字。陶坯刻字,因不同的鐫刻者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征。一部分齊陶文,刀痕清晰,字形多見傳統大篆筆意,而又與書寫之美有所區別;另一部分齊陶文,草率急就,用刀深淺易變,線條肥瘠曲直輝映,出于自然,而入妙境。成陶刻字,因為所用載體已經成型,質地清脆,鐫刻湊刀時,往往一蹴而就,線質爽利,字勢輕健,予人以勁險之感。
(2)從打制印文角度來看
陶坯印文,印模宛然如初,其字形之密、線條之肥腴,大概只有印陶文才能做到這一點。
(3)從風格角度上來看
陶坯及成陶器物,有著很多的因素會影響到作品風格,例如:陶器器形的不同導致的受力面積的不同以及湊刀位置的不同、陶坯刻字前的干燥程度、陶土的粗細程度、陶質的疏松或堅密、細微砂粒的意外干擾等等。但總體來說,齊陶文的文印形式都緊密承接著同一時代的金文、墨跡的字法原則和造型基礎,但因載體的不同,經過歷史的積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不同于齊金文、齊墨跡的書法藝術表現形式,它有著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藝術魅力。
經過前人和時代先賢的共同努力,陶文的著錄和研究均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為我們的繼續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伴隨著科技技術的不斷豐富,對于陶文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從而讓我們更能清晰地認識到之前的研究依然存在著不少問題,隨著對陶文的綜合研究我們不僅豐富了對陶文這一藝術形式的認識,而且也逐步地理清了陶文在古代的發展形勢。同時,陶文的出土以及對于陶文的研究對于今天的我們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古文字學,是從甲骨文的發現而開端的,而實際上,陶文的發現和鑒定比之甲骨文還要更早一些。通過對陶文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將會為我們帶來不同的古文字學觀,這對于我國的古文字發展史是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在考古學研究方面,齊陶文的出土、鄒平丁公陶文的出土以及古魯國西漢陶文的出土等等都進一步豐富了我國考古學資料寶庫,為我國的考古學研究史料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書法篆刻藝術發展史研究方面,陶文的藝術可考性也是獨具色彩的,陶文的文字形式、章法處理、刻畫痕跡等等引起國內外書家的借鑒和學習,同時,戰國齊的戳印陶文,更是豐富了篆刻藝術的形式來源,通過對齊國陶文印脫的借鑒與學習,眾多篆刻家、書法家均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啟發。從這三個方面而言,陶文的發現與研究給我們帶來了豐富的文字、藝術資料,使我們進一步打開了對古代文化發展感受的大門。它給我們帶來的豐富多彩的文字,使古代先民的生活畫面再現在我們視線中,使我們更能進一步地了解先民、感知先民。
注釋:
①顧廷龍 《季木藏陶序》
②孫敬明 《齊陶文比較研究》 《管子學刊》1994年3期,第54—58頁。
③王恩田 《齊國地名陶文考》 《考古與文物》1996年4期。
④王恩田 《“右里”二量真偽辨》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9年1期。
⑤陳家寧《從齊國文獻看戰國時齊國的社會經濟——戰國齊陶文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3期。
⑥王恩田 《陶文圖錄·自序》,齊魯書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287頁。
⑦中科院考古作業山東隊 《山東平度東岳石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與戰國墓》 《考古》1962年10期。
⑧袁仲一 《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⑨王國維 《桐鄉徐氏印譜序》 《觀堂集林》卷第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182—185頁。
⑩許淑珍 《齊國陶文的幾個問題》 《齊魯文博》,齊魯書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143—144頁。
[1]徐正考、佟艷澤 《漢代陶文著錄與研究述論》 [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7月第4期;
[2]任相宏 《新泰出土陶文十品》 [J]東方考古 (第9集);
[3]喬志敏、趙丙喚 《新鄭館藏東周陶文簡釋》 [J]中原文物,1998年第四期;
[4]陳家寧《從齊國文獻看戰國時齊國的社會經濟———戰國齊陶文與傳世文獻的比較研究》[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三期;
[5]曹定云 《山東鄒平丁公遺址 “龍山陶文”辨偽》 [J]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6]吳振武、于閏儀、劉爽 《吉林大學文物室藏古陶文》 [J]史學集刊,2004年10月第4期;
[7]鄭同修、楊愛國 《山東漢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 [N]考古學報,2003年第三期;
[8]李寶壘 《齊國陶文與田氏代齊研究》 [J]齊魯文化研究,第九輯;
[9]陳全方、尚志儒 《秦都雍城新出陶文研究》 [D];
[10]鄭莉 《史前陶文研究綜述》 [N]滄州師范專科學校學報,第24卷第一期,2008年3月;
[11]孫敬明 《考古新得齊陶三則跋》 [J]東方考古 (第8集);
[12]徐在國 《談齊陶文中的 “陳賀”》 [N]安徽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一期;
[13]許淑珍 《臨淄齊國故城新出土陶文》 [J]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4期;
[14]陳根遠、陳洪 《新出齊 “陳棱”釜陶文考》 [D];
[15]李零《齊、燕、朱移、滕陶文的分類與題銘格式——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介紹[J]管子學刊,1990年第一期;
[16]孫敬明 《齊陶文比較研究 (續)》 [J]管子學刊,1994年第4期;
[17]郝導華、郭俊峰、禚柏紅 《齊國陶文幾個問題的初步探討》 [J]齊魯文化研究總第六輯,2007年;
[18]陳全方 《周原出土陶文研究》 [D];
[19]高明 《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 [D];
[20]王恩田 《陶文圖錄》序 [M]齊魯書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1]叢文俊 《中國書法史·先秦·秦代卷》 [M]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