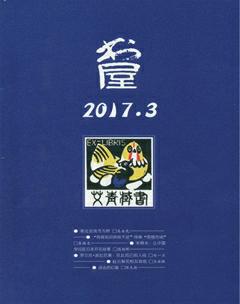更不如今還有
易彬
作為一位新詩人,羅念生先生的名聲不彰。其實,早在清華讀書期間,他就曾在《清華文藝》、《清華周刊》等處發表詩作。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后,其詩作可見于《北平晨報·詩與批評》、《大公報·文藝副刊》、《益世報·文學周刊》、《新詩》等知名報刊,其詩歌寫作生涯,大概持續到了1948年。詩作中有一首長達十二節二百六十余行的敘事詩《鐵牛——一名戰爭》,不過似乎極少為人所知。他亦有詩集出版,不過僅有薄薄的一冊《龍涎》(時代圖書公司,1936年),一百來頁,大抵也并不為人矚目。
羅念生也是一位新詩理論的建設者,他這方面的名聲顯然要大不少。《龍涎·自序》談道:“我們的‘舊詩在技術上全然沒有毛病,不論講‘節律(Rhythm)、‘音步的組合(Metre)、韻法,以及韻文學里的種種要則,都達到了最完善的境界;只可惜太狹隘了,很難再有新的發展”;“我不反對‘自由詩,但是單靠這一種體裁恐怕不能夠完全表現我們的情感,處置我們的題材。我認為新詩的弱點許就在文字與節律上,這值得費千鈞的心力。”這段話顯示了羅念生討論新詩理論的基本出發點。實際上,在三十年代中段的平津詩壇,新詩批評家們就新詩形式問題競相發表創見,爭執往還,一時之間非常熱鬧,羅念生算得上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參與者,相關文章在十篇之上。學界對于羅念生當年和朱光潛、梁宗岱、林庚等人所展開的討論已有較多梳理。實際上,羅念生不僅在理論上積極申揚,在寫作上也是多有實踐,《龍涎·自序》即指明了對于體裁和音組的冒險嘗試,包括“十四行體”(Sonnet)、“無韻體”(Blank verse)、“四音步雙行體”(Tetrametre couplet)、“五音步雙行體”(Pentametre couplet)、“斯彭瑟體”(Spenserian stanza)、“歌謠體”(Ballab metre)、“八行體”(Ottave rime)和抒情雜體。
當然,羅念生先生留給世人更為主要的形象,無疑還是古希臘文學的翻譯者與研究者。2004年,十卷本《羅念生全集》初次結集出版時,劉厚生先生在《序》中即有感慨:“這一套大書的編成出版會像是在中國文化大地上搬來了一座希臘群神聚居的奧林波斯山一樣。”誠如斯言,全集的主體部分涵括了羅念生翻譯的古希臘文學名著,如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悲劇詩人歐里庇得斯、戲劇詩人阿里斯托芬以及亞里士多德、荷馬等人的主要乃至完整的傳世作品,其譯文被認為是“最大限度地貼近了希臘精神中的‘高貴的簡樸與靜穆的偉大”。2016年,《羅念生全集》修訂重版——“希臘群神聚居的奧林波斯山”再次降臨中華大地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而隨著更多文獻的搜羅整理,羅念生的歷史形象也將得到更為宏闊的呈現。
相比于初版,新版全集在篇目上有較多增加,在體例上亦有一定的調整。前七卷為前述古希臘文學名著的翻譯(初版為前六卷),第八卷為《意大利簡史》、《哈代小說選》、《施篤謨小說選》(初版為第七卷);第九卷為研究論著卷(初版為第八卷),包括兩部關于古希臘羅馬文學的研究著作《論古希臘戲劇》、《論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散篇論文部分新增為多,也有個別的如《論新詩》,因為主題內容相異而移到第十卷。第十卷為散文、詩歌、書信、散篇論文的合集,包括曾結集出版的散文集《芙蓉城》與《希臘漫話》、詩集《龍涎》,“關于朱湘”則是從《二羅一柳憶朱湘》中析出的部分以及相關文字的合輯。其他的,書信共錄一百五十七通,通信人包括數位國際友人以及國內的曹葆華、胡喬木、錢光培、周健強等人。此次新增的有四十余封,其中也包括我在整理彭燕郊先生資料時所發現的兩封信。彭燕郊當年為湖南人民出版社籌劃“散文譯叢”,其中有羅念生先生編譯的《希臘羅馬散文選》,為漓江社籌劃“犀牛叢書”,也曾向羅先生約稿;而且,羅先生還曾為《朱湘譯詩集》寫序,此書列入彭先生籌劃、組稿的湘版大型外國詩歌翻譯叢書“詩苑譯林”,所以,從常理推斷,羅、彭二人的書信還有不少,還可待進一步的清理。實際上,有一個話題這里不便展開,那就是除了致周健強、錢光培等四、五位友人的信量大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只有一封,失收的書信應是不少。至于原本作為第十卷附錄的《羅念生生平》、《羅念生年表》以及家屬、學者回憶、評論羅念生的文字,則移出全集,單出一卷附冊,這在體例上也顯得更為合理。
下面,還是想結合第十卷散篇部分來繼續談談羅念生作為新詩人和新詩理論建設者方面的話題。所謂“散篇”(初版稱之為“拾遺”),即未曾結集過、散見于各類報刊的詩文,篇數由十篇增加到數十篇之多。其中就包括二十四首新詩和一批討論新詩理論問題的文章。全部新詩和詩論文章集合起來,夠得上單獨出一冊比較厚實的《羅念生新詩與詩論集》。傳記資料顯示,二十年代在清華讀書期間,羅念生就開始了研習古希臘文學,他在三十年代較多寫作新詩、并發表新詩理論文章的時候,已經有過留學希臘、并翻譯過不少古希臘文學名著的經歷了,因此,大體上可以說,羅念生的新詩寫作、新詩理論的建構與古希臘文學的翻譯、研究之間,具有某種同源同構的關系。進一步說,羅念生的新詩寫作及新詩理論建構可謂蘊涵了一種獨特的文化自覺意識:在理論層面,著力于術語的界定、辨析與厘清,“近來討論新詩的人漸漸多了,大家都覺得我們的問題依然是一個形式的問題。可是沒有一種共同的術語,我們的討論往往不能接頭”。《韻文學術語》(《新詩》,1937年第四期)共列出術語七十八條,包括詩、輕重、節奏、節律、音步等等。在寫作上,即是試圖通過來西方詩體的引入與嘗試,以拯救新詩形式(“文字與節律”)的流弊。
問題在于,當年身處“新詩底十字路口”的嘗試者們自認為“值得費千鈞的心力”的創舉——包括先前在提及詩集《龍涎》時所著意列舉的若干詩體,也包括前述新詩理論家們所標舉并為之實踐的諸多概念,對今日從事新詩寫作與批評的人而言,早已是歷史的絕響。江弱水教授感慨“奧登在任牛津大學教授期間,什么都不講,只講作詩法”;“大詩人講寫作心得,比如杜甫,比如瓦雷里和艾略特,總是落實在具體的技術層面上”。但今日的新詩批評“已經不講‘作詩法(versification)了”。他曾指出朱朱詩《寄北》,“十八行詩除了第八行稍稍破格外,都可以統一劃為五頓”,“這正是二十年代以來,孫大雨、卞之琳、吳興華等莎士比亞中文譯者用來移譯作為莎劇主體的五韻步‘素體詩(blank verse)的漢語形式。這接近說話調子的詩體,句子長短伸縮自如,節奏和韻律可隨時調控,有極為豐富的調式。”但《寄北》卻只是“這些年看到的唯一一例”,“表明幾代莎劇漢譯家悉心研究的成果未遭徹底拋棄”(《起于愉悅而終于睿智——對兩首小詩的激賞》,《新詩評論》,2007年第二輯)。羅念生的名字并沒有出現這里,但也無妨,重要的是類似的詩學問題重新在當下詩歌寫作與批評之中浮現出來。
換個角度說,這也可視為羅念生名聲不彰的一個表征。而諸多原因之中,文獻的長期散佚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羅念生先生的新詩理論文章此前從未匯集出版,詩集《龍涎》也早已絕版,《鐵牛——一名戰爭》這等敘事長詩,不僅日后文學史全然不提,它的名字甚至都極少為人所知。今日讀者,大概只能從長期致力于新詩資料搜集與整理的劉福春先生撰寫的《中國新詩編年史》、《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詩歌卷》一類新詩文獻輯錄書籍之中,獲知最簡單的發表信息。因此,盡管所占比例有限,盡管還有若干遺漏和些許編年錯誤,比如《鐵牛》發表于《北平晨報·詩與批評》第九號,1933年12月22日,而不是1923年;新版《羅念生全集》在中國新詩文獻的整理方面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羅念生作為新詩人和新詩理論建設者的形象終于有了比較清晰而完整的呈現:一個創作量并不大但“很勇敢的”、有著“冒險嘗試精神”(借用羅念生評林庚語)和特殊詩學抱負的詩人,一個執著于新詩形式建設的理論家。放眼新詩史,同為知名翻譯家,王道乾、葉汝璉、沈寶基等人早年也有過新詩寫作實踐,且已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參見張松建:《現代詩的再出發:中國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新版《羅念生全集》的出版,也可說為新詩人、新詩理論建設者羅念生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
當然,外國詩歌及其文體自然并非新詩發展的絕對參照系,但從一開始,外國詩歌即是新詩發生的源動力之一,而在新詩寫作日益失范的今日,重溫這些“表面似乎無關輕重,其實是新詩底命脈”(《大公報·文藝》編輯按語)的新詩經驗資源,還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羅念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