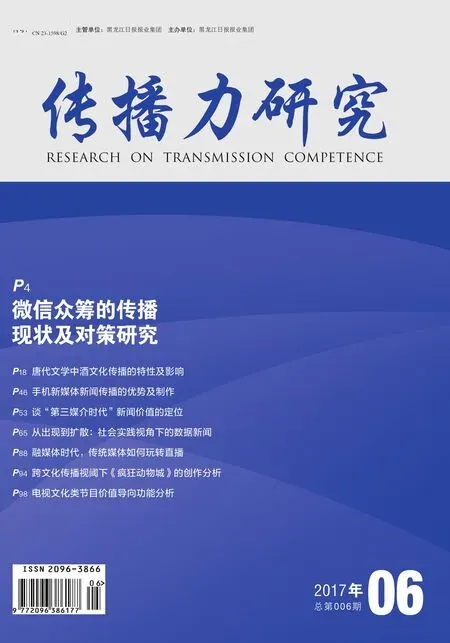“喪文化”浪潮中大學生的角色分析
文/尤凱港 嵇紅亮
最近,一家名為喪茶的奶茶店繼喜茶之后成為奶茶界新晉“網紅”,整個調性定位就是滿滿的“負能量”。與此同時,網絡社會又迎來了一批新鮮流行詞,其中“葛優躺”這一詞應當成為最為關鍵的一個網絡熱詞。“葛優躺”出自于1993年的一部情景喜劇《我愛我家》,該部情景喜劇的第17、18 集劇照中葛優扮演的一個“二混子”混吃混喝的狀態。[1]在“葛優癱”的帶領下,悲傷蛙、長腿兒的咸魚、馬男波杰克、鮑比希爾等善于散播毒雞湯的“喪文化”代表們正在受到95后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群體的追捧。
一、“喪文化”浪潮中大學生的角色分析
(一)大學生在“喪文化”浪潮萌芽期——澆灌者
正是這樣頹廢、絕望、悲觀、生無可戀的形象,和90后大學生群體倡導的積極、健康、向上的正能量主流精神顯得格格不入,而事實卻大相徑庭。當下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也日益凸顯,而當代大學生通過社交媒體可清楚地認知其嚴峻性。而“葛優躺”的出現,以大學生群體為代表的90后紛紛表示“自己每到周末就是這個樣子,這才是真的自己,生活在壓力之下好累,而且希望每天都是這樣子”,于是掀起了一輪強勁的社交媒體轉發和分享的潮流,“喪文化”浪潮在以大學生群體為代表的90后澆灌之下萌芽。
(二)大學生在“喪文化”浪潮漲潮期——推動者
“葛優躺”橫空出世之后,這些散亂的戲謔性產品也被整合在一起,在以大學生群體為代表的90后的社交媒體中肆無忌憚地轉發分享。其受眾群逐漸通過90后的社交媒體被放大至各年齡各職業人群,一次隨手轉發分享,一句負能量的文字配個表情包,仿佛就能緩解工作生活的壓力、把所有負面情緒都釋放掉。
促成這一系列現象的原因正是 “喪文化”浪潮的“澆灌者”演化成“推動者”,以大學生群體為代表的90后從眾心理和求異心理往往會主導其消費傾向,因此“喪文化”龐大的受眾群背后蘊含著巨大的商業價值。
(三)大學生在“喪文化”浪潮退潮期——退出者
以大學生群體為代表的90后的 “喪文化”并不是一味地無所事事、混吃等死,更多的其實是面對現實生活的殘酷競爭空有抱負卻懷才不遇,在這一個矛盾體中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慵懶的負面情緒。當大學生群體的理智戰勝了求異從眾心理,當看似新潮的“喪文化”衍生品變得大眾化,當同個年齡段的社交圈慢慢遺忘“葛優躺”,大學生在“喪文化”浪潮的退潮期會成為最先的退出者。
二、“喪文化”浪潮中大學生的角色反思
此次“喪文化”浪潮過后,大學生群體需進行反思,而高校、社交媒體以及政府和社會也應當正確、合理地發揮其作用,以促進大學生群體的茁壯成長。
(一)理性看待大學生群體“喪文化”
由于青春期的特殊性,大學生群體易產生叛逆、頹廢等色彩的“喪文化”等“青年亞文化”,是有必然和應然的生理基礎,因此,應當理性、客觀看待該文化的存在。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理應對各種文化采取包容的態度,當然是指“青年亞文化”中的積極部分,而對待一些消極、頹廢的文化需要去其糟粕。
(二)支持引導大學生群體樹立正確價值觀
高校應當進一步開展互聯網教育、文明上網教育和積極課程教育,定期開展心理輔導和心理治療,引進學校社會工作者、心理咨詢師,強化師資隊伍,尤其是能夠開展積極課程、積極課題的教師。
政府一方面應進一步整治互聯網市場,優化和完善互聯網輿論監督機制,開展和宣傳互聯網正能量故事和事跡,對于低俗、惡俗文化提出整改意見,積極引導青年正確上網,正確、科學選擇網絡言論和“網絡套餐”[2];另一方面應構建四位一體模式,即政府職能部門、用人單位、大學和大學畢業生本人四個方面組成一體,既要各負其責,又要協同配合,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決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以緩解大學生的結業壓力,從源頭上應對“喪文化”。
三、結語
對于當今時代中國的90后尤其是大學生群體來說,在互聯網時代已經被貼上了足夠多的標簽,其中很多標簽是被“污名化”的。大學生群體自身應理智應對各方壓力,化壓力為動力,施展新時代青年的抱負與理想;而社會各界不應對大學生持一味否定與批評態度,應當正面支持和引導大學生群體獲得文明健康文化的熏陶,用積極、健康的主流文化和民族精神去引導大學生去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
[1]周霖.“葛優躺”的社會心理學[J].南風窗,2016(18):90-91.
[2]蕭子揚.從“廢柴”到“葛優躺”:社會心理學視野下的網絡青年“喪文化”研究[J].青少年學刊,2017(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