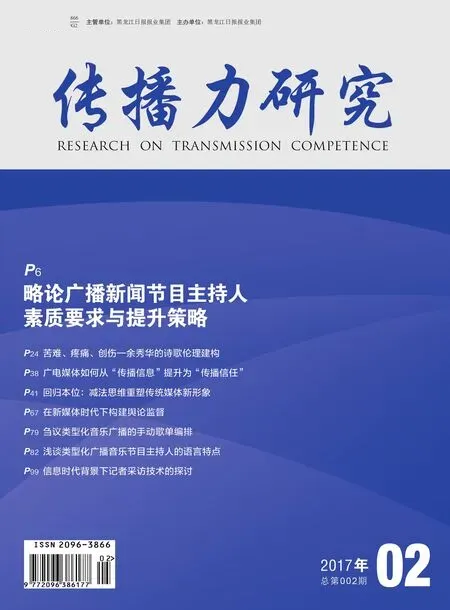苦難、疼痛、創傷—余秀華的詩歌倫理建構
文/吳海洋
余秀華詩歌自2014年9月于《詩刊》上發表之后,“腦癱詩人”“農民詩人”“草根詩人”的稱號,隨著官方刊物、大眾傳媒與學者、詩人的推波助瀾,余秀華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一躍成為近年來最為紅火的詩人,不僅獲得了各方的追捧,贏得了盛名;而且相繼出版了三本詩集;《月亮落在左手邊上》、《搖搖晃晃的人間》、《我們愛過又忘記》[1],可謂名利雙收。余秀華及其詩歌的走紅,有著藝術內部自身的審美因素,也有著與大眾文化心理的合拍以及當代社會文化的推動。余秀華或者其詩歌創作顯然已經成為一個文學事件,深刻地影響了當代文壇與當代大眾,其詩歌倫理又體現著當代文學與當代大眾文化的癥候。
一、余秀華詩歌的藝術審美性
余秀華詩歌創作量較大,現在僅以發表與結集出版的詩歌為例,進行藝術審美特性的分析。對余秀華詩歌進行分類,按地域、題材,主要是農村題材;按照主題可分為:日常生活類、愛情題材類、親情題材類、女性題材類,這些多是帶有敘事、抒情成分的;還有大量的比較空洞的說理詩、抒情詩。總的來說,前者的藝術價值較高,而后者則缺乏藝術審美性。這不難理解,這些詩歌還缺乏藝術的凝練與沉淀,自然,也與詩人自身有關。
(一)詩歌內容
1.田園鄉村中的牧歌提起余秀華詩歌,橫店這個她居住的村莊一直是她吟詠的對象,余秀華為讀者呈現了一個田園牧歌式的“桃花源”。草可以與人產生感應:“一顆草怔了很久/在若有若無的風里/扭動了一下”(《后山黃昏》),夫妻在油菜地的爭吵中的甜蜜(《給油菜地灌水》),可以看到水鳥、蘆葦、喜鵲,覺得“與天空這么近”(《站在屋頂上的女人》),如《五月 小麥》:
在春天唱歌,
每個春天我都會唱歌,看云朵從南來
風再輕一點,就是真正的春天了
一個人在田埂上,蒲公英懷抱著小小的火焰
在春天里奔跑,一直跑到村外
而我的歌聲他是聽不到的
我總想給他打電話,我有許多話沒說
一朵花開的時間太短,一個春天駐足的日子太少
他喊:我聽不清楚,聽不清楚
他聽不懂一個腦癱人口齒不清的表白
那么多人經過春天,那么多花在打開
他猜不出我在說什么
但是,每個春天我都會唱歌
歌聲在風里搖曳的樣子,憂傷又甜蜜
這里一切都被詩人主體審美化了,春天、唱歌、蒲公英、憂傷又甜蜜的愛情,哀而不淫,樂而不傷,甜蜜而略帶悲傷的鄉村生活,儼然適合在春天放聲歌唱。
2.日常生活題材
如《我養的狗,叫小巫》:
我跛出院子的時候,它跟著
我們走過菜園,走過田埂,向北,去外婆家
我跌倒在田溝里,它搖著尾巴
我伸手過去,它把我手上的血舔干凈
我一聲不吭地吃飯 他喝醉了酒,他說在北京有一個女人
比我好看。沒有活路的時候,他們就去跳舞
他喜歡跳舞的女人
喜歡看她們的屁股搖來搖去
他說,她們會叫床,聲音好聽。不像我一聲不吭
還總是蒙著臉
我一聲不吭地吃飯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塊丟給它
它搖著尾巴,快樂地叫著
喊“小巫,小巫”把一些肉塊丟給它
它搖著尾巴,快樂地叫著
他揪著我的頭發,把我往墻上磕的時候
小巫不停地搖著尾巴
對于一個不怕疼的人,他無能為力
我們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經死去多年
這里不僅有對家庭不幸生活中苦難地訴說,也有著對生活伴侶—小巫,親人外婆的深深的留戀與真摯的感激,而言說語氣又是非常平淡的,濃烈的情感藉以平淡的言說方式,更加深了情感的力量,真摯、單純而又樸素。
3.愛情詩
詩人也有對愛情的期盼。“我被天空裹住,越來越緊/而我依舊騰出心靠左邊的位置愛你/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我想要的愛情》 “我想念那個不曾愛我的人”《闊葉林》,中年對愛人的期盼“我們走了多少岔路/于這玩球的凄清里,才巧遇/我已準備好了炭火,酒,簡單的日子/與你想要的一兒半女”(《岔路鎮》)。
4.女性題材的詩歌
這些詩歌通常帶有自敘傳色彩 。“紅色的裙子在風里搖擺/紅色的疤痕在她的眉間,美與破壞都突兀”《平原上》,這種對美的破壞,不僅是對破壞的懲戒,也是對美的贊歌,其實是一種詩人自身境況的言說,雖然帶有藝術虛構的成分,如《我身體里也有一列火車》:
你沒有看見我被遮蔽的部分
春天的時候,我舉出花朵,火焰,懸崖上的樹冠
但是雨里依然有寂寞的呼聲,鈍器般捶打在向晚的云朵
總是來不及愛,就已經深陷。你的名字被我咬出血
卻沒有打開幽暗的封印
詩中有著對真摯愛情的堅守,對誘惑的拒絕,帶著對美麗愛情的渴望,其間隱含著女性主題的困惑與矛盾。
(二)藝術特色
1.對鄉村日常生活中瑣事的描述
如《莫愁街道》、《在棉花地里》、《一個男人在我的房間里呆過》、《一只水蜘蛛游過池塘》。《我愛你》:
巴巴地活著,每天打水,煮飯,按時吃藥
陽光好的時候就把自己放進去,像放一塊陳皮
茶葉輪換著喝:菊花,茉莉,玫瑰,檸檬
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帶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內心的雪
它們過于潔白過于接近春天
在干凈的院子里讀你的詩歌。這人間情事
恍惚如突然飛過的麻雀兒
而光陰皎潔。我不適宜肝腸寸斷
如果給你寄一本書,我不會寄給你詩歌
我要給你一本關于植物,關于莊稼的
告訴你稻子與稗子的區別
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
春天
余秀華將鄉村日常生活審美化,并且帶著一種平淡的語氣進行言說,詩中自然充滿人間生活氣息,再現了美麗的鄉村日常生活圖景。
2.自我真摯情感的抒發,“殘缺”情感的審美化。
余秀華始終帶有對純真愛情的渴望與贊美,對親人的關懷,對日常生活的禮贊,感情是真摯的,也是感人的;如果說前面是樂觀的歌唱,那么占據余秀華世界的就是一種“殘缺”之感,這時她是痛苦的。“一顆孤獨的稗子給予我的相依為命/讓我顫抖又深深哀傷”《在村子的馬路上散步》,“漏風的身體,也漏雨”《在黃昏》,“它們踩在我身上,總是讓我疼,氣喘吁吁”《荒漠》,“把愛過的人再愛一遍,把疼通過的再疼一遍”的癡情者(《人到中年》)。如《我以疼痛取悅這個人世》:
當我注意到我身體的時候,它已經老了,無力回天了
許多部位都交換著疼:胃,胳膊,腿,手指
我懷疑我在這個世界作惡多端
對開過的花朵惡語相向。我懷疑我鐘情于黑夜
輕視了清晨
還好,一些疼痛是可以省略的:被遺棄,被孤獨
被長久的荒涼收留
這些,我羞于啟齒:我真的對他們
愛得不夠
作為農民的余秀華、作為女人的余秀華、作為殘疾人的余秀華,這三重身份中有著鄉村物質的貧乏與生活的單調,不幸婚姻的哀嘆以及對理想愛情的渴望,肢體的殘疾,余秀華在詩中充滿了一種對痛苦的言說,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憧憬,而這種感情通常是容易使讀者產生共鳴與感動的。
3.語言方面,運用口語寫作。
余秀華運用口語寫詩,通過錘煉,詩歌充滿原始語言的感染力、穿透力。“如我所愿,秋天咬了我一口”(《在秋天》,) “月亮那么白,除了白,它無事可做/多少人被白到骨頭里/多少人被白到窮途里”(《九月,月正高》)。最為著名的是《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其實,睡你與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無非是
兩具肉體碰撞的力,無非是這力催開的花朵
無非是這花朵虛擬出的春天讓我們誤以為生命被重新打開
大半個中國,什么都在發生:火山在噴,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關心的政治犯與流民
一路在槍口的麋鹿與丹頂鶴
我是穿過槍林彈雨去睡你
我是把無數的黑夜摁進一個黎明去睡你
我是無數個我奔跑成一個我去睡你
當然我也會被一些蝴蝶帶入歧途
把一些贊美當成春天
把一個與橫店類似的村莊當成故鄉
而它們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這些語言是原生態的,用漢語口語寫作的,并且經過錘煉,“睡你”、“摁進”,極具有語言的質感,乍看之下具有陌生化效果,然而又是非常生活化的,在口語中是常見的。
二、作為文學事件的余秀華詩歌
“文學事件化是指文學的影響力與受關注度,不是,或主要不是來自其自身的主題、人物形象、意象、修辭等美學或文學要素,而是與作家離奇經歷、容貌身份,或者文人官司、名人逸事、時政要點、社會突發事件等一切具有社會新聞效應的特定事件相聯系,通過與文學相關的這些事件發酵擴大文學在社會公共空間關注度與影響力的廣度、深度與持久度。”[2]余秀華詩歌的廣受關注,自然離不開媒體的包裝與宣傳,當然也是有著詩歌藝術審美性的感染,更為重要的是余秀華以及其詩歌暗合了這個時代的大眾文化心理,因而能夠在社會中廣泛地傳播與產生深遠的影響。
總體上來講,在余秀華及及其詩歌文學事件化的癥候背后存在著三個因素:苦難、疼痛、創傷。余秀華其人同其詩歌其實是事件的一體兩面,“風格即人。”[3]劉勰認為:“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正,并情性所爍,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4]顯然可以用來說明問題。余秀華身上存在著三重身份:農民、女人、殘疾人,而這三種身份都是在社會被“邊緣化”的,可以說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而讀者在被其詩歌的語言與風格所傾倒的同時,一種由心底油然而生的同情與共鳴更加強烈,而這才是余秀華詩歌在讀者大眾中“走紅”的關鍵所在。
“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5]因而人們在遭受創傷之后,這種欲望進入潛意識,不為意識所察覺,但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著不自覺的流露,而余秀華的詩歌正是起了釋放人們潛意識,撫慰創傷的作用。可以說當今社會的人們在商品經濟大潮中,受到了極大的壓抑,面對現實的荒誕,渴求著對田園牧歌,希圖溫柔的撫摸,醫治殘缺的身體與心靈。而余秀華詩歌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渠道,人們正是在余秀華身上寄托了自身,渴望著自由,純真的愛情,安靜的鄉村,以及對痛苦的逃避。正是在這一點上,個人的體驗同時代大眾的感受合拍,余秀華的“疼痛”正是應與了大眾心中的“創傷”,余秀華的“苦難”正是所有人的“苦難”,身體的“欲望”、“殘疾”、“疼痛”經歷了“升華”,表達了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缺失,余秀華與她的詩正好對應了這種缺失,也因此余秀華能夠在大眾“走紅”,這并非只是媒體的宣傳作用,而是余秀華跟她的詩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也是這個時代的需求,可以說余秀華走在了大眾文化的前列,而這是余秀華詩歌事件癥候的特點。
三、大眾文化與自我救贖
“可以說余秀華的情感是有殘疾的,這在個時代,大部分人的情感都是有殘疾的,她與這個時代合拍了”[6],不論余秀華是抱著何種意識在寫作,一旦發表同讀者接觸,就必然要面對大眾社會的挑戰,余秀華詩歌走紅,自然是迎合了社會大眾的心理,當然也要接受大眾文化的改造與運作。在第一點中講的是余秀華詩歌同大眾文化的認同,而第二點是他們之間的抗拒。
“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已經從過去的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消費品。”[7]余秀華及其詩歌已經進入了大眾的文化消費過程之中,因而遭到市場的“改造”,以適應大眾消費的需求,而余秀華本人也積極參與了詩歌消費運動之中,與“資本”共舞,取得了經濟上、商業上的勝利,但是無疑減損了詩歌的藝術特性。
大眾對詩歌的偏愛,從市場邏輯上來說,是一種明顯的“媚俗”心理。詩歌是雅文化的象征,同大眾是分離的,但是在大眾文化時代,雅俗文化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詩歌也開始為大眾所享有,近年來出現的“梨花體”、“忠秧體”、“咆哮體”、口語詩等見證了大眾對詩歌的極大興趣。追逐時尚、制造轟動效果,在詩歌界已經屢見不鮮。大眾對詩歌的偏愛,與其說是一種藝術上的追求,不如說是一種“惡趣味”的模仿,對“詩歌”的消費。余秀華的詩歌正是在這一點上成為大眾“媚俗”心理的消費品。余秀華詩歌的語言是口語性質的,消除了大眾與詩歌,或者高雅藝術的距離感,因而對大眾具有心理上的親切感;而在藝術形式上余秀華采用自由詩的排列,以一種自然而不見可以經營的形式而呈現出來;同時余秀華的農民出身,理所當然地同大眾底層相互指認,詩成為大眾底層的對象而可供消費,高深晦澀的現代詩,清高而不可接近的詩人,一直大眾所拒斥,余秀華作為底層、民間詩人,憑借其與生俱來的身份與詩歌語言、形式的簡練、形象的可感,同時那種田園鄉土的詩情,正應與了大眾厭惡現代文明,渴望回歸的心理。此時,余秀華及其詩歌在大眾的審美視野中是“媚俗”的,是一種大眾的詩歌。同樣,伴隨著“媚俗”,余秀華詩歌的被“改寫”與同質化就成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一切都為大眾文化所改造,而其中的異質性被消除,在市場邏輯中失去其藝術的主體性,而淪為市場、大眾的奴隸。
“疼痛”、“創傷”、“苦難”作為余秀華詩歌的文化癥候與敘事倫理,是余秀華農民、婦女、殘疾人三重身份的一種外在顯現。正是這三種身份引起的“壓抑”,余秀華詩歌中才因而具有一種異質性:對貧困的超脫、女性意識的顯現、新的視角的發現(如搖搖晃晃),余秀華在那種超脫背后,是有著一種苦難的意識的,詩在她那里是一種自我救贖的工具,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大眾那里,與其說是一種救贖的感覺,不如說這種“苦難”、“創傷”、“疼痛”以及農民、婦女、殘疾人三種身份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獵奇心理、消費心理、媚俗心理是大眾文化所采取的態度,苦難成為了消費。大眾欣賞的只是余秀華詩的社會屬性,一種外在的光環,而并非藝術的審美本質,“展示價值”取代了“崇拜價值”,余秀華詩歌在走下詩歌“神壇”,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之后,失去“靈韻”,這也是大眾文化的文化邏輯與必然命運。
[1]余秀華.月亮落在左手邊上[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余秀華.搖搖晃晃的人間[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
余秀華.我們愛過又忘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更多余秀華詩作見其實名認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34106437_0_1.html
[2]孫桂榮.余秀華詩歌與“文學事件化”.南方文壇[J].2015(04):87.
[3](法)布封.論風格.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上)[M].伍蠡甫、胡經之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223.
[4]劉勰.體性第二十七.文心雕龍譯注[M].王運熙、周鋒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6.
[5](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216
[6] 張執浩.余秀華那種殘缺的情感與這個時代暗合. http://cul.qq.com/a/20160606/031145.htm
[7](美)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M].唐小兵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