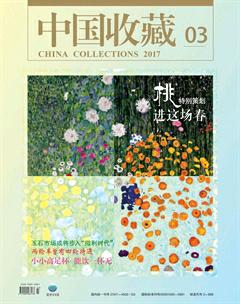問桃為何伴神仙
劉明杉
桃是中國古代慶壽活動中最重要的果品,自古以來為長者祝壽時,晚輩都要向長者獻上象征健康長壽和幸福吉祥的壽桃。這一悠久的文化習俗,與古代神仙觀念中將桃視作仙果,食之可長生有關。
志怪故事多
早期文獻里有不少記載仙桃的志怪故事,如漢末建安前后的《漢武故事》中,記載了武帝向王母請不死藥,王母送其仙桃之事。“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因出桃七枚,母自啖二枚,與帝五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為?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又記武帝擅殺,王母與之斷緣,遣使再贈三桃,是日東方朔死。“后上殺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謂上曰:‘求仙信邪?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與帝絕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極壽。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之,問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上厚葬之。”北魏人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卷10“桃”引《神農經》:“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之,臨死日服之,其尸畢天地不朽。”
最香艷的食桃得長生之事,要屬“劉阮天臺遇仙”典故。長久以來,這個故事就作為各類文學戲劇和藝術品的創作素材,被廣泛傳播,人們將去而復來的人稱作“前度劉郎”。清乾隆時人馮浩為唐代李商隱《玉溪生詩詳注》卷1注中,有一段活色生香的描寫。“《御覽》引《幽冥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晟、阮肇共入天臺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經十余日,遙望山上有桃樹,大有子實。至上,啖數枚下山。見山腹一杯流出,有胡麻飯度山出。一大溪有二女子,姿質妙絕。二女便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遂同還家,有群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留半年,求歸甚苦。女呼前來女子,集奏會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八山迷不得歸。”
英國巴特勒爵士藏有一件清康熙早期劉阮入天臺故事青花碗,描繪了兩位佇立于幽幽山谷深處的仙女,正在盛情地邀約劉晟、阮肇二人隨她們還家。畫面中站在仙女下方的劉、阮二人早已疲憊不堪,其中一位肩上還扛著采谷皮等草藥的鋤頭。劉、阮二人因迷路饑餒殆死,是仙桃讓他們恢復了體力。群女出迎,手中也各持三五桃子。留宿半年,歸家已是七世。
桃作為仙界神果,婦孺皆知的故事,是王母娘娘生日邀群仙參加蟠桃盛會,其最主要的傳播方式就是演劇。宋元時期的《王母蟠桃會》,全劇已佚,作者不詳,惟有《南曲九宮正始》、《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南詞定律》中引錄三支佚曲:“【中呂引子·金菊對芙蓉】濃靄香中,水云影里,迥然人世難同。似玉皇金苑,寶錄仙宮。萬花開處神仙滿,盡笑語俱樂春風。蟠桃佳會,特離絳闕,來此相逢。【正宮近詞·春色滿皇州】索居仙洞僻,與無心去來白云為侶。清興逸幽閑自得仙機。聞知,今日是王母生辰,來慶賀略伸微意。(合)歡娛處,見群仙開列,共樂瑤池。【前腔換頭】今日,晚來和氣舒。見祥云滿空,光景熙熙。香霧靄,和風麗日遲遲。偏宜,庭前見花木生春,麟鳳躍魚龍游戲。”三首曲牌為蟠桃會開始時所唱,首曲由王母唱,后兩曲由赴宴的群仙唱,詠敘蟠桃會之盛。
教坊雜劇興
入明以后,教坊演出了大量的神仙道化劇。教坊在太祖朱元璋初克金陵時即設,《明史·樂志》記其職能:“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及進膳、迎膳等曲,皆用樂府、小令、雜劇為娛戲。”按明初所定《大明律》卷27刑律10“搬做雜劇”:“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這就導致教坊雜劇中,神仙道化劇風行。《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是鄭振鐸1938年在上海發現的中國戲曲史文獻,其中很多為宮廷教坊司和鐘鼓司藝人所作,慶壽雜劇有《寶光殿天真祝萬壽》、《紫薇宮慶賀長春壽》、《群仙慶賞蟠桃會》、《賀萬壽五龍朝圣》、《祝圣壽金母獻蟠桃》、《眾天仙慶賀長生會》、《降丹墀三圣慶長生》 《慶冬至共享太平宴》、《眾神圣慶賀元宵節》、《賀升平群仙祝壽》、《祝圣壽萬國來朝》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爭玉板八仙過滄海》、《廣成子祝賀齊天壽》、《慶豐年五鬼鬧鐘馗》 、《黃眉翁賜福上延年》、《河嵩神靈芝慶壽》、《感天地群仙朝圣》等。晚明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25“雜劇院本”云:“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以至三星下界、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皆系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并勛戚貴珰輩贊賞之耳。”
教坊雜劇的缺點是劇情雷同、形式單一。無非是天上諸路神仙云集下界,集天下稀罕寶物為人間的帝王后妃慶壽。戲劇家朱有燉是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嫡長子、太祖第六孫,父子都曾在權力斗爭中遭受過打擊,為避禍遠離政治,專意戲曲創作,有雜劇31種存世。在其作品《群仙慶賞蟠桃會》中,王母派董雙成、許飛瓊二仙女看守蟠桃,她倆在樹邊略睡,東方朔化作千年靈龜、仙鶴前去偷桃,被仙女捉住,場面詼諧,調節了乏味的舞臺氣氛。而優勢在于排場氣派、砌末華麗。以該劇“穿關”(裝扮實況)為例,神仙的衣著扮相和所持砌末都很考究。“董雙成、許飛瓊:同前東方朔、老沒影:散巾、邊綢道袍、絳兒、鹿衣東方朔、老沒影又上:同前,仙鶴衣正末南極星:如意蓮花冠、鶴氅、牌子、玎珰、白發、白髯、執袋仙童、仙女:同前鐘離:雙髻陀頭、紅云鶴道袍、錦襖、不老葉、法墨踅、喬兒、網裙、雜彩絳、執袋、行纏、布襪、八答鞋、猛髯、棕扇呂洞賓;九陽巾、茶褐云鶴道袍、錦襖、不老葉、法墨踅、喬兒、網裙、絳兒、執袋、腿繃護膝、布襪、八答鞋、雙劍、三髭髯、裙扇鐵拐李:鬅發陀頭、皂補納、錦襖、不老葉、法墨踅、喬兒、網裙、雜彩絳、執袋、行纏、布襪、八答鞋、猛髯、鐵拐韓湘子:雙髻陀頭、邊襕道袍、不老葉、執袋、白發、白髯、驢扇藍采和:韶巾、祿襕、偏帶板曹國舅:雙髽髻陀頭、云鶴道袍、不老葉、執袋、絳兒、金牌笊籬張四郎:秦巾、云鶴道袍、不老葉、執袋、絳兒、笛”,此處記述了東方朔、南極星、鐘離權、呂洞賓、鐵拐李、韓湘子、藍采和、曹國舅、張四郎等。
張四郎原是八仙人物之一,在《賀升平群仙祝壽》、《眾天仙慶賀長生會》中都有此人物。從傳世實物看,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宋代緙絲《群仙拱壽圖》,下方八仙圍在一起抬頭仰望壽星,一些仙人望天拱手;上方騎仙鶴的壽星向下拱手,呼應群仙。可以看出圖中皆為男仙,而社會需要八仙中出現一位女仙,加之張四郎的傳說又少,到了明代中期,就被何仙姑取代了。實物見清宮舊藏一件剔黑八仙祝壽圖八方盒,高21厘米,口徑26.4厘米,足徑19.8厘米。八角式,朱漆錦地雕黑漆紋飾,蓋面為《八仙祝壽圖》,周身均在開光內雕鳳穿牡丹紋,徑足部雕海獸紋。蓋內刻一首乾隆御題詩,末署“乾隆壬寅御題”款。盒內及底髹黑光漆,底左側刀刻填金“大明永樂年制”楷書偽款。蓋面上八仙人物圍站在壽星身邊,鐘離權向壽星獻酒,右下方是舉著一柄蓮蓬的何仙姑。此器漆層淺薄,從工藝和人物來看,都符合明代中期特征,“大明永樂年制”款和乾隆題詩均為后刻。
“偷桃”受歡迎
晚明時期,朱有燉創作的《群仙慶賞蟠桃會》仍在上演,只是張四郎被何仙姑所取代。此時在景德鎮民窯瓷器上,常將社會流行的戲劇情節描繪在民窯瓷器上,以吸引大眾購買。如首都博物館藏一件萬歷青花碗,其上就描繪了《群仙慶賞蟠桃會》的劇目情節,即八仙祝壽圖和東方朔偷桃圖組合。該碗口徑21厘米,釉色純凈光潤,釉面潔白。外壁一周繪張果老、呂洞賓、鐘離權、韓湘子、鐵拐李、藍采和、何仙姑、曹國舅八仙祝壽圖。額頭高聳的壽星端坐在石臺上,與獻桃的鐘離權對視。在壽星的頭肩部,畫有一個圓形背光,凸顯其至尊的身份。壽星又稱南極仙翁、南極老人、長生大帝,是中國神話中的長壽之神。鐘離權被全真道尊為“正陽祖師”,后列為全真北宗第二祖,曾十試呂洞賓度他成仙,還傳授其“點石成金”之法。鐘離權在八仙中成仙較早,名氣較大,資格較老,因此在“八仙祝壽圖”中,由他向南極仙翁祝壽。
此碗碗心繪東方朔偷桃故事,畫風以特寫手法表現,主題人物占據畫面突出位置,庭院背景則作弱化處理。畫面中心繪身穿道袍的東方朔雙手捧一蟠桃,神色狡黠地回望身后是否有人發現他。庭院是簡約的山石、松樹和欄桿,為示意此處為仙境,畫面右上繪一朵碩大的如意云頭。圈足外壁以青花繪一道弦紋,底部“大明萬歷年制”青花楷書款。《漢武故事》中記載:“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又:“東方朔于朱鳥牗中窺母,母謂帝曰:‘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 可見東方朔偷桃典故出現較早,明代此題材很受民眾歡迎,文藝作品有吳德修撰《東方朔偷桃記》傳奇和佚名雜劇《東方朔》,傳世的藝術名品有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唐寅畫作、現藏美國馬薩諸塞州美術館的吳偉畫作,以及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以沈周畫作為藍本的緙絲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