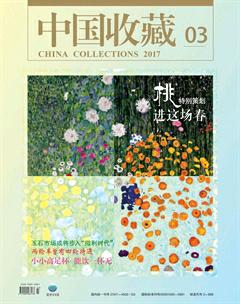百囀千聲隨意好
“百囀千聲隨意好,琪花瓊草逐時(shí)新。”這是一句題寫在瓷器上的春日景色,詩(shī)中描繪的繁花、鳥(niǎo)鳴恰如這件器物上的繪畫,描繪了一幅美好的春光。這是一件雍正朝的琺瑯彩梅花牡丹紋碗,其以玻璃白為底,渲染其上的梅花淡雅柔和,牡丹嬌嫩艷麗,且一改舊時(shí)單線平涂的手法,畫面富有層次感和立體感,實(shí)為琺瑯彩中的上品。
冬去春來(lái),乍暖還寒之時(shí),梅花率先悄然盛開(kāi),這樣的景象被畫工記錄在瓷器之上,若是嫌報(bào)春的梅花太過(guò)孤單,畫工常配以靈芝,或?qū)⑾铲o躍然枝上,一改冬日的安靜與孤寂,也寄托了古人美好的心愿。
梅花清雅,以玻璃白為底最妙;牡丹雍容,與之相應(yīng)的搭配也更為多變。在眾多的彩色釉中,琺瑯彩與粉彩實(shí)為其中的上品,更適宜表達(dá)繁花似錦之景。琺瑯彩是宮廷御用瓷器中極為名貴的一種,清代的琺瑯彩始燒于康熙一朝,直至嘉慶朝初期停止燒造,僅四十余年的輝煌。燒造時(shí)間如此之短的一個(gè)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琺瑯彩的制作成本頗高。最早琺瑯彩瓷器顏料多為進(jìn)口來(lái)的,在景德鎮(zhèn)燒制好瓷胎運(yùn)入大內(nèi),由宮廷畫師繪制圖案,再于宮中進(jìn)行二次燒制。清帝對(duì)此頗為重視,每一件琺瑯彩瓷器的圖樣都由皇帝親自過(guò)目,并提出修改意見(jiàn)。清朝時(shí)的琺瑯彩皆為宮中御用,民間并未曾燒制和使用過(guò)。
慈禧對(duì)粉彩亦十分青睞,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大雅齋”的粉彩牡丹梅花花鳥(niǎo)紋圓盆和盆托,盆口沿紅彩書(shū)“大雅齋”三字楷書(shū)款和“天地一家春”五字篆書(shū)款。天地一家春是圓明園中的一處住所,相傳慈禧曾于此承寵懷上了阿哥,也就是日后的同治皇帝,于是慈禧多年一直鐘情于此處,認(rèn)為這里是一處福地。這件器物上牡丹花團(tuán)錦簇,梅花枝頭鶯聲燕語(yǔ),這樣的無(wú)限春光,當(dāng)與慈禧其時(shí)的心境相符吧?
琺瑯彩與粉彩恰如春日里的繁花爭(zhēng)奇斗艷,難分伯仲。然而色彩太過(guò)于濃艷與古代文人含蓄的表達(dá)方式不大相符。若是踏春之時(shí)攜一支春日里嬌艷的花枝而歸,將其插入梅瓶之中,把春光留在屋中,也許是再好不過(guò)的了。梅瓶起于唐代,勝于宋時(shí),這也許與宋人的文人情趣分不開(kāi)。梅瓶因口徑之小與梅之瘦骨相若而得名。瓶體修長(zhǎng),小口、短頸、豐肩,肩下漸收斂,許多較早時(shí)期的梅瓶都帶蓋,這說(shuō)明梅瓶原是裝盛液體之類的容器,后來(lái)其主要用途則是作為裝飾品和陳設(shè)用器,實(shí)用功能反而退居其次了。若是用甜白釉的梅瓶插上一束花,想必會(huì)不負(fù)這春日的明媚。
古人說(shuō)莫負(fù)了韶華,便將姹紫嫣紅與鳥(niǎo)語(yǔ)鶯聲繪于瓷器之上,萬(wàn)般春色皆出于此。若是不能將其把玩于手,倒不如走出屋門,親眼去見(jiàn)一見(jiàn)這畫中的美景,身臨于這般生機(jī)盎然的景色之中,也是一種莫大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