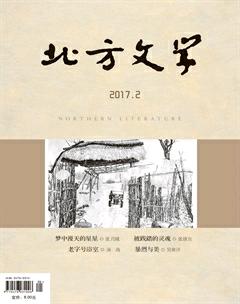不見長安
張齊
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座長安城,但有些人,尋尋覓覓,兜兜轉轉,花了一輩子,才明白,自己其實從未到過那里。
——題記
長安,是一座城,唐人的城。柳絮飛,箜篌響,路人醉。無論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的慵懶,還是“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的肆意。宋人筆下的情態,早在幾百年前的長安就有了。蘇軾的“大江東去”,柳永的“曉風殘月”,豪邁與婉約的碰撞,早在幾百年前的長安就有了。后來,長安沒了,唱斷了弦的琵琶,即使換了八九回的新曲,卻依舊是舊時長安城里曾響過的悲歡。
長安,是一座城,那里有最快的馬、最烈的酒、最鋒利的劍;那里有最精致的畫舫、最珍貴的筆墨、最威嚴的府宅;那里有最妖嬈的舞姬、最風流的墨客、最高不可攀的權貴。長安城里智者狂,癡者悲,一句詩換一場醉,長歌嚎啕哭幾回。后來,長安沒了,汴京、臨安、北平,再沒有一個都城能像它一樣能在史書里獨占鰲頭。汴京足夠滄桑但奢華不足,臨安溫軟有余卻缺乏剛硬,北平倒是極好的,朱墻金瓦,明晃晃的紫禁城照得人心都要醉了,可它經歷了太多屈辱,炮火和血淚,給了它狠狠的一巴掌。
長安——永寧之意,是經歷了戰國紛爭后的儒家思想的大成,是保留了巍巍大漢朝百年光輝的延續,是秦時明月漢時金吾的畢生追求。它承載了黎民百姓經年的愿望——天下太平。它也確實太平:胡姬酒肆、胭脂娥眉,在這太平盛世的模樣里,彌漫的空氣都是軟的。有多少人,為了一世長安的夢想,辭家去戶來到長安;又有多少人,為了長安的永寧,金戈鐵馬赴邊關。來也想長安,去也念長安。好像時刻將長安掛在嘴邊,就真的能一世長安。
但長安,真的能長寧嗎?但凡是人間之城就不可能是一塊樂土,長安是在時代掌控下的一座城。就像狄更斯的《雙城記》里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同樣的,長安是最好的城,也是最壞的城。既然有“朱門酒肉臭”也就不乏“路有凍死骨”,長安居,大不易,他人冠蓋滿京華,我則凄涼獨自行者比比皆是。
這長安,是紙上的長安,是故事里的長安。
曾經的那座城,現在已經是西安了。雖然依舊是芙蓉面楊柳眉,但卻更加平添了幾分愁緒與寂寥。
走在西安的馬路上,環抱著參天的古樹,感受著它粗糲的皮膚,好像就聽到了長安的微弱心跳。踏在堅硬的瀝青馬路上,暴烈的太陽掀起令人眩暈的刺鼻氣味,就好像這座城過去種種癡嗔恨怨的凝結。不知我踏上的這片土地下,坍塌過多少的畫棟雕梁,曾經的王侯將相,又有多少在這里含笑或飲恨而終。又有誰能知道,這片蒼穹之下,黃土之中,曾有一人,傾盡風流,艷絕天下?曾有一人,機關算盡,寥寥半生?
長安在時,長安不寧,長安已逝,何處永寧?
長安是一個桃花源,武陵人尋而不至。同樣的,我們心中的長安城,我們也從未去過。我們得到的,只有一個暗戀的長安,我們用那點對模糊長安的微薄渴求,盼望著,一世長安。
長安居,大不易,身在長安,就不可能一世長安。長安尋夢,如夢里尋花——拾一朵,失一朵。真正長寧的人,若非得天獨厚,便是不在長安。
長安城是花柳繁華地,富貴溫柔鄉,永寧之所多是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凈土,世間真正得到永寧的——如同范蠡、張良,泛舟五湖,歸隱山林。寄情山水,遠離紛爭。鳶飛戾天者,經綸世務者,都在長安長寧的騙局下,一輩子汲汲營營,為人做裳。
長安像一個巨大的墳墓,埋了許多人的一生。城門上寫的不是長安,而是不寧。城里人的一生一句話就能概括:生于此,謀于此,死于此。
此非人,不過一棋子耳。
我們尋到的長安,不能長安,心里的長安,卻從未去過。
心上掛著的東西那么多,那樣重,那么累,怎么可能長安呢?
此心安處,即是長安。心無掛礙,便是長安。
不見長安,或許方能一世長安吧。
(作者單位:甘肅省蘭州市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