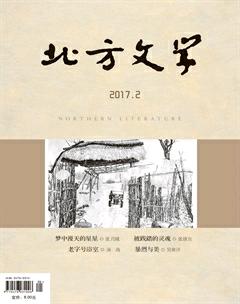歸化、異化在翟譯和趙譯《三字經》中的具體表現
顧燁
摘要:本文以翟譯和趙譯《三字經》為目標文本,從風格、文化和語言三個層面剖析了歸化與異化在兩文本中的具體表現,以此吸引更多的國內外學者關注中國典籍的英譯,促進中華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提升中國在國際中的影響力。
關鍵詞:《三字經》;歸化;異化
一、風格層面
《三字經》共1000多字,它之所以膾炙人口,口口相傳,是因為三字的的韻文詩句極易成誦。對比兩個譯本,以第一節為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趙譯: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翟譯: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Their natures are much the sam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趙彥春,2014:1)
翟里斯作為一位優秀的英語詩人,他一般是按照構成和押韻的方式來翻譯詩歌,保留英文詩歌的韻律,但是他翻譯的《三字經》卻缺少了本應保留的節奏韻律。為了服務于漢語教學的翻譯目的,他選用了英漢對照的編排方式,給每一個漢字都注了音,并且每個音的右上角都用阿拉伯數字(1-4)來表明它的聲調。雖然對于每一個漢字的發音,他都做了做了一個語音翻譯補償,希望讀者可以欣賞到原來的中文節奏,但是他既沒有考慮到原文句子的工整性,也沒有注意到句子的韻腳押韻,只是單純地把原文的意思翻譯出來了。而趙譯本用三個英文單詞對應漢語的三個字,用詞精準,使用小句,并且采用了偶韻體(aabb韻式)來類比《三字經》原文的aaba韻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風格特點。
就譯文的文體風格和特點來說,趙彥春教授采用了異化的策略,盡量向原文靠攏,保留了原文的特色,最好地反映了他的寫作意圖和藝術風格。而翟譯本則采用了歸化的策略,通篇以直譯加解釋為基本手法,為了讓西方讀者更好地學習漢語。
二、文化層面
王佐良先生(1916-1995)曾說過:"譯者處理的是個別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Leech,1987:21)文化負載的處理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鑒于譯者不同的翻譯目的,以及他們不同的文化意識和創造性,他們處理的策略和可能也會不盡相同,下面我們來比較一下兩譯本的處理方法。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死書。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
趙譯:To further learn,
You now turn
From school nooks
To Four Books.
Analects—the lections,
Has twenty sections.
Confucius and disciples
Gave off sparkles.
翟譯:Those who are learners,
Must have a beginning.
The ‘Little Learning finished,
They proceed to the four books.”
There is the Lun Yu,
In twenty sections.
In this, the various disciples,
Have recorded the wise sayings of Confucius.”(趙彥春,2014:179-184)
《三字經》這幾句涉及到了一些中國傳統的文化知識。譯者對這種文化因素的翻譯常常采用的是音譯加注釋的方法。翟里斯在翻譯這幾句話的時候也是采取的這種方法。把論語翻譯為"the Lun Yu”并加注釋"The Lun Yu contains practically all we really know of the sayings and doings of Confucius.It is ascribed by tlie Chinese to the immediate disciples of the Sage.”翟里斯使用漢語拼音(the Lun Yu),這種異化的策略,保留了源語的文化特征,并且切合了他漢語教學的目的。但這里趙彥春教授就把論語直接譯為眾所周知的"The Analects”,采用的是歸化的策略,更多地考慮了譯文讀者的理解。
同時,我們可以發現,兩個譯者對"小學”這個詞的翻譯也不相同,翟里斯采用的還是異化的策略,以音譯加注釋的方式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專有名詞。當然這里由于翟里斯將小學譯為"Little Learning”與后文表示"四書”之一的Great Learning(《大學》)相對應,并且還與下行的"the four books”在句式上構成并列關系,容易使讀者以為"Little Learning”也是部書。但就當時來說,翟里斯最大限度地尊重和傳播了中國獨有的文化因素,以音譯加注釋的方式實現了形式的對等。而這里趙彥春教授采用的是意譯的方法,用"school nooks”指代小學學習生活,“nook”一詞生動形象,具有隱喻的聯想美,增添了語言的生動性和形意張力。
三、語言層面
在英譯中國典籍時,典故的翻譯是個重點,也是個難點,因為譯者往往很難找到與之對應的英文詞匯,對比兩譯本,可以發現,兩譯者在翻譯典故時都采用的是歸化的策略。
“蔡文姬,能辯琴。謝道韞,能詠吟。
趙譯:Tsai could discern
An ill-tuned zithern.
Hsieh could prose
Or poems compose.
翟譯:Tsai Wen-chi
Was able to judge from the sound of a lute.
Hsieh Tao-yun
Was able to compose verses.”(趙彥春,2014:401-402)
此節經文講述中國古代的兩位才女,蔡文姬和謝道韞。蔡文姬幼時聽父親演奏焦尾琴時,她能聽出琴弦斷了,斷的是哪根;謝道韞,七八歲時便能出口成章,即興作詩。
原文中"辯琴”的琴指的是蔡邕制作的焦尾琴,是古代中國的四大名琴之一,屬于文化負載詞,因此無法找到英文對等詞,屬于"詞義空缺”。面對此情況,翟譯和趙譯均選擇了歸化譯法,翟里斯選擇了"lute”,趙譯選擇了"zithern”(指古歐洲的弦樂器),容易使譯語讀者聯想到"古代樂器”,幫助讀者理解。
雖然兩位譯者的翻譯目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兩位譯者同時采用了歸化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翻譯目的。
縱觀兩譯本,可以發現,兩位譯者都是在忠順、透明、以歸化為主的前提下,采用了歸化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