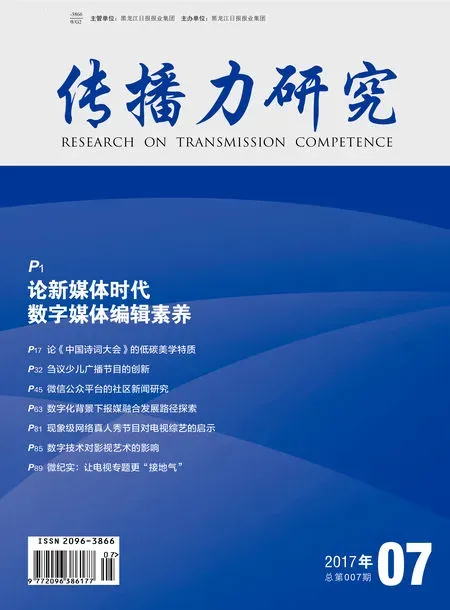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對高校應(yīng)急管理的影響
文/胡洪
一、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
(一)網(wǎng)絡(luò)輿情
軍犬輿情創(chuàng)始人彭作文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輿情,是“網(wǎng)絡(luò)輿論情況”的簡稱,是以網(wǎng)絡(luò)為載體,以事件為核心,廣大網(wǎng)民情感、態(tài)度、意見、觀點的表達(dá)、傳播與互動,以及后續(xù)影響力的集合。網(wǎng)絡(luò)成為反映社會輿情的主要載體之一。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社會輿情載體呈現(xiàn)多樣化趨勢,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成為新的主要載體。廣大手機(jī)用戶依托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通過手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網(wǎng)站、手機(jī)視頻、手機(jī)微博微信等方式,閱讀、分享身邊的新聞事件,發(fā)表自己的觀點。
網(wǎng)絡(luò)輿情與網(wǎng)絡(luò)輿論不同,前者是個體的無序表達(dá),是人們情感、態(tài)度的原初表達(dá)。但是當(dāng)輿情出現(xiàn)聚集的時候,就會向輿論迅速轉(zhuǎn)化。陳力丹認(rèn)為,“輿論是公眾關(guān)于現(xiàn)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xiàn)象、問題所表達(dá)的信念、態(tài)度、意見和情緒表現(xiàn)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qiáng)烈程度和持續(xù)性,對社會發(fā)展及有關(guān)事態(tài)的進(jìn)程產(chǎn)生影響。其中混雜著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因此,網(wǎng)絡(luò)輿論是一種導(dǎo)向,是一把“雙刃劍”,無論對于國家治理,還是高校治理都至關(guān)重要。要避免網(wǎng)絡(luò)輿情向網(wǎng)絡(luò)輿論轉(zhuǎn)化帶來的負(fù)面影響,就需要對網(wǎng)絡(luò)輿情進(jìn)行全面分析,把握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特征,積極引導(dǎo)網(wǎng)絡(luò)輿情向良性健康方向發(fā)展。
(二)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
CNNIC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發(fā)布的報告稱[2],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7.51億,手機(jī)網(wǎng)民7.24億,大學(xué)本科及以上學(xué)歷的網(wǎng)民占比11.6%,網(wǎng)民的人均周上網(wǎng)時長為 26.5 小時。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網(wǎng)民各類手機(jī)互聯(lián)網(wǎng)應(yīng)用的使用率中,即時通信、網(wǎng)絡(luò)新聞、手機(jī)搜索、網(wǎng)絡(luò)視頻、網(wǎng)絡(luò)音樂占前五位。社交應(yīng)用方面,微信、QQ空間、微博、郵件和論壇位居前列,其他興趣社交代表是豆瓣網(wǎng)、天涯社區(qū)和領(lǐng)英。從以上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看出,大學(xué)生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的重要使用群體,移動端已經(jīng)成為網(wǎng)民獲取新聞、社會交往的最主要渠道。
大學(xué)生手機(jī)上網(wǎng)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繼而出現(xiàn)的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已然成為高校應(yīng)急管理需要重點關(guān)注的信息源。對近年來高校網(wǎng)絡(luò)輿情危機(jī)事件的過程分析發(fā)現(xiàn),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可能集中在幾個方面:一是大學(xué)生眼中的“熱點或焦點”,如國內(nèi)國際時政大事,特別是涉及國家主權(quán)、民族尊嚴(yán)、歷史定性等方面的熱點事件。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社會所認(rèn)為的“熱點或焦點”不一定能夠成為大學(xué)生的手機(jī)閱讀關(guān)注點。二是社會事件在大學(xué)生群體中的發(fā)酵。大學(xué)生群體關(guān)注的社會事件,與社會民生息息相關(guān),如拆遷、腐敗、安全、醫(yī)療、教育、社會公德等等。這些事件極易引起大學(xué)生群體關(guān)注,也極易引發(fā)他們作出及時的評論和回應(yīng),從而推動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走向。三是高校范圍內(nèi)大學(xué)生群體學(xué)習(xí)、生活上的關(guān)切點,如課程考核、學(xué)籍管理、獎助學(xué)金發(fā)放、榮譽稱號評定、違紀(jì)處分、食堂飯菜質(zhì)量和價格等。這些與學(xué)生實際緊密聯(lián)系,輿情發(fā)生的空間狹小,極易在短時間內(nèi)完成輿情聚集。因此,對于高校應(yīng)急管理來說,要切實把握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行為特點,從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主體、客體、網(wǎng)絡(luò)輿情自身、數(shù)量、強(qiáng)烈程度、持續(xù)性、功能表現(xiàn)和質(zhì)量八個要素入手進(jìn)行全面分析,以期準(zhǔn)確把握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特征。
二、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特征
彭蘭認(rèn)為,網(wǎng)絡(luò)的傳播媒介屬性包括復(fù)合性、開放性、多級性和連通性。[3]網(wǎng)絡(luò)通過點對點、點對面、面對點,將傳播者與受眾、受眾之間聯(lián)結(jié)起來,實現(xiàn)一級傳播或多級傳播或同步傳播,抑或異步傳播。同時由于手機(jī)網(wǎng)絡(luò)具有便攜性和普及性、即時性和互動性、個性化和多元化、自在性和強(qiáng)制性的特點,大學(xué)生群體基本能夠隨時隨地接入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使得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速度、頻度和廣度都是非常強(qiáng)烈的。
(一)直接與突發(fā)
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直接性與突發(fā)性,與手機(jī)媒體本身的特性息息相關(guān)。手機(jī)作為一種移動終端,以通訊網(wǎng)絡(luò)為基礎(chǔ)、以雙向或多向互動為主要傳播方式進(jìn)行信息傳播。同時,智能機(jī)的普遍使用,“低頭族”熟諳手機(jī)輸入法,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4G時代的來臨,更加速了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能夠即刻實現(xiàn)一對多的群發(fā),也能夠通過微信朋友圈實現(xiàn)一對多個群的信息發(fā)布。這使得高校在輿情爆發(fā)點的當(dāng)口,大學(xué)生群體在第一時間,直接從參與者或旁觀者的角度予以傳播,從而突然將現(xiàn)實事件轉(zhuǎn)化為網(wǎng)絡(luò)“熱點”,成為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發(fā)酵的第一顆“火星”,或引燃一邊倒的評論,或引發(fā)手機(jī)網(wǎng)絡(luò)上口誅筆伐。
(二)隨意與偏差
鑒于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資費的降低,大學(xué)生即便在沒有免費WIFI的情況下,也能夠低成本地接入移動數(shù)據(jù)4G網(wǎng)絡(luò)。這為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提供了沒有時間、空間限制的客觀條件。這樣的客觀現(xiàn)實,不僅助推了輿情傳播的直接性和突發(fā)性,更帶來傳播者和受眾者在傳播過程中的隨意與偏差。在交互性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中,信息傳播的失真被無限放大,況且可能從第一個手機(jī)網(wǎng)絡(luò)傳播者開始,該信息本身就是不真實的。這與大學(xué)生群體關(guān)注政治、社會熱點事件的熱情有關(guān),也源于他們?nèi)狈ι鐣?jīng)驗,理性辨識能力不足。這樣的隨意和偏差,很容易助推輿情進(jìn)一步發(fā)酵,導(dǎo)致信謠傳謠者的范圍擴(kuò)大,影響高校應(yīng)急管理者的有效疏導(dǎo)。
(三)多元與隱蔽
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傳播中,多元性和隱蔽性一方面體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言論沖突中,傳播方式從文字、圖片到視頻、音樂和直播不一而足。另一方面由于傳播者和受眾界限模糊,網(wǎng)絡(luò)監(jiān)督難以精確實施。大學(xué)生群體正處于獨立思維的培養(yǎng)期,思維比較活躍,對網(wǎng)絡(luò)輿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從而引發(fā)網(wǎng)絡(luò)言論沖突,甚至可能導(dǎo)致行為輿論沖突。此外,傳播者和受眾的界限模糊,除了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的影響外,網(wǎng)絡(luò)新聞內(nèi)容制作的專業(yè)機(jī)構(gòu)與自媒體并存現(xiàn)實也是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傳播者也是受眾,受眾也是傳播者。大學(xué)生群體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長大,部分成為了網(wǎng)絡(luò)新聞內(nèi)容的提供者,在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中不再僅僅是被動接收者的角色。
(四)淡化與轉(zhuǎn)移
在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傳播中,多數(shù)情況下,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來得快,去得也快”。這樣的傳播特征,在一些關(guān)注學(xué)生不太集中、社會媒體逐步淡化、社會影響面不太廣、政府及時出面澄清的輿情中,大學(xué)生群體會很快淡化此輿情,并將注意力轉(zhuǎn)移到下一個輿情或者個人的學(xué)習(xí)生活事項中。即便是發(fā)酵時間較長、關(guān)注數(shù)量較多,程度較強(qiáng)烈,負(fù)面影響較大的輿情,總歸也會走向淡化和轉(zhuǎn)移,畢竟大學(xué)生群體有自己的學(xué)習(xí)主業(yè),有教學(xué)規(guī)章和學(xué)生規(guī)范需要遵守,沒有長期的注意力集中關(guān)注某一個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
三、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對高校應(yīng)急管理的影響
一如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傳播特征契合網(wǎng)絡(luò)輿情從產(chǎn)生、傳播、形成、爆發(fā)、應(yīng)對和消退六個步驟[4],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對高校應(yīng)急管理的影響也基本與網(wǎng)絡(luò)輿情的演變過程同步。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在搭建師生即時溝通平臺的同時,對高校應(yīng)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應(yīng)急監(jiān)控難度增大
大學(xué)校園輿情傳播的受眾相對集中,輿情客體容易引起這一類群體更多人的關(guān)注,加上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爆發(fā)的突然性,輿情傳播形式的多樣化,加大了高校應(yīng)急管理的監(jiān)控難度。從輿情客體上說,國內(nèi)國際時政事件在手機(jī)網(wǎng)絡(luò)上不斷刷新,實時報道;國內(nèi)社會事件也不時觸發(fā)大學(xué)生群體關(guān)注熱情;校內(nèi)教學(xué)和生活安排也受到社會民生環(huán)境的影響出現(xiàn)改革、重置等變化,這些除了在全局上把握大事件可能在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上形成輿情外,其他可能形成輿情的“觸點”,即便在高校信息管理部門的實時監(jiān)控下,也很難在輿情形成前做到更為全面的監(jiān)控和把握。
(二)應(yīng)急管理標(biāo)的模糊
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中,同一時間可能出現(xiàn)多個輿情,同一名學(xué)生可能關(guān)注多個輿情。一個輿情的傳播者可能是另一個輿情的受眾,關(guān)注學(xué)生有重合,但也會出現(xiàn)毫不相干的現(xiàn)象。學(xué)生關(guān)注點的不一致,或者說關(guān)注點的多樣化,帶來高校應(yīng)急管理對象的模糊,甚至錯誤。在這紛繁復(fù)雜的傳播網(wǎng)格中,還有可能出現(xiàn)誤傳、瞎傳和亂傳的“起哄”現(xiàn)象,進(jìn)而可能轉(zhuǎn)化為大學(xué)生群體在宿舍區(qū)、教學(xué)區(qū)、運動場區(qū)域聚集的行為。高校應(yīng)急管理部門要同時關(guān)注多個輿情的演變,要歸納學(xué)生的集中關(guān)注點,及時制止錯誤信息的傳播。
(三)應(yīng)急管理面臨群體極化現(xiàn)象
手機(jī)網(wǎng)絡(luò)將每一名學(xué)生納入一個由輿情客體營造起來的虛擬社區(qū)。這個社區(qū)組建高效,雖然意見多元,但帶有現(xiàn)實社區(qū)的群體心理特點。每一個不管是主動介入還是被動“拖入”的學(xué)生,在對輿情發(fā)表看法的時候,都面臨著群體壓力,或者明確支持多數(shù)人的意見,或者保持沉默卻反過來支持了多數(shù)人的意見。這種“沉默的螺旋”[5]、“群體精神統(tǒng)一性的心理學(xué)規(guī)律”[6],極易帶來群體極化現(xiàn)象,也就是對輿情的態(tài)度更傾向于冒險或保守,使得輿情集中爆發(fā)。因此,高校應(yīng)急管理者面臨如何提前介入該虛擬社區(qū),培養(yǎng)社區(qū)意見領(lǐng)袖的問題,以引導(dǎo)學(xué)生意見趨于理性和平和。
(四)應(yīng)急管理容易忽視網(wǎng)絡(luò)弱勢群體
大學(xué)生手機(jī)網(wǎng)絡(luò)輿情的形成與爆發(fā),可能是學(xué)生關(guān)注社會的一個窗口,也可能異化為一場“網(wǎng)絡(luò)狂歡”,成為青年學(xué)生的一場消遣。但是,網(wǎng)絡(luò)廣場上的集體行為容易帶來“網(wǎng)絡(luò)暴力”行為,不論是群體壓力,還是窺探其他同學(xué)的隱私空間,手機(jī)網(wǎng)絡(luò)中的弱勢學(xué)生群體往往在輿情的持續(xù)發(fā)酵中受到傷害,并默默承受。從高校應(yīng)急管理的角度,關(guān)注輿情的演變也要分類指導(dǎo),關(guān)注被裹挾進(jìn)入輿情的學(xué)生,關(guān)注學(xué)生的權(quán)益,從而在輿情消退的時候,保證校園教學(xué)生活秩序的平穩(wěn)。
[1]陳力丹.輿論學(xué)——輿論導(dǎo)向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11.
[2]第40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報告[EB/OL].http://cnnic.cn,2017-8-4.
[3]彭蘭.網(wǎng)絡(luò)傳播學(xu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37-51.
[4]李景升、黃華龍.高校網(wǎng)絡(luò)輿情六位一體應(yīng)急處置機(jī)制初探[J].思想教育研究,2013(3).
[5][德]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M].董璐,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3:5.
[6][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