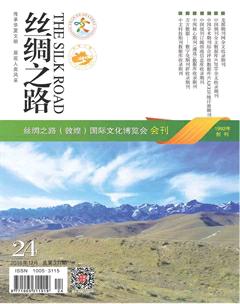《文心雕龍》“虛靜”探微
李銘泰
[摘要]作為《文心雕龍》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術語,歷來學者對虛靜的含義有著不同的闡釋和解讀,以致發生爭論。但是他們都沒有把“虛靜”放在原文中進行深層次的解讀。本文在總結前人觀點的基礎上,力圖把虛靜說還原到《文心雕龍》文本中,尤其是放在創作論部分中探討。虛靜作為一種創作中的狀態,它對物、情、言這些重要文學創作因素之間的關系有重要影響,并對糾正當時的文風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文心雕龍》;虛靜說;文學批評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24-0051-04
一、虛靜的含義
“虛靜”一詞出現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第一篇《神思》中,其文曰“是以陶鈞文思, 貴在虛靜”。①我們知道,劉勰的創作論是以《神思》篇為綱的,作者在此篇中對于“虛靜”作了相關闡述。所以“虛靜”是《文心雕龍》中十分重要的術語。
就目前來看,學術界對《文心雕龍》中虛靜的含義主要有以下幾種看法:第一種主要以汪春泓為代表,他認為虛靜主要來源是佛教思想。②第二種主要以王元化、楊明照為代表,他們認為虛靜來源于荀子“虛壹而靜”的思想。③第三種主要是以黃侃先生為代表,他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認為虛靜與老莊道家思想相關。④另外,張少康先生在《〈文心雕龍〉神思論》中取眾家之所長,折中以上三種觀點,他認為虛靜應該是“以佛道為主,而兼有儒家之長”。⑤筆者認為,以上各家的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中張少康先生的論證最具有說服性。但以上各家重在于對“虛靜”二字本身的哲學探討,他們均過于側重“虛靜”的歷史淵源,而對于結合劉勰當時的文化背景,及對“虛靜”在《文心雕龍》文本體系中,尤其是創作論范圍內的具體印證略顯單薄。
不可否認,“虛靜”首先是作為一個哲學術語出現,然后才逐漸引用到藝術領域,進而又引進文學領域。所以“虛靜”一詞是一個流變的概念,在不同時期它的意義和應用范圍在不斷發生變化。虛靜這個術語最早是由老子提出來:“致虛極,守靜篤。”他所說的虛靜,指我們在認識事物時不要被表面現象迷惑,要讓自己達到虛靜的狀態,深入到事物的內部本質,抓住規律,這樣才能“知常”、才能“曰明”。其后,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這一思想,認為得到事物的本質就要排斥人的感性認識,這樣才能進入“虛靜”這高一層次的認識狀態,達到“大明”的境界。到戰國末期,荀子在《解蔽》篇中提出“虛壹而靜”而至于“大清明”的境界,這是一種比較綜合的說法,即重視內心的清凈無物,又不忽略感官認識。到兩漢之間,佛教傳入中國,結合儒家和道家,“虛靜”的內容進一步豐富,變為佛家修行參理的一種重要狀態。自西漢末到南北朝年間,許多藝術家則開始把“虛靜”引進了藝術創作中,稍前于劉勰的宗炳就是一個代表。他在《畫山水序》中就提出了“澄懷味象”之說,認為藝術家創作活動的展開,要建立在虛靜的精神狀態之上,不應受到種種雜念的干擾。接著陸機把虛靜說引進文學創作論中,他在《文賦》里開篇就說“佇中區以玄覽”,就是為了能夠“精婺八極,心游萬仞”。⑥很明顯劉勰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思想成果,以虛靜說論創作。
我們可以肯定,《文心雕龍》里所說的虛靜是特指文學創作過程中的虛靜,劉勰討論的是文學創作問題而非一個哲學問題。他汲取了前人的哲學思想成果,又受到近代宗炳、陸機等人藝術論的影響,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理論。他絕不是按部就班地抄襲,所以認為劉勰的虛靜論屬于哪一家哪一派這是不科學的。我們結合其在《神思》中上下文語境來看:
故思理為妙,而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而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首先,劉勰認為作為一個創作主體必須要有很厚的學養,“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這是為了練習作者察物體情的本領。一個作家必須要在現實中觀察和研究生活,這樣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才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特點,體會入微的感情,寫出動人的篇章。這是作者達到虛靜狀態的前提。其次是作家真正進入“虛靜”的要求。“神居胸意,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這里需要注意“關鍵”和“樞機”,這里的“關鍵”是指用思想情感和氣勢表達胸臆;“樞機”是指用辭令描摹事物。虛靜就是要使“樞機”“通”而“關鍵”不塞,達到玄解的境界,使得情真而物實。⑦
劉勰是在自己創作經驗的基礎上討論寫作的。他本人對虛靜當有切身的體悟。筆者認為,劉勰所說“虛靜”的含義應該包括兩點:第一,虛靜是創作活動中作者的一種臨文狀態。第二,虛靜是要去除其他思想的干擾,用自己學識所積累的能力構思文章,自然而然地打破物與情、情與言、言與物之間的隔膜,寫出物實情真的文章。
二、虛靜和物、情、言之間的關系
物、情、言是文學創作的三個基本要素,文學創作論主要研究的就是如何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論述在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中早就出現過。牟世金先生指出:“如《尚書·堯典》中的‘詩言志,歌永言;《論語》中的‘文質彬彬;《樂記》中的‘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左傳》中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語;《毛詩序》中的‘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等等,都是講物、言、情三者間的關系。”⑧劉勰是文學理論上的集大成者,當然也要討論這些重要的問題。但是,筆者發現劉勰討論物、言、情這三個要素時,往往和虛靜關聯。
(一)虛靜在物、情關系中的作用
劉勰在《物色》篇討論物、情關系時說: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劉勰認為,人的感情會隨著季節不同事物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從而提出“物以情遷”的觀點。“是以詩人感物,連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詩人在感受事物的時候完全與耳目間的風景、聲音融為一體,隨著對象的變化而情感“婉轉”“徘徊”。他肯定《詩經》“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的方法,能夠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而抒發心中的情感。“《詩》《騷》所標,并據要害,故后進銳筆,怯于爭鋒。”但是后來的人卻一味“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不用真情去體悟山水。
劉勰說:“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欲疏。”意思是“景物有固定的姿態,思緒卻沒有固定的規則。有的好像滿不在乎,就寫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有的用盡心思,反而差得很遠。”⑨由此劉勰提出“入興貴閑”說,“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目的是“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使“物色盡而情有余”;羅宗強認為:這里的“興”是指由物引起人情感,然后使得物有所托喻。而“閑”則包含了“虛靜”“平靜”“悠閑從容的態度和儀態”。⑩筆者認為,在這里劉勰提出的“入興貴閑”實際上就是“虛靜”。第一,上文里我們指出,對于臨文的作者而言,“虛靜”就是要打破客觀事物與主觀情感的隔膜,達到物我一體的狀態。這里所說的“興”就是這個意思。作者和物融為一體,物引起作者的情感,進一步物也包含了作者的情感。第二,羅宗強先生所說的后兩點,即“平靜、悠閑從容的態度和儀態”本身就是虛靜的外在體現。這兩點正是“虛靜”在打通“情”“物”關系中的作用和體現。羅先生的論述,恰恰可以作為“虛靜”的注腳。《物色》篇其文末贊曰“目即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這正是作者在體物時進入的“虛靜”狀態。
(二)虛靜在情、言關系中的作用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附外者也。(《體性》)
因情以立體,即體以成勢。(《定勢》)
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維。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
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性情。(《情采》)
為情造文。(情采》)
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熔裁》)
萬趣會文,不離辭情。(《熔裁》)
繁采寡情,味之必厭。(《情采》)
綴文者,情動而辭發。(《知音》)
以上研究的是情與言的問題。由上可知:第一,情和言是內與外關系,情為內,而言為外。第二,情居于主導地位,先有情而后才有言,言是由情而發的。其實這樣的觀點,早在劉勰之前就有人提出來,但是劉勰比前人的見解更加深入。劉勰指出,創作者在處理情和言的關系時往往會有這樣的情況:其一是針對辭人而言,“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茍馳夸飾,鬻聲釣世”,意即辭賦家往往本無真情而故作情繁之辭,使得文章“淫麗而泛濫”。這是說“言”脫離了實際情感。其二,“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將于風云而并驅矣。方其搦筆,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也”。也就是“情數詭雜”。這是說在創作過程中存在言不能達情的情況。
針對上述的兩種現象,劉勰提出了解決和修正的方法。對于無真情而空有言、為文造情的問題,劉勰結合《詩經》《風》《雅》指出“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情采》)。又舉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例子說明情真言實,防止“才濫辭詭”導致的“心理愈翳”。對于情真而言難達的現象,劉勰在《神思》中提出了他的看法:“是以意受于思,言受于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這里所說“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就是指當言不能達情時,創作者應該不必苦思多慮,而是盡量排除雜念。
其實劉勰提出這兩種處理情言關系的方法都源自于他的虛靜說。“才濫辭詭,心理愈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窺情風景之上”(《物色》),辭賦家的感情不是從心里發出的,而是追求“文貴形似”,從外物尋得。這樣就使得口心不一。要達到口心如一的狀態,創作者要想求“真”,就要進入“虛靜”的狀態,從自己的內心出發,體會自己真正的情感。“水停以鑒,火靜而朗”(《養氣》),正是“虛靜”的印證,只有平靜的時候才能顯現出自己內心最真的情感。對于另一種方法:“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詹锳在《文心雕龍義證》里認為,“秉心”指盡量使自己的精神活動減少。很明顯這就是“虛靜”的狀態,這樣才能“玄解”打通“文章神明樞機”(《聲律》)。11
由此可知,“虛靜”在追求真情、達到“言”“情”統一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虛靜”狀態里寫作者作文才能更容易達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征圣》)。
(三)虛靜在物、言關系中的作用
劉勰在他的創作論里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物”和“言”的關系。
趨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明詩》)
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曠無隘。(《銓賦》)
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神思》)
寫氣圖貌,即隨物以婉轉。(《物色》)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音,“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嚖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 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殊狀: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環聲,模山范水,字必魚貫……(《物色》)
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比興》)
由此可見,“言”就是要盡量準確地表現“物”,使物形象生動,使人如見其面。但是使言完全忠實于物,并十分準確地抓住事物特征達到“取心”的程度,這對于創作者而言有一定的難度。“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事物的姿態不變,但是創作者對事物的思考卻是千變萬化的。像《詩》《騷》里描寫的事物,那才真正是抓住了要害。但是,后來的作者已經達不到那樣的水平而“怯于爭鋒”,導致“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環聲,模山范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但是劉勰對這種風氣并不是完全否定的,“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且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介。故能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物色》)。雖然當時的辭賦家描寫事物極為詳盡和紛繁,但是不可否認他們這樣的寫法確實能夠“瞻言而見貌,即字而知時也”,即使得描寫的事物宛然在目,連時節都可以知曉。這是劉勰肯定的部分。劉勰真正否定的是這種文章的“繁”“麗淫”。“詩騷所標,并居要害”,但是后進者過于“繁”而抓不住事物的要害。“若乃山陵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缺,詳說則繁”,在這里劉勰指出了作者處理“言”與“物”關系時存在的問題,即 “言”過其“物”,或者“言”不達“物”。對此劉勰指出,辭人“應方以接巧,即勢以會奇,善于適要”,繼承和學習前人,根據自己的體悟“接巧”“會奇”“適要”,如此,就會“雖舊而彌新”。
那么,后來詩人摹物時如何做到劉勰所說的“接巧”和“會奇”“適要”,這就要歸于“虛靜”的作用了。上文我們說“虛靜”含有兩個側面,簡言之就是一方面學習前人的經典文章,另一方面在為文時排除雜念,回歸到自然狀態進而更好地理解事物。此處正就是從這兩個方面去討論的。“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舞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余者,曉會通也”,指出要學習前人抓住事物要害的這種方法,因襲繼承。劉勰認為,前人的文章“思接千載”,是非常經典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創作者照抄照搬,而是要參伍相變、因革為功才能做到。另外,劉勰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物色》),強調回到文章的根本上來,物(山林)才是文思真正發源之地。所以應該虛靜觀其物,抓住事物的要害、以適當準確的語言描寫之。
從上面的三點可以看到,“虛靜”在為文中發揮著不可忽略的作用。優秀的創作者往往能在虛靜的狀態中打破情、物、言的關系,貫通內外,寫出既有真情實感又文采斐然的文章。這正是劉勰針對當時文壇風氣所提出的解決方法。《序志》篇中他指出,當時的文章“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褩帨,離本彌遠,將遂訛濫”。可見他們的文章的缺點就是去圣離本和繁縟無物,而“虛靜”恰恰就補充了這兩點。“積學儲寶,酌理富才”,就是要學習前人,防止“去圣”“離本”。而“樞機通”、“關鍵開”的“玄解之宰”就是要求深切地感受事物、體會真情實感,從而防止文濫和言之無物。
[注 釋]
①[南朝宋]劉勰著、戚良德釋:《〈文心雕龍〉校注通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322頁。以下原文均引此書。
②汪春泓:《〈莊學〉與〈文心雕龍〉關系的重新討論》,載《文心雕龍研究》(第四 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頁。汪春泓認為,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引用老莊之語,不過是他表達思想的筌蹄而已。劉勰的佛家思想是用中土文獻典故來表達的。劉勰所說的“虛靜”已度越老莊,直臻佛境。劉勰創作論,其主干應是佛學思想,而非《莊》旨。
③王元化:《讀〈文心雕龍〉》,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17頁。在《劉勰的虛靜說》一文指出,劉勰的虛靜說和老莊的虛靜說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個消極一個積極,區別十分明顯。先秦諸子提倡虛靜說的并不止道家。荀子“虛壹而靜”是說:虛則入——心能虛,才能攝取萬物萬理;壹則盡——心能壹,才能窮盡萬物萬理;靜則察——心能靜,才能明察萬物萬理。此說也是作為一種思想活動前的準備手段而提出的,這與劉勰把虛靜作為一種構思前的準備手段并無二致。
④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1頁。文中作者引《莊子》“惟道集虛”以及《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來解釋“陶鈞文思,貴在虛靜”。
⑤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282頁。
⑥引自(梁)蕭統《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26頁。
⑦以上觀點參閱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984頁。
⑧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頁。
⑨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頁。
⑩羅宗強:讀《〈文心雕龍〉手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17~125頁。
11根據《荀子·解蔽》篇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此句意思即:言語是文章中表達情感的關鍵。這與《神思》篇“辭令管其樞機”相印證。
[參考文獻]
[1]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李金松,黃鶯.《文心雕龍》中“虛靜”說之學術淵源考辯——兼同王元化先生商榷[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