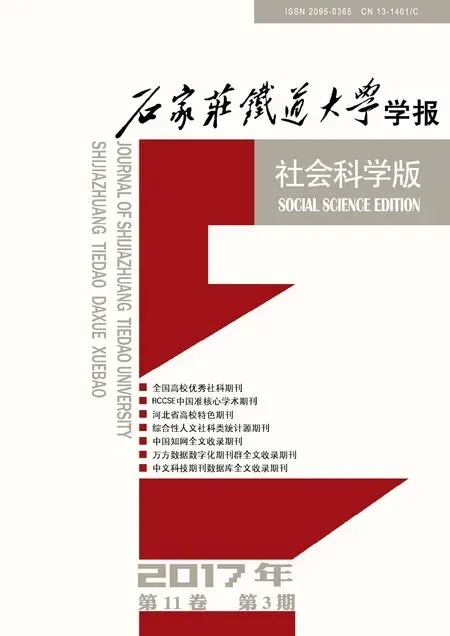基于股利理論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方案改進
陳 平 花
(福建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基于股利理論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方案改進
陳 平 花
(福建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現階段,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存在上繳比例偏低、分紅比例一刀切、同股不同酬等問題,難以實現紅利分配公正化。為此,在借鑒西方股利理論和股利政策基礎上,根據股份制改革進程設計適合我國壟斷企業發展的紅利分配政策。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方案應當結合自身特殊性,對于正在進行或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壟斷企業,應當參照低正常加額外股利政策。對于尚未開始股份制改革的國有獨資企業,應當借鑒剩余股利政策。
股利理論;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
一、文獻綜述
國有壟斷企業是指享受國家特殊政策或資源優勢從而控制社會生產,操縱和獨占市場的企業[1]。長期以來,它們憑借“共和國長子”的身份,以其享有的特殊國家政策或絕對市場優勢獲得大量超額利潤,然而這些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并沒有將這巨額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還利于民,而是通過各種途徑內化為企業高管的在職消費和員工的隱形福利,難免引發社會對國有壟斷企業收入分配制度的強烈不滿,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分配的呼聲甚囂塵上。針對這一問題,2007年,財政部及國資委聯合發布《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的10%利潤上繳比例結束了國有壟斷企業不繳紅利的歷史。時至今日,雖然國有壟斷企業的紅利分配政策已經過多次調整,但這些紅利分配政策的制定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性[2]。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政策缺乏相對科學的依據,并且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近年來,對于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紅利分配成效檢驗以及紅利上繳比例等方面。在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的成效檢驗上,李曉寧指出,資源、資本和消費者剩余的剝奪帶來了國有壟斷企業超額利潤,然而現行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上繳比例低,資源要素低價獲取,國有壟斷企業在自身內部瓜分了本屬于全民的利潤[3]。錢雪松、孔東民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國家參與國有企業利潤分配將改變國企內部人的激勵和行為選擇,有助于緩解國有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問題[4]。劉金偉選取2010年滬深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構建計量模型分析得出國有企業現金分紅能夠有效抑制國企在職消費并且隨著國企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其抑制作用更加明顯[5]。在紅利上繳比例方面,鄭飛認為現行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征繳比例過低,他通過對電力行業紅利上繳比例的估算并綜合各方面利益,提出應當將這一比例提高至40%~60%之間[6]。王永在其博士論文中通過變彈性生產函數模型和半參數變系數估計方法估算國有壟斷行業應該上繳的分紅比例,為國有壟斷企業紅利上繳比例的確定提供方便[7];楊蘭品、陳錫金等指出要在切實保證利潤上繳的基礎上再適度提高上繳比例,完善壟斷行業內國有企業信息披露機制和內部治理結構,提高國有壟斷行業上繳利潤中用于民生的比例[8]。
以上學者基于不同視角研究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為紅利分配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但就具體分配方案的制定來說,現行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政策依然缺乏系統明晰的理論路徑。筆者認為,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方案可以在借鑒西方股利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國有壟斷企業特殊性和市場適用性加以改進。基于此,文章在借鑒西方股利理論的基礎上,對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現狀進行分析并就該項分配方案的改進提出初步構想。
二、西方股利理論與股利政策
隨著西方資本市場的發展,股利理論經歷了從古典股利理論到現代股利理論的演變,并以此為依據形成了四大股利分配政策,為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制度的改革和重構提供了有益的理論依據。
(一)古典股利理論
古典股利理論包括完美資本市場環境下的MM股利無關論以及現實資本市場環境下的“手中鳥”理論和稅差理論。1958年,美國學者莫迪格利尼(Franco Modigliani)和米勒(Mertor Miller)提出的MM理論認為投資者并不關心公司的股利分配,且股利支付比例不影響公司的價值,利益相關者根據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來評價公司價值,而與股利的支付時間和支付形式無關。按照該理論的觀點,企業所指定的股利分紅方案既不會影響企業現金流量,也不會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然而實際上資本市場存在著諸多影響因素,例如交易成本、代理成本等,使得股利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企業市場價值。因此,在MM股利無關論之后,產生了觀點相互沖突的股利政策理論。1962年,麥倫·戈登在威廉姆股票價值股利貼現模型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手中鳥”理論,該理論認為投資者更偏好于現金股利,隨著公司股利支付率的提高,權益價值因此而上升,即所謂的“一鳥在手,強于二鳥在林”。這一理論的假設是股東偏好高的股利支付率。1967年,法拉和塞爾文提出的稅差理論認為如果存在股票的交易成本,甚至當資本利得稅與交易成本之和大于股利收益稅時,偏好取得定期現金股利收益的股東自然會傾向于企業實施高股利政策,該理論的假設基礎是股東偏好較低的股利支付率。
(二)現代股利理論
現代股利政策理論是對古典學派的完善和發展。主要包括信號傳遞理論、代理理論和追隨者效應理論。雖然現代學派的各種觀點在不同程度上還存在一些缺點,但它們改變了傳統理論的思維定式和分析方法,極大地擴展了財務學家的研究視野,從而使股利政策問題研究在“量”和“質”上均產生了很大的飛躍。1977年,美國學者羅斯系統地將不對稱信息理論引入資本結構和股利政策分析中,他假定企業管理當局相對于投資者掌握更多關于企業未來收益和投資風險信息。此時在資本市場中,管理當局所選擇的資本結構和股利政策就是把企業內部信息傳遞給市場的一個信號,投資者只能通過這一信號來評價公司價值并作出投資決策。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經濟學家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發展起來的代理理論認為,企業中的股東、債權人、經理人員等諸多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并非完全一致,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有可能會以犧牲另一方的利益為代價,這種利益沖突關系反映在公司股利分配決策過程中表現為不同形式的代理成本。因此,實施高股利支付率的股利政策有利于降低因經理人員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而引發的自由現金流代理成本。實施多分配少留存的股利政策,既有利于抑制經理人員隨意支配自由現金流的代理成本,也有利于滿足股東取得股利收益的愿望。追隨者效應理論是在古典稅差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認為每個投資者所處的稅收等級不同,他們對股利政策的偏好也會有所不同:收入高的投資者因其擁有較高的稅率表現出偏好低股利支付率,希望少分現金股利或不分現金股利,以更多的留存收益進行再投資,從而提高所持有的股票價格;而收入低的投資者以及享有稅收優惠的養老基金投資者表現出偏好高股利支付率,希望支付較高而且穩定的現金股利。
(三)四大股利政策
根據上述不同股利理論并結合西方企業現狀及其管理目標,西方國家目前主要采用的公司股利政策有以下四種。其一是在MM理論指導下的剩余股利政策,該政策認為當企業存在良好投資機會時,企業稅后利潤應當首先滿足資本預算對資金的需求,其次才考慮向股東不分紅。該政策的優點主要表現在擁有理想的資本結構使得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低,從而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缺點是向投資者發出相互矛盾的信號,股利發放額每年隨投資機會和盈利水平的波動而波動,不利于投資者安排收入與支出。其二是固定股利政策,根據“一鳥在手”理論與“股利信號理論”,企業應當將每年發放的股利固定在某一相對穩定的水平上,并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不變。由于股利支付與公司盈余脫節,在任何情況下,不論盈利多少,均按固定股利發放,該項股利政策一般很難被企業長期的采用,因為當企業資金緊張時卻仍要支付固定的股利,往往導致財務狀況的惡化。但是該項政策也有利于公司樹立良好形象,保持較為穩定的股票價格,增強投資者的信心,便于投資者安排股利收入和支出。其三是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即公司確定一個股利占盈余的比率,長期按此比率支付股利的政策。在股利信號理論看來,公司派發股利往往能夠向投資者傳達其未來發展的信號,采用股利支付率政策會使得股利隨盈余的波動而變動,給投資者帶來投資不穩定的印象,從而影響到公司形象。其四是低正常股利加額外股利政策。在這一政策下,公司每年只支付數額較低的固定股利,在盈余較多時再根據實際情況向股東發放額外股利,但這并不意味著公司將永久地提高股利支付率。這一股利政策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公司可以根據當年的經營狀況決定股利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財務困境,同時也吸引住了那些需要固定股利的股東。需要注意的是,倘若公司長期發放額外股利,突然又由于資金不足而取消固定部分股利時,就會傳遞出公司財務狀況的風險信號,給公司帶來負面影響。
企業紅利分配制度是指企業決定把凈利潤按照一定比例在股東(投資者)與企業之間進行分配的政策安排,這一政策的關鍵問題在于確定企業盈余中紅利發放數量即現金股利支付率的高低。股利政策起源于西方股利理論,主要就是研究股利政策與企業價值之間是否具有相關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合理確定企業的紅利分配方案。經過多年的發展演變,其理論體系已經趨于成熟和完善,不僅有效地指導了西方國家企業股利分配政策的調整和優化,而且也有利于企業治理機制和資本市場的完善。因此,這些理論研究成果及其政策主張,對于同樣處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分配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顯然具有啟示與借鑒價值。
三、 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現狀
(一)紅利分配比例偏低
國有壟斷企業憑借其自身的優勢和地位,每年均可獲得大量超額利潤,因此國家作為壟斷企業重要投資主體,有權利分享企業稅后利潤。自2007年參與壟斷企業稅后利潤分配以來,國有壟斷企業分紅比例經過多次調整,上繳比例由最初的10%到2011年的15%再到2013年的15%~20%甚至到如今的20%~25%,國有壟斷企業收益上繳比例不斷提高。這與過去13年不繳利潤的情況相比雖屬一大進步,但相對于國有壟斷企業總體盈利水平來說,上繳比例依然偏低。據財政部數據顯示,2011—2013年國資委所屬第一類企業凈利潤占中央企業凈利潤比例在79% 以上[9],2014年中央企業累計實現凈利潤6 269.2億元,其中盈利能力排名第一的中國煙草總公司凈利潤為1 649.4億元,占比26.3%[10]。這類企業稅后利潤大部分依靠的是壟斷優勢而非經營業績,其獲取的超額利潤本應該回報社會而不是滯留于企業內部,轉化為高管薪酬或員工收入。而且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國有壟斷企業上繳紅利的比例同樣偏低。例如世界銀行對16個發達經濟體的49 家國有企業分紅比例研究發現,2008年平均分紅比例為30%~45%,其中電信行業分紅比例一直處于高分紅態勢,在2010年之后甚至達到60%的水平[9]。從西方國家來看,法國國有企業上繳50%的利潤給政府,意大利上繳紅利比例為65%,新西蘭和新加坡的分紅比例甚至高達70%[6]。國有壟斷企業分紅比例遠遠不及這些國家分紅水平,25%的分紅比例實屬偏低。
(二)分紅比例一刀切,缺乏合理的科學依據
現行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將國有壟斷企業利潤上繳比例分兩類執行,第一類是中國煙草總公司,其上繳比例為25%;第二類包括石油、電力等壟斷性企業,上繳比例為20%。這一收取辦法雖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中國煙草總公司這一巨型壟斷企業的特殊性,但對于石油、石化等第二類壟斷企業來說,由于日常運營、財務周轉等企業狀況不一,倘若按20%的比例“一刀切”似乎顯得太過隨意,缺乏科學依據。雖然“一刀切”的分配政策有助于壟斷企業紅利征繳統一監管,但是反觀企業個體來說,由于企業經營績效或者收益狀況又或者其所承擔的社會職能不同,采用統一的上繳比例顯然是一種不公平的利潤分配行為。例如中國石化和中國電信同屬于壟斷企業,但中國石化屬于資源兼行政性壟斷企業,不僅享有巨大的壟斷市場而且還擁有豐富的低價資源,從而獲取超額利潤的空間也相對較大,理應相應提高其利潤上繳比例,而中國電信完全屬于行政壟斷型企業,其單一壟斷性質獲取的超額利潤也相對較少,其所上繳的比例似乎應當稍次于中國石化。另外,“一刀切”的分紅比例政策似乎忽略了各企業所特有的資本結構以及發展戰略等財務狀況,使其并不能完全符合現行財務理論中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財目標。對比國際上針對壟斷企業的紅利分配政策政策,他們并不是采用固定劃線的方式確定分紅比例,而是在考慮企業自身特點之后確定的分紅結果。例如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等國家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政策是董事會根據整個商業周期的預期盈利來設定目標分紅率,通常挪威還會不定期地以特別紅利的形式將資本金歸還給國家[11]。新加坡則通過考慮企業現金流來確定國有壟斷企業分紅比例。
(三)紅利分配同股不同酬
“同股同酬”是資本市場亙古不變的原則,但現行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卻呈現“同股不同酬”的現象,這主要體現在國有股東和非國有股東所獲得的分紅比例不一致。就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來看,中國國有壟斷行業內的上市公司在國內不繳利潤的時候,在國外卻是以很高的比例分紅。早在2005年,世界銀行指出,中國石化在美國資本市場中的分紅比例達到25%,中國石油為31%,華能電力分紅比例甚至高達57%[6]。而在2008年在國內開始按一定比例上繳紅利之后,國外的分紅比例卻已經遠遠高出國內的10%、15%甚至更多。據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年報獲悉,2012年在美國上市的國有壟斷企業的分紅率均在30%以上,中國移動非國有股東的分紅率達到52.8%[9],而此時國內上繳比例僅為15%,這“同股不同酬”的現象完全違背了市場經濟原則。另外,據世界銀行對我國H股市場的172家國有企業研究顯示,國有企業分紅比例的平均值為23.2%,中值為22.7%[12],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國內壟斷企業對于非國有股東的分紅比例高于其上繳比例,壟斷企業分紅沒有體現“同股同酬”的原則。
四、 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制度的方案改進
鑒于上述國有壟斷企業分紅比例低、分紅“一刀切”以及同股不同酬等問題,客觀分配企業盈余以及確定合理的分紅比例已經成為方案設計的重點。近年來,國有壟斷企業已經基本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的經濟實體,其分紅制度的建立可充分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股利政策的實踐和股利理論研究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我國國有壟斷企業具有盈利性和公共性的雙重目標,在滿足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基礎上承擔著社會公共服務的責任,從這一點上講,投資者(國家)更為關心的是企業經營績效,即企業對于國家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國家根據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來評價公司價值,因此它并不關心公司的股利分配,即股利支付比例不影響公司的價值,此時,根據剩余股利政策原則設計企業的紅利分配方案似乎更為科學。另一方面,隨著股份制改革的推進,壟斷企業最為微觀經濟個體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地位日益凸顯,同時為滿足更廣大投資者的利益,其盈利性的職能也日趨重要。因此壟斷企業應當扮演起現代企業的角色,充分考慮市場經濟中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此時,所謂的信號傳遞理論、手中之鳥理論以及委托代理理論的思想均符合預期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在這一情況下,采用低正常加額外股利政策的原則來設計壟斷企業分紅方案更為恰當。綜合上述分析,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筆者認為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制度應當以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根據股份制改革進程的不同,分類設計企業紅利分配方案,在考慮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的基礎上確定合理的紅利發放數量,同時兼顧企業資本效率。另外由于各壟斷企業經營狀況千差萬別,紅利分配政策應當具體到每一企業根據企業發展規模、盈利能力,治理目標等分行業分階段分類型的確定紅利分配方案,而非簡單的“一刀切”。例如按照國家控股狀況,對于國有獨資、國有控股或者國有參股企業分別制定相應的分配政策,更進一步應當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根據企業自身發展狀況確定合理分紅比例。由于壟斷企業股份制改革的進程不同,其紅利分配改進方案也就有所區別,具體改進方案初步構想如下:
(一)對于進行或完成股份制改革的企業參照低正常加額外股利政策
對于正在進行或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壟斷企業,國家股跟普通股處于同等地位,其紅利分配政策應當按照“同股同酬”的原則經股東大會表決通過。由于企業紅利分配問題涉及企業投融資問題,在具體方案設計時應充分考慮企業的資本成本及融資結構。然而目前壟斷企業經營者對企業資本成本的理解并不全面,他們普遍只考慮外部債權資本成本而忽視留存收益作為自有資金的資本成本,這必然導致了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偏低,充裕的利潤留存使得企業普遍存在過度投資行為。因此企業在設計紅利分配方案時既要考慮內外部融資比例的協調又要防止經理人盲目投資導致資本運營效率低下。低正常加額外股利政策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公司可以根據當年經營狀況決定股利的高低,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企業財務困境,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自由現金流量,減少經理人過度投資的行為。借鑒低正常股利加額外股利的思想,股份制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首先要考慮向股東支付固定股息,然后視企業的經營發展狀況適當參與剩余利潤分配,因此國有壟斷企業所上繳的紅利=固定股息+額外紅利。公式中,固定股息是由國有資本占有量以及固定股息率乘積確定,國有資本占有量即壟斷企業資產負債表中歸屬于國家股東權益的份額,固定股息率采用企業資本成本替代,原因在于資本成本是企業投融資決策中必須嚴格遵守的報酬率水平最低界限,同時又是投資者所要求的最低報酬率,能夠較好的協調企業與股東雙方利益。額外紅利的多少則視企業發展狀況而定:對處于相對劣勢而又要重點扶持發展的企業可以收取較低的額外紅利;對那些盈利能力強,政府又想要逐步退出的企業則收取較高的額外紅利。這樣一來,不僅保證了包括國家股東在內的全體股東基本權益而且又照顧到發展過程中盈利相對不佳的壟斷企業,緩解了分紅比例“一刀切”的現象,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分配方案。
(二)對于尚未開始股份制改革的國有獨資企業借鑒剩余股利政策
盡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進程不斷加快,國有壟斷企業中仍存在一些尚未開始股份制改革的國有獨資企業,這類企業的紅利分配方案應當參照剩余股利政策,然后隨著股份制改革的推進慢慢過渡到“低正常加額外股利”分配方式。國有獨資企業的存在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并且以國家為股東的優勢使得企業資金來源渠道穩定,因此,這類企業的股利政策不會對企業現金流量產生直接影響, 股利政策作為企業融資結構的影響因素并不改變企業的市場價值。另外,這部分企業大多屬于國資委完全控制的國家行政性壟斷企業,其紅利分配更多的是紅利上繳問題,國家作為企業唯一投資者使得這一類型企業的紅利分配方案相對簡單,無需涉及少數股東權益問題。因此,為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 企業應根據依據剩余股利的原則制定企業紅利分配方案。借鑒這一思路,企業必須在年初編制資本預算,確定一個適合企業發展的“目標資本結構”,然后根據這一資本結構確定企業所需留存資金,余額全部上繳。在剩余股利政策指導下,企業必須考慮投資機會和資本成本這兩個重要因素,其中投資機會主要是指企業可獲得收益的投資項目,而資本成本的考慮不只是股權資本成本還包括其債務資本成本即所謂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當企業存在投資機會時,企業應當根據資本成本將企業的稅后利潤按目標資本結構比例留存后進行再投資。當然采用剩余股利原則最大的缺陷就是股利發放額每年隨投資機會和盈利水平的波動而波動,其所傳遞出相互矛盾的信號不利于吸引特定股東,這是影響企業融資的關鍵因素。我國國有壟斷企業股份流動性差,既不存在有效的公司控制權市場[13],也不存在“用腳投票”的股東,使得這類企業不必擔心支付不固定的股利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因此具有獨資形式的國有壟斷企業似乎根本不存在由于少分或者不分股利而撤資的情形,參照剩余股利政策來確定其紅利上繳比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1]賴 虹.我國國有壟斷企業第三類代理成本問題探討[D].南昌:江西財經大學,2013.
[2]喬 麗.國有企業紅利分配政策缺陷與改進[J].石家莊鐵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9(4):10-16.
[3]李曉寧. 國有壟斷與所有者缺位:壟斷行業高收入的成因與改革思路[J].經濟體制改革,2008(1):54-57.
[4]錢雪松,孔東民.內部人控制、國企分紅機制安排與政府收入[J].經濟評論,2012(6):15-24.
[5]劉金偉.內部人控制、現金分紅與國企在職消費[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2(2):38-45.
[6]鄭 飛.中國國有壟斷性行業利潤分配研究[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12.
[7]王 永.我國國有壟斷行業收入分配機制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3.
[8]楊蘭品,陳錫金.國有壟斷行業要素收入分配的結構性偏差[J].經濟評論,2015(2):101-114.
[9] 王哲琦.國有壟斷行業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改革障礙及調整對策[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4(1):29-33.
[10]2014年央企利潤排行榜 煙草總公司秒殺中石油[EB/OL].(2015-03-27).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5814.
[11]趙惠萍.國有資本收益分配機制研究[D].天津:天津財經大學,2013.
[12]有效約束、充分自主:中國國有企業分紅政策進一步改革的方向[EB/OL].(2009-11-17).http://documents.world bank.org/curated/en/963631468011136 270/pdf/532540ESW0CHIN00final0Nov27020090Ch.pdf
[13]陳 艷.現代股利理論對國有企業分紅制度的啟示[J].財會通訊,2007(9):73-75.
TheImprovementofDividendDistributionSchemeofState-ownedMonopolyEnterprisesBasedonDividendTheory
Chen Pinghua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China)
At present, there exist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dividend distribution of state-owned monopoly enterprises, for example, the low turning-over rate, the one size fits all proportion of dividends, the discrimination in the income of same share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realize fair distribution of dividends. To this end, it is needed to learn from the Western dividend theory and dividend policy so as to design the dividend policy for China’s monopoly enterpris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se of reform of the joint stock syste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onopoly enterprise dividend allocation schem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its own particularity, and the monopoly enterprise which is carrying out or completes the share reform should refer to the low normal plus extra dividend policy. As fo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have not yet started the shareholding reform, the residual dividend policy could be applied.
dividend theory; state-owned monopoly enterprise; dividend distribution
2095-0365(2017)03-0014-06
2017-04-25
陳平花(1992-),女,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業經營預算。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 (14AGL007)
F276.1
:A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7.03.03
本文信息:陳平花.基于股利理論的國有壟斷企業紅利分配方案改進 [J].石家莊鐵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1(3):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