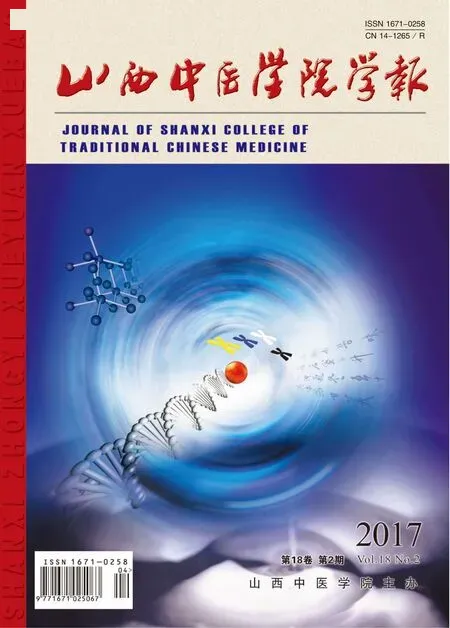《續名醫類案》誤用大柴胡湯醫案一則疑析
謝永貴,李瑞艷,馮 明
(山西中醫學院,山西太原030024)
《續名醫類案》誤用大柴胡湯醫案一則疑析
謝永貴,李瑞艷,馮 明
(山西中醫學院,山西太原030024)
Analysis of a medical record of Dachaihu decoction in Xu Mingyi Lei′an
閱讀古代醫案是每個中醫從業者提升臨床思維和療效的重要途徑,通過試析《續名醫類案》醫案一則,得出其誤用大柴胡湯之結論,旨在說明閱讀古代醫案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古文功底,還應于字句、方證間細細品味,切忌泛讀而過,方可讀出味道。
續名醫類案;大柴胡湯;醫案
《續名醫類案》一則醫案:“孫文垣治張二官,發熱頭痛,口渴,大便秘結三日未行,脈洪大,曰∶此陽明少陽二經之癥。用大柴胡湯行三五次,所下皆黑糞,夜出臭汗。次日清爽,惟額上(陽明部位)仍熱,用白虎湯加葛根、天花粉。因食粥太早,復發熱咳嗽,口渴殊甚,且惡心(食復),用小柴胡加枳實、山梔、麥芽。次日渴不可當(半夏、枳實、麥芽,皆能耗陽明津液),改以白虎湯加麥冬、花粉,外與辰砂益元散,以井水調服五錢,熱始退,渴始定。不虞夜睡失蓋,復受寒邪,天明又大發熱,人事不知(復感),急用小柴胡湯加升麻、葛根、前胡、薄荷。汗出熱退,神思大瘁,四肢皆冷,語言懶倦且咳嗽,以生脈散加石斛、百合、大棗、白芍。服后咳嗽尋止,精神日加,飲食進而愈。”[1]
對于一診,大部分學者可能會類此解析:“發熱,口渴,大便秘結三日未行”乃陽明腑證,但脈不應洪大;“發熱、口渴、脈洪大”是有陽明經證,但不應大便秘結。那到底是陽明腑證還是陽明經證呢?有點矛盾,可從少陽解,從和解的基礎上用下法,故曰此陽明少陽二經之癥。
筆者認為,既然同時有陽明腑證和陽明經證,為何不能用承氣類方合白虎湯呢?一定要從少陽和解通下?何況,此處并無少陽病八大癥之任何一癥,安可亂用柴胡類方?此一診用大柴胡湯恐屬誤用,治療法當清熱生津、少佐通腑,方用白虎湯合調胃承氣湯,分析如下。
1 癥狀用藥析疑
無汗可用白虎耶?名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所論頗佳:“仲圣當日未見有汗即用白虎湯,此不又顯與經旨相背乎?石膏原有發表之性,其汗不出者,不正可借以發其汗乎?”[2]他根據自己的臨床應用經驗,提出“若陽明之實熱,一半在經,一半在府,或其熱雖入府而猶連于經,服白虎湯后,大抵皆能出汗。”[3]
脈洪大可用大黃否?引用許叔微《傷寒九十論》一則醫論作答:“昔后周姚僧垣名善醫……及至元帝有疾,諸醫者為至尊至貴,不可輕服,宜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大而實,必有宿食,不用大黃,病不能除。上從之,果下宿食而愈。”[4]
故依名家用方藥經驗,此一診用藥不可斷然否定白虎湯和大黃。
2 從醫案編排、字句處分析
查閱《續名醫類案》原文發現,這則醫案之前還有另一則醫案和其并在一段:“沈天祿病傷寒,汗下后病不解,身無大熱,不惺惺,醫者但云譫語。以癥論之,乃錯語也(譫語錯語,極宜細辨)。緣汗下之后,元氣未復,神識不清耳。與補中益氣湯去升、柴,加麥冬、生地、熟附子,一服而愈。孫文垣治張二官,發熱頭痛……”
很明顯第一個醫案乃是用汗下法的誤治,那其汗下法用的是哪個方呢?其行文緊接著便是我們討論的醫案,作者有意把這兩則醫案編排在一起,我們有理由相信,其汗下法很有可能用的就是大柴胡湯,而第二則醫案所用大柴胡湯也非最佳之方!故陳述“此陽明少陽二經之癥”時,編者用了“曰”一字,“陽明少陽二經之癥”是孫文垣說的,并不代表編者的意見。若編者贊同,他不會借此手法而不明言。如第一則醫案的“以癥論之,乃錯語也”,這樣的陳述才是編者的意見。注家王孟英在此未作批示,不過從后文“半夏、枳實、麥芽,皆能耗陽明津液”,可以推測出他不甚贊同用大柴胡湯。
3 從“食復”的前因后果分析
一診用大柴胡湯后,“所下皆黑糞,夜出臭汗。次日清爽,惟額上仍熱,用白虎湯加葛根、天花粉”。似乎用大柴胡湯是對的,只是尚留有余邪未清。醫者也認識到汗、下后,病邪已去,但津液已傷,當用清熱生津養陰之劑善后。后“因食粥太早,復發熱咳嗽,口渴殊甚,且惡心(食復)”。
食復,是分析這則病案的關鍵點。因食粥太早導致食復,是怎樣的太早呢?此食復當因病后津液已傷,胃氣、胃陰不足,無力消化糜爛食物,而再傷胃陰致口渴、發熱,食不化則滯,胃不運降則惡心,升降失常、邪熱擾肺則咳嗽,所以此“太早”應是病者還未服用白虎湯加葛根、天花粉以生津去余邪,就先食粥了。如此,似乎只能怪病家運氣不好。但,有道是: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
設想一下,如果一診時就用清熱生津佐通腑之法,邪去津存,還會發生食復嗎?應該是不會的,并且不會有“額上仍熱”之余癥。當然,前提是病人不大吃特吃。也許有人不同意這種推測,是的,畢竟時光不可能倒流,病情不可能重演,但我們至少可以相信概率較小吧?這個是可以確定的。
4 分析大柴胡湯在一診時的作用
大柴胡湯由柴胡、黃芩、芍藥、半夏、枳實、生姜、大棗、大黃組成,沒有一味藥可以生津。大棗在脾胃運化正常的情況下可補胃陰,但在陽明熱盛傷津、便秘的情況下,反而滋膩礙胃、壅補助熱。大黃、枳實、芍藥致“行三五次,所下皆黑糞”,得以通腑去熱;柴胡、黃芩和解表里,和姜棗一起致“夜出臭汗”,然亦有強責其汗之嫌。況生姜助熱傷津,柴胡劫肝陰,黃芩苦寒傷陰,且有學者認為白虎湯加上三黃(黃連、黃芩、黃柏)即為死虎,本應順勢而為清熱透熱,卻用三黃苦寒直降,與病勢相違。半夏、枳實耗陽明津液(王孟英注)。不難看出,大柴胡湯的確不是最佳之方。
5 查閱白虎合承氣湯史據
查閱相關書籍發現,確有白虎合承氣湯一法,出自俞根初的《重訂通俗傷寒論》:“白虎承氣湯清下胃腑熱結法,俞氏經驗方:生石膏八錢(細研)、生錦紋二錢、生甘草八分、白知母四錢、元明粉二錢、陳倉米三錢(荷葉包)。何秀山按:胃之支脈,上絡心腦,一有邪火壅閉,即堵其神明出入之竅,故昏不識人,譫語發狂,大熱大煩,大渴大汗,大便燥結,小便赤澀等癥俱見。是方白虎合調胃承氣,一清胃經之燥熱,一清胃腑之實火,此為胃火熾盛,液燥便閉之良方。”[4]可見,一診癥狀與何氏所按的白虎承氣湯證輕重有別,但法理無異,處方應作劑量調整。
綜上,嚴格來說,一診用大柴胡湯屬誤用,白虎湯合調胃承氣湯方是正治。另外,從“不虞夜睡失蓋,復受寒邪,天明又大發熱,人事不知(復感),急用小柴胡湯加升麻、葛根、前胡、薄荷。汗出熱退,神思大瘁,四肢皆冷,語言懶倦且咳嗽,以生脈散加石斛、百合、大棗、白芍。服后咳嗽尋止,精神日加,飲食進而愈”可看出,此孫醫生用大隊風藥治外感熱病,再次使病人耗氣傷陰。其不明病人氣陰虧損,豈可濫用升散風藥、強發其汗?難道治發熱只有柴胡類方可用?此乃偏執傷寒經方之故也!
此次受寒復感,法應補虛托邪,當仿九味羌活湯之意,或者用東垣的麻黃人參芍藥湯(人參、麥冬、桂枝、當歸身、麻黃、炙甘草、芍藥、黃芪、五味子),或者用景岳理陰煎(熟地、當歸、炙甘草、干姜)之法,辨證加減治療。此醫案收錄至此書的“傷寒類”門下,似乎是在無聲地謹告讀者:為醫者,辨證不可不為細致,醫術不可不博聞廣學也!
[1]江瓘,魏之琇.名醫類案正續編[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2013:280.
[2]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580,582.
[3]許叔微.許叔微傷寒論著三種[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148.
[4]俞根初.重訂通俗傷寒論[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1:66.
(編輯:梁葆朱)
R249
A
1671-0258(2017)02-0007-02
謝永貴,在讀碩士,E-mail:xieyg2010@foxmail.com
馮明,教授,主任醫師,E-mail:1583405987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