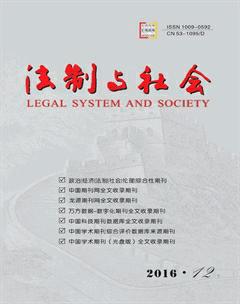淺談實現(xiàn)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良性互動
秦燕婷
摘要 本文立足于民法與市民社會的關(guān)系,試圖探求在實現(xiàn)國家與市民社會良性互動的努力中民法的正確定位和積極作用。市民社會是一定獨立于國家的一種制衡力量,而其自身的缺陷有要求國家對其有一定的協(xié)調(diào)和影響,如何實現(xiàn)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這種良性互動關(guān)鍵點就在于民法作為一個較中性的第三方對于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界限劃分以及對雙方影響時的緩沖和協(xié)調(diào)作用。同時針對中國特殊國情,提出一些民法和市民社會在中國所面臨的困難與誤區(qū)。
關(guān)鍵詞 民法 市民社會 國家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j.cnki.1009-0592.2016.12.282
一、市民社會與市民概述
“市民社會”(Soeietas civils),不僅指“單一國家,而且也指業(yè)已發(fā)達到出現(xiàn)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體的生活狀況。這些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禮儀和都市特性(野蠻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屬于市民社會)、市民合作及一句民法生活并受其調(diào)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業(yè)藝術(shù)的優(yōu)雅情致。”
市民社會概念發(fā)展來看,第一次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civilsociety,指的是“城邦”,但是城邦,相對于城市,更傾向于是一個政治的概念。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市民社會,強調(diào)的是古希臘城邦的民主社會,是在一種在古希臘政治與經(jīng)濟高度交融的情況下,市民社會和國家也相互交融的表現(xiàn)。在近代,市民社會在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中與“自然狀態(tài)”相互對應,到后來發(fā)展到“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相區(qū)別,我們可以看到就算是與“自然社會”對應時的“市民社會”,它也并非今天我們所講的給予市民以自由選擇的權(quán)利來發(fā)展培養(yǎng)他們的自治能力的市民社會,而是與自然狀態(tài)相對的政治社會或者國家。而發(fā)展到后來的“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才慢慢明晰私的領(lǐng)域與公的領(lǐng)域的區(qū)別。
這里我們所講市民社會里的市民二字,應當是與公領(lǐng)域的公民身份相互對應的私領(lǐng)域的代表個人利益的市民身份。有些學者認為市民二字是由于市民社會是基于市場經(jīng)濟而產(chǎn)生的,但是我認為將市民,市民社會局限在一個純粹經(jīng)濟的領(lǐng)域是不妥當?shù)模颂幍氖忻裆鐣吹箍衫斫鉃槌鞘兄瘢@里的城市不是狹義上的城市,而指的是地區(qū)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孕育出的經(jīng)濟、文化、思想等較為完備的社會,一種“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包括了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lǐng)域。”這種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不僅僅局限于商品交換與經(jīng)濟交往,也包括思想文化,情感聯(lián)系等多個方面;不僅僅局限于人們的財產(chǎn)關(guān)系,也應同樣涉及到人們的人身關(guān)系。
二、國家與市民社會在發(fā)展中的分離與互動
在商品交換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過程中,市民社會作為一個私的領(lǐng)域,體現(xiàn)的是一種權(quán)利本位思想,將保護市民的權(quán)利,特別是市民的自由,作為社會的追求。這種對自由的倡導和對權(quán)利的保護,要求市民具有獨立平等的主體地位,能根據(jù)利益權(quán)衡做出自由選擇,有人認為這種公權(quán)力(國家)在私領(lǐng)域的退出,給予市民以自由選擇的可能性是培養(yǎng)市民的自律自治的必然途徑,的確這種給予的自由對培養(yǎng)市民的選擇能力,責任義務意識等有重要作用。人類自身的貪欲和自私,也可以因為市民社會運作的需要達成的基本合意進行一定的彌補。
但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市民社會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一是缺少一種確定的、眾所周知的法律。二是缺少一個按照既定法律來裁判一切爭端的公允的裁判者。三是缺少權(quán)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為了彌補這些缺陷,我們需要國家能夠?qū)κ忻裆鐣倪\作有一定的影響力,即國家不能完全退出私領(lǐng)域。如果只是一味地給予自由,所謂滿足自己私利的同時也滿足他們需要的理論還是一個理想狀態(tài),當自利與他利無法達到合意,或者自利與公益產(chǎn)生沖突的時候,市民社會內(nèi)部是無法自我消化和解決的,因為市民社會的正義來自于其多樣性,而其隱藏的可能的沖突和矛盾也在于其多樣性,主體的多樣性導致其利益訴求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無法調(diào)和的情境,就是國家需要影響市民社會的情境。但是市民社會的存在意義也正在于此,即多樣性對抗國家所具有的單一性,以經(jīng)濟為力量去影響政治,使得自我的利益在政治和國家決策中得以一定的體現(xiàn)和保障。公共權(quán)力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它總是在尋求機遇擴大對自治的影響。“一切有權(quán)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quán)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jīng)驗。”而市民社會則是防止國家公權(quán)力濫用的一大制衡力量。
三、民法與市民社會的辯證關(guān)系以及對良性互動的促進作用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需求的體現(xiàn),市民社會是民法的基礎(chǔ)
“民法”一次來源于羅馬法的市民法,為與萬民法相對立的體系,后經(jīng)最高裁判官的作用,兩者融合。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由三個部分組成:
1.需求的體系——市場經(jīng)濟。
2.多元的體系——自愿組織(同業(yè)公會)。
3.司法的體系——警察和司法機構(gòu)。他認為市民社會中,人們追求私利的自由與追求私利的可能,雖說關(guān)心自己的得失,但是卻滿足了彼此相互的需求,新的社會紐帶,相互依賴。
而市民社會與國家進行分離和交融的拉鋸中,一直存在的兩大需求是:
一是保護權(quán)利自由,國家權(quán)力的干預限制。二是解決糾紛沖突,減少追求私利時個體之間的相互權(quán)益侵害。民法正是響應市民社會需求的司法體系的一部分,對平等主體的基本權(quán)益進行合理保護,當自我私權(quán)利與他人私權(quán)利產(chǎn)生沖突,發(fā)生糾紛的時候,規(guī)定國家進行恰當?shù)母深A和調(diào)和以維系市民社會基本的運作有序,以國家權(quán)力,司法標準來彌補了市民社會由于其市場經(jīng)濟的基礎(chǔ)導致的追求私利性和權(quán)利自由的不穩(wěn)定性。而民法得以誕生,正是因為市民社會的延續(xù)過程中,產(chǎn)生了這種需求,民法是應市民社會需求而生,市民社會是它的基礎(chǔ),它體現(xiàn)市民社會的需求。
(二)民法作為市民社會與國家互動的媒介,對良性互動的促進作用
民法作為一種私法,是市民社會的基礎(chǔ)——商品經(jīng)濟在法律上的體現(xiàn)。它是出于國家與市民社會分界線上的法律,劃分了市民社會不可被國家所干預的私領(lǐng)域和國家有調(diào)和可能性市民社會領(lǐng)域。這種劃分與分離式市民社會和國家的基礎(chǔ),只有國家和市民社會有各自的獨立性和平等地位,他們之間才能有產(chǎn)生良性互動的可能。在國家決策中體現(xiàn)市民合理利益,以公德給予市民社會以一定的協(xié)調(diào),這些良性互動的前提就是民法對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合理劃分。
民法在充分尊重主體意思自治的情況下,通過權(quán)利和義務的配置,保障市民社會內(nèi)部的權(quán)利自由,并對這種自由可以產(chǎn)生市民的一定自治抱有合理期待,這種對于市民社會內(nèi)部權(quán)益合理保護使得市民社會可以更好地對國家權(quán)力的擴張性、腐蝕性和破壞性存在一定抑制作用。而民法同時也是社會公德與國家權(quán)力需求的一定反應,防止私欲膨脹侵害社會公共利益和自由被濫用使社會陷入無序狀態(tài)。
四、當今中國民法與市民社會面臨的問題及存在的誤區(qū)
(一)中國的特殊國情
中國最主要面臨的特殊狀況主要有:
1.獲得、維護和拓展的空間的過程中,中國社會或者個人及社團表現(xiàn)出的對國家的依附性和相對的脆弱性(非私人資本的驅(qū)動)。
2.國家通過變革體制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其原有的“全權(quán)性”,推動了市民社會的出現(xiàn)。
3.無法忽視的中國以親情血緣為基礎(chǔ)的文化網(wǎng)絡(luò)至于整合中國市民社會的影響。
(二)民法經(jīng)濟純化的誤區(qū)
有些學者把民法的共性概括為商品經(jīng)濟,堅持將與商品經(jīng)濟無關(guān)的傳統(tǒng)市民法內(nèi)容(如親屬)排除出民法的外延,追求民法體系在商品經(jīng)濟基礎(chǔ)上的純化。我認為這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觀點,固然商品經(jīng)濟是民法的一個重要社會基礎(chǔ),但是我們無法忽視在民法體系中,如《婚姻法》等部門法中常保障的是社會生活中無關(guān)經(jīng)濟部分的權(quán)益。市民作為一個城市之民,其權(quán)益不僅僅是經(jīng)濟方面的,民法經(jīng)濟純化并不可為。
(三)農(nóng)民在民法以及市民社會中面臨的困境
市民社會的一大自治基礎(chǔ)就是契約原則,但是中國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社會,自然經(jīng)濟呈現(xiàn)的是自給自足的特點,沒有商品經(jīng)濟中人與人之間平等自由的根據(jù)契約進行商品的交換的過程。自然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社會)中的平衡的協(xié)調(diào)是在家庭或者個人的循環(huán)里進行的,在家庭甚至個人的循環(huán)過程中的權(quán)利意識和責任意識與商品經(jīng)濟為基礎(chǔ)的市民社會也不同。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農(nóng)村社會開始出現(xiàn)農(nóng)村宅基地抵押等農(nóng)業(yè)社會市場化的趨向,農(nóng)民在市民社會中的地位和權(quán)利保障將會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四)社會主義與市民社會
有人說市民社會發(fā)展的是資本主義,這是對于市民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的誤解。市民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chǔ)是商品經(jīng)濟而非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作為一種中性的經(jīng)濟體系,不存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不應因這種疑慮而回避市民社會,不進行市民社會的發(fā)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