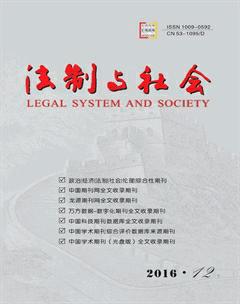淺析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的一事不再理問題
謝地 邵俊彥
摘要 根據(jù)《擔保法》第18條及其司法解釋第20條的規(guī)定,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的債權人可以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時,同時或分別向債務人與保證人請求清償全部債務。但是在審判實踐中,存在著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限制債權人先后分別起訴債務人與保證人的做法。這類做法通常以“訴訟標的相同”或“案件事實相同”為理由,認為債權人先行起訴債務人或部分保證人并獲得判決書后,再起訴剩余債務人或保證人的行為構成重復起訴。本文以《擔保法》與《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為出發(fā)點,運用債法與民事訴訟法相關理論及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意見,認為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的債權人有權先后分別起訴債務人與保證人,對此的否定意見沒有實體法與程序法根據(jù)。
關鍵詞 連帶之債 多數(shù)之債 一事不再理 債的標的
中圖分類號:D923.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305
一、問題的提出
根據(jù)《擔保法》第18條的規(guī)定,連帶責任保證的債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后保證期間內,既可以同時起訴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也可以先向個別債務人或保證人追索債務。《擔保法》第18條沒有規(guī)定債權人分別起訴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的順序。《民事訴訟法》第66條也沒有強制要求審理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的法院通知未被原告起訴的保證人或被保證人到庭參加訴訟。然而在部分省市的司法實踐中,連帶保證債務發(fā)生違約后,債權人僅起訴債務人或部分保證人并獲得一審勝訴判決書后,即使沒能就全部債務得到清償,債權人也可能面臨不能再起訴剩余保證人或債務人清償債務的風險。這個問題在“華律網(wǎng)”等法律咨詢網(wǎng)站及律師個人網(wǎng)頁上并不鮮見:連帶擔保中,債權人在起訴時未將其中一個或數(shù)個連帶保證人列為被告,判決后能否另行起訴?債權人首次提起訴訟時未起訴其他連帶保證人,是否視為放棄擔保權?債權人與一名保證人的訴訟判決后,另行起訴其他連帶保證人,是否構成一事不再理?關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一致。
(一)否定說
持此觀點的人們認為,根據(jù)我國《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債權人必須同時起訴債權人和連帶保證人,一事不再理原則禁止法院先后開庭審理連帶保證合同糾紛中的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
1.訴訟標的相同說:
一種觀點認為:保證合同是從屬合同,是為了實現(xiàn)債權人的債權而設立的,它與主債權是一個整體。主合同無效時,保證合同必然無效。因此,連帶保證合同糾紛實際上是圍繞主債務的一個訴訟,無論債權人向主債務人還是保證人主張債權,對債權人而言,都屬同一訴訟請求。保證人與債務人對同—債務承擔同時履行義務,構成不可分之債。債權人起訴連帶保證人并勝訴后,以同一筆債務未得到清償為由起訴債務人,構成重復起訴,法院應當適用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
從民事訴訟的效率和司法執(zhí)行便利的角度來看,連帶責任保證債務的債權人就同一筆債務先后分別起訴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并都獲得勝訴判決,一方面就一個債務關系產生了多起訴訟,加劇了訟累;另一方面,兩份生效判決中被告均對同樣金額的債務負有清償責任,可能導致重復執(zhí)行。
2.案件事實相同說: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連帶責任保證中,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基于不同的原因事實產生債務關系。債權人先依據(jù)保證合同將連帶保證人訴至法院勝訴后,又依據(jù)借款合同將債務人訴至法院,雖然兩個訴中當事人不同,訴訟標的也不同,但案件事實相同,同樣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二)肯定說
一種觀點認為,債務人和保證人的連帶責任基于不同的發(fā)生原因,屬于不真正連帶責任: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訴訟標的的法律性質由借款合同確定的,而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的訴訟標的的法律性質是由二者之間的保證合同確定的,因此訴訟標的不同;借款合同與保證合同不是同一類型的合同,因此兩份合同產生的訴訟標的所具有的法律性質也不屬同一種類。由于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均對主債務未清償?shù)牟糠殖袚B帶責任,二者之間存在共同的利益關系。因此,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之間的關系并非必要共同訴訟人,而是互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既可以一并參加訴訟,也可以分別先后起訴。
也有人指出,債權人分別起訴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時,前訴與后訴的案件事實不同。連帶保證人提供的擔保是合法有效的且是連帶責任保證,當債權人起訴債務人或其他連帶保證人勝訴但未獲得清償,并在擔保時效內向剩余連帶保證人主張的權利時,債權人向后訴中連帶保證人主張的是“要求其就先訴中債務人或其他連帶保證人未能就債權人的債權全部償還所承擔的補充擔保責任”。
至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各方關于“債權人是否可以先后分別起訴債務人與部分連帶保證人”這一問題產生的分歧,主要在于先訴與后訴的訴訟標的與案件事實是否相同。
筆者認為,以“訴訟標的相同”與“案件事實”相同為由,剝奪債權人分別先后起訴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的權利,沒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依據(jù),既不符合《民通意見》、《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的明文規(guī)定,也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中“一事不再理”的適用條件。
二、連帶保證合同糾紛中的訴訟標的
通說認為,在《擔保法》第18條所規(guī)定的連帶責任保證中,債務人與保證人之間處于連帶債務關系。連帶債務的債權人可以向任何一名債務人主張清償全部債務。然而上述“否定說”觀點認為,連帶責任保證屬于我國民事法律中沒有規(guī)定的“不可分之債”,債權人、債務人、保證人之間只有一個債的標的,也僅有一個訴訟標的。
筆者認為:一是連帶責任保證是單純的連帶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和每名連帶保證人之間,均存在獨立的訴訟標的;二是連帶責任保證不屬于“不可分之債”,且“不可分之債”的訴訟標的判斷標準與連帶之債相同。
(一)債務關系中的訴訟標的
債務關系中存在債的標的,它在德國民法中稱債之內容,在日本民法中稱債之目的。債的標的在性質上與數(shù)量上和訴訟標的完全無關。“否定說”以債務人與保證人均擁有同一債的標的為由,認為債權人分別起訴債務人與保證人時訴訟標的相同,混淆了債的標的與訴訟標的。
債權的內容表現(xiàn)為債權人有權向債務人請求為或不為特定行為,債務人有義務為特定行為或不為特定行為。所謂特定行為,是指給付。因此,債權內容主要是請求權,債權的客體為給付。這種請求權的來源,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依據(jù)民事實體法產生的給付法律關系。《合同法》第107條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xù)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給付之債中,給付行為是債的標的,它客觀上表現(xiàn)為債之標的物的移轉。在貨物買賣合同中,債的標的為買方應支付的貨款與賣方應交付的貨物;在借貸合同中,債務人的債的標的是作為貸款人應償還的本金與利息。
訴訟標的,指當事人訟爭的內容,是法院審理和裁判的對象,也稱作“訴訟對象”。我國通說認為,訴訟標的是“原告請求法院通過審判加以保護的法律關系和實體權利”。在民事訴訟中,涉及實體法的不同規(guī)定,法院要作出不同的裁判,其訴訟標的也就不同,因此有不同種類的訴。具體某一案件,以何法律關系為訴的標的,應以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所表明的意思而定,即應以請求人民法院裁判的事項而定。因此,給付之債中,當事人享有的實體請求權直接作為訴訟標的。
因此,在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債的標的固然是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主債務,各保證人與債務人一同對主債務負全額履行的連帶責任。但該糾紛中的訴訟標的,則是以我國《民法通則》第87條、《擔保法》第18條以及《合同法》第107條為基礎的實體法律關系。
(二)連帶債務的訴訟標的
連帶債務,是以同一給付為標的,依當事人之明示或法律之規(guī)定,各債務人間發(fā)生連帶關系的復數(shù)主體之債務。無論是從債的當事人數(shù)量出發(fā),還是從債之關系的數(shù)量來看,連帶債務都是多數(shù)主體之債。按照我國臺灣地區(qū)、日本、德國的民事法律中對連帶債務的規(guī)定,債權人依法享有先后、逐次分別起訴各連帶債務人的權利。我國《民法通則》第87條規(guī)定:債權人或者債務人一方人數(shù)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或者當事人的約定,享有連帶權利的每個債權人,都有權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負有連帶義務的每個債務人,都負有清償全部債務的義務,履行了義務的人,有權要求其他負有連帶義務的人償付他應當承擔的份額。該法規(guī)雖然并無直接使用“逐次”、“先后”等表示時間順序的詞語,明確允許債權人分別單獨起訴連帶債務人,但法規(guī)文本自身也未對此做出禁止性規(guī)定。
債務人之間存在單向的連帶關系和求償權,是連帶債務的法定類型之一;在保證合同中,當事人雙方之間沒有對等的給付義務,因此保證合同為單務合同,在保證中不發(fā)生義務履行的順序問題。我國《民通意見》首先確立了債權人與保證人之間可以成立連帶關系。將我國《擔保法》第18條、《擔保法》司法解釋第20條第1款。的規(guī)定與上述其他大陸法地區(qū)民事實體法對“連帶債務”的規(guī)定相比較,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與履行方式,不存在任何差別。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斷:連帶責任保證中的債務人與保證人之間,成立連帶債務關系。
在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債權人與債務人締結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成立基礎債務關系。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屆滿后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可以《合同法》第107條與《擔保法》第18條為基礎請求法院要求債務人按照合同約定的內容履行給付義務。因此,債權人對債務人,基于給付金錢或貨物為內容的主債務合同,在債務人違約時享有一個獨立的請求權,可以提出一個以清償全部債務為內容的訴訟請求。
債權人與連帶保證人之間,依據(jù)《擔保法》第18條成立連帶責任保證合同關系。保證合同,既可能作為主債務合同文本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債權人與保證人所單獨簽署的一份保證協(xié)議。但無論存在形式如何,債權人均可以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時,根據(jù)保證協(xié)議的約定,依據(jù)《擔保法》第18條,選擇向部分或所有連帶保證人請求清償全部債務。保證具有獨立性,雖然保證人的保證債務與主債務人之間形成主從關系,依主債務的存在而存在,在成立上、范圍與強度上、移轉上、變更與消滅上,具有從屬性;但是保證債務并不是主債務的一部分,而是獨立于主債務的單獨債務。因此,債權人對每一名連帶保證人,基于保證合同享有獨立的請求權,可以對每一名連帶保證人提出一個以履行保證責任、清償全部債務為內容的訴訟請求。
至此,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債權人與主債務人、各保證人之間,處于具有連帶性的給付之債的關系中,主債務人和保證人均屬于連帶債務人。債權人分別先后起訴各連帶債務人時,每個訴都有獨立的實體法律為基礎的請求權,因此具有獨立的訴訟標的。
(三)不可分債務的訴訟標的
“否定說”中所提及的“不可分債務”,是以多數(shù)主體以同一個不可分給付為標的債務;不可分債務與連帶債務均具有擔保機能,但不可分債務更強。不可分之債,其內容與給付方式客觀上具有某種不可分的物質屬性。因此,不可分債務中,任何一名債務人都對全部債務負有一次性清償責任,債務人之間客觀上、物質上不能按份清償不可分債務。強行由債務人按份清償債務,會導致債之標的物價值的減損。
由此可見,多數(shù)債務人之間具有連帶性是連帶債務與不可分債務的共同特征,債權人可以向一名、數(shù)名或全體債務人提出完成全部給付內容的請求。兩種類型債務的唯一不同,在于其給付內容是否在物質上、法律上可分。債務的連帶性本身,不使得債務具有不可分性。
主要大陸法地區(qū)的民事法律同時規(guī)定了“連帶之債”與“不可分之債”,后者要求債權人依據(jù)“連帶之債”的規(guī)定向債務人行使權利。例如,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第292條、《德國民法》第431條以及《日本民法》第430條。因此,不可分債務同連帶債務一樣,債權人與每一名債務人之間均存在單獨的給付之債法律關系,從主體與法律關系數(shù)量上看都是多數(shù)債務;債權人可以任意起訴某一名債務人,不需要同時起訴全體債務人,也不構成必要共同訴訟。以給付之債法律關系的數(shù)量來看,不可分之債中也存在多個訴訟標的。
我國《民法通則》與《擔保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均沒有規(guī)定“不可分債務”。連帶責任保證合同中,債的標的物一股是現(xiàn)金。從物理性質來看可分;從當事人間約定內容來看,全體保證人就主債務能夠最終得到全額償還向債權人做出保證,沒有約定履行順序,沒有設置保證責任履行的前提條件。因此,連帶責任保證合同中的給付之債,性質上不屬于“不可分之債”。從另一方面來說,根據(jù)不可分之債在我國臺灣地區(qū)、德國與日本民事法律中的規(guī)定,債權人也有權先后、分別向債務人請求履行清償義務,當一名債務人不能清償不可分割的債之標的物時,債權人有權向下一名債務人繼續(xù)主張權利。
因此,即使連帶責任保證合同成立不可分之債,債權人也有實體法依據(jù),分別先后向每一名債務人、保證人主張償還不可分的債之標的物。
三、案件事實與一事不再理
在“否定說”中,“訴訟標的相同說”是對實體法中債的標的與訴訟標的之間的關系的誤讀,而“案件事實相同說”則是完全從民事程序法的角度考慮一事不再理的適用問題。持此觀點的人認為: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存在主從合同關系,當法院先后審理債權人分別依據(jù)主合同與從合同對債務人和保證人發(fā)起訴訟時,前訴與后訴的案件事實高度相似,應當視后訴為重復起訴,即使前訴與后訴的當事人與訴訟標的不同。筆者認為,“案件事實相同說”限縮了構成重復起訴的法定必要條件,是對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相關規(guī)定的片面理解,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判決中的精神。
(一)重復起訴的判定標準
“案件事實”是否相同,在《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中并不是重復起訴的判定標準。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適用《民事訴訟法》解釋第247條的規(guī)定,兩起先后發(fā)生的訴訟構成重復起訴的法定必要條件為:一是訴訟當事人相同;二是訴訟標的相同;三是訴訟請求相同,或實質性互相否定;三個條件同時滿足時,后訴才視為對前訴的重復起訴。鑒于司法實踐中該解釋設定的標準仍比較概括,最高人民法院進一步細化了重復起訴的判定標準:
判斷當事人在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分別起訴所形成的案件是否屬于同一案件,應當從案件的當事人、案件的性質(法律關系)、案件的事實以及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等方面是否同一進行綜合考量。基于相同的當事人、同一事實、同一法律關系以及主要訴訟請求相同,在不同地方法院分別提起訴訟所形成的案件,可以認定屬于同一案件。
由此可見,“案件事實”并非法律、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的法定要件,而是實踐中高級別法院產生的司法經(jīng)驗,對下級法院不具備強制性約束力,僅作為參考意見。而且,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應當綜合地、平等地考慮訴訟當事人、訴訟標的、案件事實與訴訟請求,而非僅參照案件事實。因此,“案件事實相同說”中僅依據(jù)案件事實這一個理由認定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前訴與后訴為重復起訴,既沒有《民事訴訟法》及其解釋中的依據(jù),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意見。
(二)規(guī)范性分析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對《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以及審判意見中確立的重復起訴審查標準,我們認為以金錢債務為標的物的典型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債權人先后分別起訴債務人與保證人,不構成重復起訴,原因如下:
1.當事人不同:
債權人首先起訴債務人或保證人,在獲得勝訴判決卻無法通過執(zhí)行獲得全部清償時,才會起訴剩余的債務人或保證人。因此,后訴中總是存在著先訴尚未起訴的當事人。
2.訴訟標的不同:
如上文所述,債權人同主債務人和每一名保證人之間,處于連帶債務關系中,享有獨立的實體法請求權。因此,作為給付之訴的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債權人對債務人與保證人分別發(fā)起的前訴與后訴擁有不同的訴訟標的。
3.訴訟請求有差異:
債權人起訴債務人與保證人的最終目的,是要求清償全部債務。從這一點看,與債務人和保證人分別發(fā)生的訴訟,似有相同的訴訟請求。但是,訴訟請求是原告在每一次訴訟中提出的具體主張,而非主觀目的。債權人對剩余債務人或保證人發(fā)起的再次訴訟,其具體訴訟主張,往往是要求被告人清償先訴中被告人無法清償?shù)牟糠帧6遥V訟當事人是訴訟請求指向的對象,給付之訴中債務人是債權人請求權指向的對象。因此,即使債權人均要求前訴與后訴被告就相同的債之標的物履行清償義務,前訴后訴當事人不同,也會導致訴訟請求不同。
4.案件事實有差異:
債權人請求債務人清償債務基于主債務合同違約的事實;與保證人之間的訴訟則基于保證合同請求保證人履行合同約定。主債務合同通常是借款與貨物買賣合同,債務人的違約行為具體有不履行、延遲履行給付義務以及瑕疵履行;連帶責任中的保證人既可能共同向債權人保證債務人償還債務,也可能分別先后為主債務合同提供保證,保證期間的起始點可能各不相同。先訴與后訴涉及的債之標的物數(shù)量也會存在差異,債權人在先訴中得到部分清償,又從后訴中得到部分清償,亦或者兩次訴訟均沒有得到全部清償。因此,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中,債權人與債務人、保證人之間的案件事實存在區(qū)別。
四、總結
民事審判活動,既是審判人員適用法律解決糾紛的過程,也是解釋法律活動。法律規(guī)定的文字與詞句,是一切法律解釋方法的出發(fā)點。對法律進行解釋,要按照法條中詞句的通常意義進行解釋;審判人員超越文字的字面含義對法律進行解釋,便構成了創(chuàng)造法律,而非解釋與適用法律。
綜上所述,從《擔保法》及其解釋相關規(guī)定的內容來看,連帶責任保證合同糾紛本質上是具有多數(shù)債之主體的給付之債,債權人與債務人、各連帶保證人之間構成連帶債務關系。因此,債權人對每一名債務人享有實體法請求權,存在多個獨立的訴訟標的,“訴訟標的相同說”不能成立。從《民事訴訟法》及其解釋來看,法院在民事審判中,需要以債權人先后分別起訴債務人與連帶保證人時,前后發(fā)生的訴訟中具有不同的訴訟當事人、訴訟標的,在訴訟請求與案件事實上存在差異,“案件事實相同說”也不能成立。因此,債權人只要遵循《擔保法》及其解釋關于保證期間的有關規(guī)定,及時起訴債務人和連帶保證人,就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適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