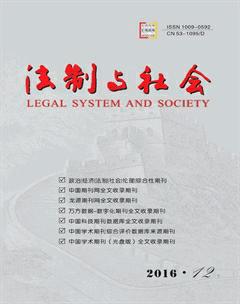論三方當事人類型的侵權責任及正當化基礎
劉濤
摘要 《侵權責任法》第32條監護人責任與第34條雇傭人責任雖然都是存在三方當事人的侵權責任關系,但是其責任性質與正當化基礎完全不同,監護人責任是監護人為無侵權責任能力人所承擔的補充責任,而雇傭人責任則是雇傭人基于危險責任與報償主義所承擔的自我責任。以上理解也影響到對第32條和第34條的構成要件的確定。另一方面,侵權責任法對侵權責任能力的理解也影響到對第32條和第34條的定位。
關鍵詞 監護人責任 雇傭人責任 補充責任 替代責任 侵權責任能力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307
侵權責任法所規定的一股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都是以當事人甲侵害當事人乙的權益,乙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向甲請求損害賠償為基本模型的。要求乙證明甲具有過錯的稱為一股侵權行為(過錯責任原則。《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第1款),甲必須證明自身不存在過錯才可能免除責任的(過錯推定原則。第六條第2款),以及不考慮甲是否有過錯,根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的(無過錯責任原則。第七條)稱為特殊侵權行為。也就是說在侵權責任的基本模型里,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雙方當事人登場。
但是,例外的,侵權責任法也對直接加害人以外的第三人規定承擔侵權責任。如《侵權責任法》第32條對未成年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的監護人責任,第34條對被雇傭人的侵權行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雇傭人責任。
對比第六條第七條所設立的侵權法基本模型,針對基于他人行為產生的侵權責任,我們必須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在直接的加害人之外,“誰”,在“什么情況”下,要為侵權行為承擔責任。我們需要從以下兩個基本的視角出發去理解這一問題。
責任人承擔責任的方式。首先,責任人是否只在行為人因為特殊事由無法承擔責任時才承擔侵權責任,即補充責任方式,還是責任人作為自身責任而承擔侵權責任,即替代責任方式。我國《侵權責任法》第32條的監護人責任和第34條雇傭人責任都被認為是替代責任方式。但是何為替代責任,以及以下兩個具體問題并沒有得到解答。其一,就監護人替代責任而言,第32條將侵權責任能力等同于民事行為能力的做法導致應當具有損害賠償能力的行為人完全不承擔自我行為的法律后果,而監護人一方承擔完全的替代責任,證明自己盡到監督責任的也只可能減輕責任,而不能免除責任。這種情況下的監護人嚴格責任是否能被正當化。其二,第34條中,雇傭人承擔的無過錯責任是旨在替代被雇傭人承擔侵權行為的后果,還是基于自身過錯承擔責任。對第34條性質的不同理解會導致雇傭人和直接行為人之間的最終責任問題的解決。
責任的正當化基礎。第二個視角是,為什么要由行為人之外的人承擔侵權責任。侵權責任法就監護人責任和用人者責任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因此,針對為什么要承擔責任的疑問,答案是法律的規定。但是,不僅僅為不是自己的行為承擔法律后果,而且還需要承擔無過錯的侵權責任,其正當化理由,不是僅僅一句保護被害人所能解決的。
一、監護人責任的正當化基礎
(一)監護人責任的意義所在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2條,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自身不承擔侵權責任。而第33條同時規定,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自己的行為沒有意識或失去控制的,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侵權責任(“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自己的行為暫時沒有意識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損害有過錯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反面解讀。所謂“過錯”并不是指《侵權法》第六條的過錯,而是第33條第二款所例舉的事由。)。對比這兩個法條我們可以得出我國侵權責任法雖然沒有專門法條,但是認可侵權能力這個概念的結論(第九條也可佐證這一結論)。
在不具有責任能力(我國侵權法上等同于行為能力)的行為人從事了侵權行為的情況下,根據所有人自擔風險的原理,被害人只能承受這一后果。那么,在這種情形下,有沒有比被害人更適合的承擔損害的第三人呢?第32條的意義在于,被害人就此有了向加害人之外的第三人進行損害賠償請求的可能性。根據第32條,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
第32條的監護人責任是以行為人本人沒有責任能力,因此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前提的,反過來說,如果直接行為人本人具有責任能力,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第32條第二款第一句: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就不會產生第32條第一款的責任承擔方式。這種責任承擔方式顯然屬于補充責任。當然,有學者已經進行了深度分析,該補充責任是否承擔的標準不應是第32條第二款的有無財產的標準。
而如果認為本條屬于監護人的自我責任,其存在的正當化基礎應當是未盡監護職責的過錯責任,或多數學者指出的至少也應當是以未盡監護職責為過錯事由的過錯推定責任。而不是現行法第32條的無過錯責任。
(二)監護人責任的構成要件
就監護人責任的構成要件,首先需要考慮承擔監護人責任的責任人的范圍。比較法上承擔監護人責任的通常是父母(父母離婚的情況下,有可能在親權人之外選定照顧權人,照顧權人成為責任人,而親權人免除監護人責任),另外,代替監護義務人(父母及其他)對被監護人進行監護的其他主體,如幼兒園小學老師,精神病院的醫生等,與監護人承擔同樣的責任。
在我國,父母近親屬之外,規定單位也必須在一定情況下承擔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的侵權責任。該規定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公有制企業占社會經濟組織的絕大多數,國家要求公有制企業和社會基層組織承擔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等),也成為第32條第二款規定的一個重要理由。
責任構成要件中的核心問題是,究竟采取什么歸責事由。本條的適用前提是直接行為人不承擔侵權責任的情形。根據本條,只要屬于監護人,便須無條件承擔侵權責任,即使“監護人盡到監護責任的”,至多只能“減輕其侵權責任”,也就是說,監護人責任屬于無過錯的補充責任。
事實上,即使在比較法上,監護人盡到監護職責的概念也并不限于阻止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權益這樣的具體的結果阻止義務,而是往往等同于“教育子女不侵害他人權益”這樣廣義的監護責任概念。在采取過錯推定原則的德日等國家,對于監護職責的廣義的理解也導致監護人責任在司法實踐中成為事實上的無過錯責任。但是,將侵權能力從行為能力中獨立出來,讓有識別能力的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而監護人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與直接行為人一起承擔連帶責任。也就是說,監護人承擔無過錯的補充責任的范圍原則上來說要比我國的第32條窄得多。
例如,同樣的侵權事實,分別是小學四年級九歲的A和高中二年級17歲的B,將同學的手機偷出來扔進河里,在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B不能免除自身責任,因此不構成監護人責任,在此情況下,被害人有可能會面對無完全賠償能力的加害人。我國侵權責任法將責任能力等同于行為能力,確實可以避免此種情況的出現。而就侵權責任法“歸責”的性質而言,將具有侵權法上識別能力的直接行為人排除在責任承擔體系之外,而由對被監護人的管理控制可能性降低的監護人承擔無過錯責任,僅僅一句“被害人救濟”是無法成為其正當化基礎的。
(三)未成年人責任與監護人責任的思考方法
與物權法等相比,侵權法屬于在比較法上差異較小的領域(經常被言及的一些侵權法上的多樣性,包括過錯、因果關系的認定等,更多的是表面的、技術層面的不同,在結論上往往并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其中還是存在若干有著重大不同的制度,未成年人從事侵權行為的情況下其自身及其監護人的責任承擔問題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問題之一。
從英美法(英國、美國)與大陸法(德國、法國)的二分法來看,英美法比較容易認定未成年人的侵權責任,而針對監護人承擔未成年子女的侵權行為之責任則非常謹慎。反之,大陸法上通常將未成年人免責,尋求父母承擔責任的方法。
而在大陸法系內部又存在多樣性。在法典的層面上存在如下幾種情形:
1.對低齡行為人設定特別規則,并且明示侵權責任的年齡界限。如《德國民法典》第828條。
2.對低齡行為人設定特別規則,但是沒有明示承擔侵權責任的年齡界限。如《日本民法典》第712條。
3.對低齡行為人沒有設立特別的責任能力規則。
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具體從幾歲開始具有侵權責任能力的規則一般由判例形成,而其具體年齡在不同國家又有很大差異。
1992年制定的荷蘭民法典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值得我們注意。根據《荷蘭民法典》第六編第169條規定,未成年人被分為14歲以下,14歲至16歲,16歲以上三種。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承擔無過錯責任,14歲至16歲的未成年人,父母承擔過錯推定責任,而16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根據該條具有侵權能力,父母有可能因為自身過錯而承擔一般侵權責任,與直接行為人構成連帶責任(該種連帶責任形式的監護職責一般來說至直接行為人成年年齡而終止)。
二、雇傭人責任的正當化基礎
(一)雇傭人責任的意義
和監護人責任不同,雇傭人責任中,被雇傭人(直接行為人)的行為滿足侵權行為成立要件,構成獨立的侵權行為。也就是說,雇傭人承擔的不是補充性質的責任,并不是被雇傭人不能承擔責任雇傭人才承擔責任,而是以雇傭人的自身責任為出發點的責任方式。雇傭人的這種責任承擔方式是實質意義上的替代責任,即雇傭人代替直接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
根據《侵權責任法》第34條,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即雇傭人承擔無過錯的侵權責任。對照德國法上的雇主過錯責任,我們需要找到我國法上雇傭人承擔無過錯的替代責任的正當化基礎。我國侵權責任法上存在所謂的“損害賠償的焦慮”,因此解釋上通常從保護被害人的觀點出發,認為雇傭人較被雇傭人在經濟上處于更加優勢地位,更加有利于對被害人進行賠償。但是“保護被害人”并不能成為無過錯責任的正當化基礎,或者說法制上不應當以是否存在賠償能力為是否承擔責任的考量因素。
事實上,雇傭人責任的更加實質意義的歸責基礎在于,針對自身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損害應當由雇傭人自身承擔責任。雇傭人通過被雇傭人的工作擴大了自身的活動領域,進而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就該擴大的領域中發生的損害不承擔責任顯然不合理。伴隨自身經濟活動產生的風險由自身承擔責任的思想,與危險責任的歸責思想相同,另一方面,從伴隨經濟活動而產生的與收益相伴的損害的角度,雇傭人責任又可以用報償主義解釋。
(二)雇傭人責任的構成要件
比照同樣屬于三方當事人侵權行為的監護人責任,本文在雇傭人責任的構成要件中,主要探討直接行為人的侵權行為。
第34條雖然只規定了行為人造成他人損害,事實上被雇傭人的行為構成侵權行為是雇傭人責任成立的前提。但是,“直接行為人構成侵權行為”是不是包含有“行為人承擔侵權行為”的意義?尤其在直接行為人為無責任能力人的情況。
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考量該問題:
首先是如何定位責任能力的問題。如果堅持責任能力是過失要件的應有之義,欠缺責任能力的情況下就無法認定行為人存在過失,侵權責任自然就不成立。但是如果認為侵權責任能力與過錯無關,是為了保護特殊類型的加害人而存在的制度——侵權能力被定位為加害人的免責事由——的話,侵權人即使沒有責任能力,也不妨礙侵權責任的成立。
第二個問題在于如何理解雇傭人責任的性質。如果將雇傭人責任理解為類似法國民法的保證責任的話,被雇傭人必須具備包含責任能力在內的全部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不具備侵權責任能力進而導致被雇傭人的侵權行為不成立的情況下,相當于主債務不成立情況下的保證債務,處于類似于保證人地位的雇傭人責任當然不成立。
反之,如果雇傭人責任不僅僅是為了確保被雇傭人的侵權行為之債得到履行,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固有的歸責基礎而產生的責任,那么被雇傭人的侵權行為成立與否就不再那么重要。被用人的行為導致的侵權行為,是伴隨經營活動產生的風險(危險主義),還是與經濟活動產生的收益相伴而生的損失(責任)(報償主義),才是決定雇傭人責任性質的根本。
這一問題的意義反映在第34條上,具體體現為雇傭人在向被侵權人承擔責任之后,是否能向直接行為人追償,還是只能自己負擔全部侵權責任。
如前所述,雇傭人承擔無過錯責任的基礎在于其承擔的是自我責任,這一責任不因為直接行為人偶然的是一個無責任能力人而改變。同時,不同于保證人與主債務人之間的關系,雇傭人與被雇傭人之間也不是百分百的必然存在求償關系。因此,即使我們將第34條稱為替代責任,這一責任的性質也不完全等同于保證責任。
綜上所述,第34條中的被雇傭人的行為,只要在客觀上被評價為侵權行為即可,而不需要就被雇傭人的行為是否滿足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的一般要件進行更進一步的判斷。
三、結語
本文簡要分析了三方當事人的侵權責任關系中典型的兩種情形,即監護人責任和雇傭人責任的意義和構成要件,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同樣是存在三方當事人的侵權責任關系,監護人責任作為被監護人不承擔侵權責任情況下存在的補充責任,其責任存在的前提在于直接行為人必須是無侵權責任能力人。隨著直接行為人識別能力的逐步提高,監護人承擔責任的形態也應當隨之變化。這也是侵權責任法作為“歸責法”(責任分配法)的體現。
其次,雇傭人承擔的是雇傭人自身的侵權責任,是實質意義上的替代責任,而該無過錯責任的正當化基礎在于伴隨自身經濟活動產生的風險,即危險責任原理,以及與收益相伴的損失,即報償主義原理。而這一基礎反映在構成要件上,一方面,被雇傭人的行為在客觀上被評價為侵權行為即可,而不需要完全根據《侵權法》第6條嚴格其構成要件;另一方面,因為雇傭人承擔的是自我責任,而不是對于被雇傭人責任的保證責任,因此雇傭人與被雇傭人之間也不存在必然的求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