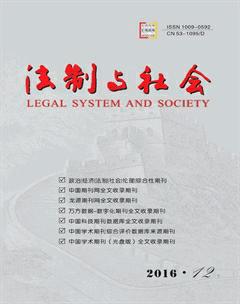共犯脫離相關問題研究
李浩東
摘要 共犯脫離指在共同犯罪中,自共犯關系形成之后到該犯罪行為完成的整個犯罪過程期間,部分處于共犯關系的人自動的從該共犯關系中脫離出來,切斷與其他共犯的關系,而不論其他共犯后續進行的犯罪的狀態如何,該脫離的部分共犯對脫離后其他共犯的行為不承擔責任。該理論對于化解共同犯罪人的共同參與、削減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意志、減輕和化解對被害人的風險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探討了共犯脫離的概念,研究了共犯脫離的認定,探索了共犯脫離成立的條件。
關鍵詞 共犯關系 共犯脫離 共犯中止
中圖分類號:D92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397
在共同犯罪中界定的共犯的中止,需出于行為人自己的意志而自動停止犯罪,以及需要有效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進一步實施犯罪行為,最終能夠有效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然而,行為人不是基于任意行為而與其他共同犯罪者解除共犯關系的,或者即使行為人與其他共犯解除了共犯關系,但若沒有能夠有效地預防犯罪結果發生的,均不能夠適用犯罪中止理論。此種情況,若一律嚴格執行共犯“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原則,對行為人若按既遂對待,難免顯得過于苛刻;如果按中止犯對待,卻又不完全符合中止犯的構成要件。為此,共犯脫離的理論就順勢產生。共犯脫離理論旨在解決共同犯罪人的犯罪均衡問題。該理論對于化解共同犯罪人的共同參與、削減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意志、減輕或化解對被害人的危險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共犯脫離源于日本,并非是我國刑法中所規定的內容,目前共犯脫離問題在我國屬于屬理論層面探討的內容,而不是立法上的規定,從而使共犯脫離的認定與成立條件等重要問題都需要細化和探討。
一、共犯脫離的概念
“共犯關系脫離”(簡稱“共犯脫離”)是由日本學者大塚仁最早提出的。大塌仁教授認為,所謂“共犯關系脫離”指在共同正規的實行著手后還未達于既遂的階段,共同正犯中的一部分人切斷與其他共犯的共同故意關系,而從其共同犯罪中脫離出去。
日本刑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共犯脫離,但審判實踐中法院的判例中默認了共犯脫離的概念。共謀者中的一部分人在其他共謀者做出實行行為之前表明從其共謀關系中脫離的意思并被其他共謀者了解時,不追究其對其后的其他共謀者的實行的責任。。可見,這類判例明確了在預備階段的共犯脫離及其法律責任,但它不同于大塚仁教授在對共犯脫離定義中提出的共同正規的實行著手后還未達于既遂的階段。另有一種觀點建立在因果關系論的基礎上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要求消除共犯行為所產生的物理的因果性與心理的因果性,分為著手前的脫離和著手后的脫離。在著手前表示脫離共犯關系,且告知其他共犯人,就肯定共犯關系的脫離;著手后的脫離,即使行為人努力消除這種效果,但如果客觀上沒有實際消除,須承擔犯罪既遂的刑事責任。
二、共犯脫離的認定
共犯脫離指在共同犯罪行為開始后至犯罪結果發生之前的任何階段,部分共同犯罪的行為人自動放棄了犯意,脫離了該共同犯罪,而其他共同犯罪行為人則繼續實施并完成了犯罪的情形。例如,某甲為殺害某乙準備了尖刀作為作案的工具,并邀請好友某丙進行幫助。一天晚上十點左右,某甲和某丙在某乙回家必須經過的小道上將其攔住。某甲用尖刀刺向某乙,某乙腹部負傷逃跑,某甲和某丙隨后緊追。此時,一位巡警發現某甲和萊丙二人,二人立即逃離犯罪現場。某丙逃離后就回家休息了。而某甲則隱藏在犯罪現場某處,待巡警離開后,某甲繼續四處尋找某乙,最后在某乙的家附近發現了某乙,某甲捅向某乙數刀,某乙身亡。本案某丙的行為如何定性?
上述案例的特點是:由2人組成的共謀故意殺人的共同犯罪中,其中一個行為人在該共同犯罪完成之前,從共犯關系中抽身脫離出去,而另外一個行為人則繼續將殺人犯罪實施完畢達到既遂的狀態。根據我國刑法之規定,對于該案例中的被告人某丙無法認定其構成犯罪中止。我國《刑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在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是犯罪中止”。很顯然,本案中某丙在自動放棄犯罪方面沒有太大的爭議,但是在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方面則不符合該要件的要求,無法認定某丙的行為構成犯罪中止。另外,對于此類案件,司法實踐中以及學界專家大多認為某丙的行為構成了犯罪既遂,但很明顯,以犯罪既遂來認定某丙的行為性質,顯得有些過于苛刻。這種己犯罪既遂的認定模式,不能夠有效貫徹以因果共犯論為基礎的“共犯自我責任”原則,也不能夠反映出某丙與某甲行為性質的差異,難以體現罪刑法定主義和罪刑均衡的原則。為此,如何有效解決此類行為人停止參與共同犯罪之后,但是犯罪結果卻發生了的行為人的責任問題,因我國立法上的漏洞,現實中成為理論上的難題。那么,共犯脫離理論正是為了解決該領域的難題。通過該理論,對于那些徹底割裂了與其他共同正犯之間的聯絡,并且不再對后者的行為產生作用的人,不管其是在著手前還是著手后解除了共犯關系,均對其脫離之后的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從而為共犯打開了輕罰甚至出罪的通道。
共犯脫離不等同于共犯中止,不需要依照中止犯的構成要件。共犯脫離以共同犯罪中個人的罪責為依據,能夠有效矯正共同犯罪部分承擔全部責任原則的不合理規定,較好地體現了刑法個人責任原則。
三、共犯脫離成立的條件
從總體上分析,共犯脫離應具備能夠解消原有的共犯關系之程度。具體包括以下要件:
(一)主觀要件
共犯脫離在主觀方面應具備“自動放棄”犯意的條件(自動性)。這種“自動性”應是出于脫離者“本人”的一種“己意”。
國外刑法理論對脫離者放棄犯罪的“自動性”有三種不同的觀點:非物質障礙說、衷心悔悟說和任意中止說。“自動性”指脫離者在心理上而不是因外部障礙而停止和放棄犯罪的。這種情況下,放棄犯意的“自動性”,應與“犯罪中止”的自動性的情況一致。
國內有學者認為,在共犯脫離情境下,只要脫離者出于“己意”中止共同犯罪,客觀上脫離了共犯關系,即使其行為人共犯完成了犯罪,也應當對其論以“中止犯”,即依法對脫離者給予減輕或免除處罰。
本文認為,共犯脫離的主觀要件應具備:其一,“脫離者主觀上以某種方式傳遞出脫離共同犯罪的意思;其二,以該種方式所傳遞出的意思表示需達到被他共犯人所了解的程度。某種表達方式包括積極或消極兩種方式。積極的表達方式包括明確地表達或暗示地表達了本人脫離共同犯罪的意圖。消極的表達方式包括以自身的行動表明脫離該共同犯罪的意思,也就是說能夠令其他共犯人意識到脫離即可。該主觀要件反映出脫離者來自內心不再參與共同犯罪活動,是脫離者主觀惡性消減的體現,也反映出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意方面的分崩離析。該理論有利于罪刑均衡,有利于實現刑罰的個別化,激發犯罪者從共同犯罪中撤離,是對共犯脫離行為人從輕、減輕、不予處罰的主觀判斷基礎。因此,脫離者以某種方式傳遞了脫離共同犯罪的意思并為其他共同犯罪人所知曉,是成立共犯脫離的主觀基準要件。
(二)客觀要件
客觀要件主要體現為行為人事實上需實施了停止自己的共犯行為而脫離了共犯關系,表明脫離者用客觀實際的行動反映出其脫離共犯的主觀意圖。也就是說,行為人傳遞出脫離共同犯罪的意圖并為其他共犯者所知曉這一主觀要件只是共犯脫離成立的前提要件,除此之外,還需考量該脫離人是否徹底終止了自己的犯罪行為并脫離了共犯關系。這樣會使共犯關系的構成發生改變,犯罪的破壞性減弱,從而導致其他共犯人完成犯罪的可能性下降。這是判斷脫離者減免刑罰的客觀依據。
脫離共犯關系行為應以是否解除原有的共犯關系為準。該脫離行為又可分為積極的脫離行為和消極的脫離行為。前者指行為人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圖讓其他共犯知曉,需要付出努力采取進一步措施來瓦解和阻卻其他共犯的犯罪行為,其意圖在于阻卻犯罪結果的發生。后者則只能發生在共同犯罪著手實施之前(在共同犯罪中處于被動和被支配地位的共犯),只要消極地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圖傳遞給其他共犯,消除原來的共犯關系即可。這種消極行為,不管是明示還是暗示,只需令其他共犯感知到其脫離意思就可以。例如,起協助作用的行為人沒有按照原來的約定時間和地點為共同犯罪人提供犯罪工具,足以另其他共犯認知到其脫離的意圖即可。
(三)效果要件
脫離者具備了前述兩個要件之后,并不能一定能夠認定已構成了共犯脫離。共犯脫離的認定,最終仍需從法律評價的視角考量是否已經遮斷了犯罪中的因果關系。其判斷依據是:是否遮斷了脫離者與其他共同正犯之間物理與心理的因果關系。若消除了自身貢獻的因果影響,可以認定已構成了共犯脫離;若沒有完全消除自身貢獻因果影響的,也有可能構成共犯脫離。因此,因果影響是否消除是從法律規范角度進行判斷和評價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事實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