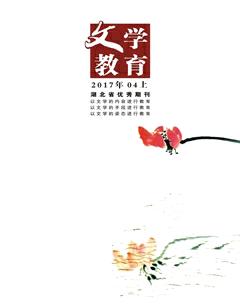漢語與中國文化在異質語境中的傳播與變異
宋陽+黃宣方
內容摘要:本文以美國華裔為研究個案,通過漢語符碼嵌入和文化意象使用等具體分析,分析了漢語和中國文化在美國異質文化語境中的傳播和變異。這一現象有助于當下的我們進一步研究漢語和中國文化在異質文化語境中的傳播與變異。
關鍵詞:漢語 中國文化 異質語境 傳播
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如何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中國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也越來越重視漢語與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以及傳播的過程中所面臨的與傳播國的異質文化語境之間的博弈。美國華裔對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態度是研究這一論題的絕妙切入點,他們所處的生存環境充分體現了美國社會環境的語言、文化多樣性的特點。在這個極具跨越性的領域中,漢語與英語、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在此相遇,由于彼此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體系的差異而產生了對話、交流甚至沖突、斗爭的互動與交鋒活動。
這種語言與文化的互動與交鋒的結果之一便是華裔的語言特色——漢語符碼的嵌入。一種嵌入的是在英語中已有對應詞的漢語符碼,即某些符碼在英語中已經具有約定俗成的“符號對等”。這類語碼多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在世界范圍內造成較大影響的事物的名稱,如“tofu”(豆腐)、“Mah-Jongg”(麻將)、“chopstick”(筷子)等詞語。另一種漢語符碼嵌入采用的是拼音的形式,也可以叫做“語音翻譯”,這是最常見且出現頻率最高的一種,或者直接采用漢語拼音,或者參照耶魯羅馬化系統進行拼寫,如“Chuangtzu”(莊子)、“chiu chiu”(蛐蛐)、“Kuen Ming”(昆明)等詞。最明顯的漢語符碼嵌入形式是直接使用漢字。這種情況并不常見,通常出現在封面設計中。美國華裔拒絕漢語與英語之間邊緣/主流、非法/合法的二元對立,也拒絕兩種語言所代表的作為“文化記憶”的中國文化與作為“本土記憶”的美國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通過將各種形式的漢語符碼嵌入英語,華裔將英語拉下神壇,使其從高高在上的霸權語言回歸為“僅是一種普通語言”;另一方面,華裔通過在異質語境中對漢語符碼的挪用、保存和轉換,打破了漢語原本渾然一體的穩定性,使其成為夾雜著鮮活異域生存經驗的時刻變化、生長著的“活的語言”。
漫漫五千年,勤勞、聰慧的中華民族不止創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物質文明,更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學寶藏。從《詩經》、《樂府》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國文化記憶一直回響在美國華裔心中。在與湯亭亭的一次談話中,陳美玲就坦言了自己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看法:我寫詩時常回想到唐朝。我感到自己確實是那中國傳統的一部分。我不愿與它割斷聯系。這就是我學習古漢語的原因。我感到它非常非常重要……我們的根在很早以前。我們是古老的心靈……我感到與我的中國根緊密相連。[1]
從林永得的美好靜謐的月夜意象到陳美玲的形單影只的沙鷗意象、從湯亭亭的“木蘭”到宋凱西的“壑舟”、從施家彰的“柳風”與“關關雎鳩”到姚強的李賀與李商隱,中國文化被華裔一次又一次地書寫,總能在不同時空的炎黃子孫心中引起共鳴。那很久以前的、古老的中國傳統的一部分,早已銘刻在每個華族個體的身上,成為“世代存于我們文化中”的記憶,得到不斷的傳承與發揚。
華裔以中國文化的文化記憶為源、以華裔詩人的本土經驗為源,承襲了漢語與英語、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兩個文學傳統。在承襲的同時,他們既拒絕中西文化傳統的絕對權威和穩定性,又否認兩者的二元對立,通過對語言和文化傳統的挪用、改寫和馴化等方法,華裔拼貼出了仿似馬賽克般鮮活生動的語言形式與文化意象。這一現象在兩種語言和文化傳統之間找到了協調和平衡之處,有助于當下的我們進一步研究漢語和中國文化在異質文化語境中的傳播與變異。
參考文獻
[1]Marilyn Chin. “Writing the Other: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Kong Kingston(1989).”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Paul Skenazy and Tera Martin eds.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p. 94.
本文是遼寧省社科規劃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狀況與中國文化傳播對策研究》(L16DYY008)、沈陽大學“大創”項目《基于漢語國際教育跨學科視角的英語專業學生從業規劃》(201611035000077)和沈陽大學外國語學院項目《基于漢語國際教育視角的中國文化之異質語境傳播研究》的成果。
(作者介紹:宋陽,文學博士,沈陽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亞裔美國文學和海外華人詩學;黃宣方,沈陽大學外國語學院2014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