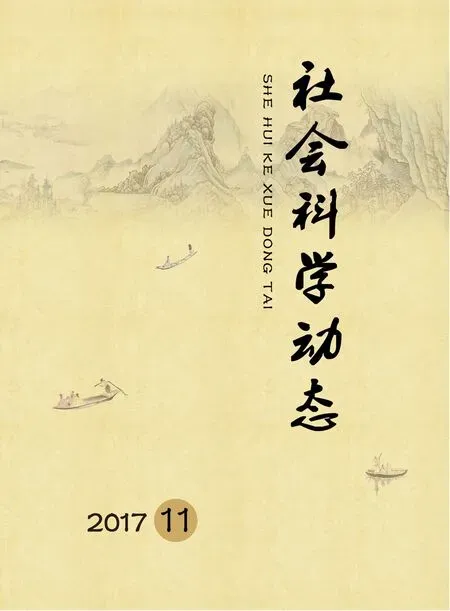論共同體道德債務(wù)
羅明星
學(xué)術(shù)新論
論共同體道德債務(wù)
羅明星
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是真實(shí)卻被忽略了的倫理事實(shí),表征著共同體之間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的非平衡關(guān)系,其有效性取決于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之間“承認(rèn)共識”的達(dá)成。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可能因傷害產(chǎn)生,因奉獻(xiàn)生成,亦可能是純粹基于身份的先在規(guī)定,分別形成傷害性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奉獻(xiàn)性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和先在性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物性償債與靈性償債是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清償?shù)幕痉绞剑鼉攤鶆t是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清償?shù)淖罡咝问健5赖聜鶆?wù)之于共同體并非絕對的熵性存在,作為實(shí)存的倫理資源,道德債務(wù)可以實(shí)現(xiàn)共同體的精神集成,促成共同體的有機(jī)團(tuán)結(jié),還可以在共同體內(nèi)實(shí)現(xiàn)有效的社會動員,為共同體發(fā)展集聚精神動力,而道德債務(wù)的加載、清償、轉(zhuǎn)移或遺忘,則可以成為共同體治理的價值工具。
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清償
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既是影響共同體自身穩(wěn)定的道德存在,也是關(guān)涉社會穩(wěn)定與社會發(fā)展的道德因素。正視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并通過道德債務(wù)清償實(shí)現(xiàn)共同體和諧,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必然選擇。
一、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本質(zhì)
“債”從“人”從“責(zé)”,自古以來,債就是人之責(zé)。在一般意義上,債務(wù)是一個法律概念,即按照合同約定或法律規(guī)定,在主體之間產(chǎn)生的一方享有請示他方為或不為特定行為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與法律債務(wù)不同,道德債務(wù)是主體之間基于道義的非平衡狀態(tài)而形成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按照普適性的道德公義,主體之間的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應(yīng)該對等,但是,在實(shí)際的道德生活中,當(dāng)主體獲得的道德權(quán)利大于其履行的道德義務(wù)時,“道德權(quán)利”減除“道德義務(wù)”的余額,客觀上就成為了“道德債務(wù)”。與法律債務(wù)一樣,道德債務(wù)亦有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的區(qū)分,享有權(quán)利的一方為道德債權(quán)人,履行義務(wù)的一方為道德債務(wù)人。
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是以共同體作為主體的道德債務(wù),反映著共同體之間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的非平衡關(guān)系。但是,由于共同體是由個體構(gòu)成的有機(jī)整體,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客觀上亦是共同體中每一個體的道德債務(wù)。就像盧梭理解的那樣,共同體是一個契約性存在,擁有“統(tǒng)一的自我意識,擁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①。因此,從共同體中獲得其社會本質(zhì)的個體,理所當(dāng)然地成為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實(shí)際承擔(dān)者。作為依賴于共同體生存的偶然性存在,個體的唯一選擇是,與共同體成員一道以最具效益的方式清償?shù)赖聜鶆?wù),讓共同體盡快從道德債務(wù)中解放出來,自己亦在共同體的解放之中獲得自我解放。
道德債務(wù)雖然廣泛存在,但只有達(dá)到特定閾值的道德債務(wù),即達(dá)到了作為共同體的債權(quán)人或債務(wù)人利益計較值的道德債務(wù),才能引起共同體的集體性關(guān)注,成為共同體必須面對和清償?shù)牡赖聜鶆?wù)。按理說,只要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產(chǎn)生了不平衡,道德債務(wù)就必然產(chǎn)生,但事實(shí)上,現(xiàn)實(shí)生活中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的不平衡盡管無處不在,可道德債務(wù)卻并沒有如影隨形。根本原因在于,絕大多數(shù)道德債務(wù)并沒有觸及共同體的“利益計較值”,并不足以引起共同體的道德注意,由于客觀的道德債務(wù)沒有得到共同體的主觀確認(rèn),道德債務(wù)也就成為事實(shí)上的無效債務(wù)。應(yīng)該說明的是,由于共同體本身有層級的區(qū)分,而且同一層級共同體由于經(jīng)濟(jì)、政治或文化的差異性,其利益計較值的“閾值”也可能盡然不同。這就意味著,同樣性質(zhì)與同等程度的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的不平衡,在A共同體視域中可能成為有效道德債務(wù),在B共同體視域中則可能成為無效道德債務(wù)。
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有效性還取決于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之間“承認(rèn)共識”的達(dá)成。事實(shí)上,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并不一定同時得到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的共同確認(rèn),由于道德債務(wù)的認(rèn)知不協(xié)調(diào),道德債務(wù)有時很難在共同體之間形成共識。其中的情形很復(fù)雜。一種情況是,道德債務(wù)之債務(wù)人否定道德債務(wù)的存在,但債權(quán)人卻堅信這一債務(wù)的存在。比如,土耳其人對亞美利亞人因?yàn)橥罋⒁瓿龅牡赖聜鶆?wù),亞美利亞人作為債權(quán)人認(rèn)為這是不爭的事實(shí),但土耳其人作為債務(wù)人卻拒絕承認(rèn)。由于對道德債務(wù)的承認(rèn)可能損害共同體的倫理形象,尤其可能引申出重大的經(jīng)濟(jì)利益賠償,作為債務(wù)人的共同體可能以犧牲良心的方式拒絕道德債務(wù)的存在。另一種情況則相反,債務(wù)人承認(rèn)道德債務(wù),債權(quán)人卻對道德債務(wù)加以否認(rèn)。典型的例證是,在中國,子女共同體習(xí)慣將自己置于道德債務(wù)的債務(wù)人角色,因?yàn)橹袊改笍淖优錾从枰越^對性付出,子女會將對父母的虧欠理解為不可推卸的道德債務(wù)。但作為債權(quán)人的父母共同體卻并不這樣認(rèn)為,他們將對子女的絕對付出理解為自己的天然職責(zé),并不承認(rèn)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道德債務(wù)關(guān)系。沒有承認(rèn)共識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只能是單邊債務(wù),但單邊債務(wù)也是債務(wù),道德債務(wù)不被承認(rèn)并不影響道德債務(wù)的客觀真實(shí),只可能導(dǎo)致道德債務(wù)的無法清償或清償無效。道德債務(wù)的共識達(dá)成,需要理性的智慧表達(dá)與行動的效果檢驗(yàn),也是一門讓共同體走向和諧的道德藝術(shù)。
必須說明的是,共同體道德債務(wù)與共同體經(jīng)濟(jì)債務(wù)、政治債務(wù)及法律債務(wù)往往是一體性存在,通常,經(jīng)濟(jì)債務(wù)、政治債務(wù)及法律債務(wù)的清償過程同時也是道德債務(wù)的清償過程。但不管是怎樣的債務(wù),唯有蘊(yùn)含其間的道德債務(wù)得到清償,共同體債務(wù)問題的終極解決才成為可能。
二、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形成
1.由傷害而產(chǎn)生
傷害是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形成的最常見原因。縱觀人類歷史,國家共同體、種族共同體、宗教共同體、家族共同體等在歷史的時空轉(zhuǎn)換中興衰存亡,其中,傷害性共同體沖突成為人類文明進(jìn)程中的悲劇性記憶。雖然共同體沖突有政治上的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在道德世界里,任何一種沖突都是人類的精神苦難,尤其是暴力性的共同體沖突,總是不得不用鮮血褻瀆生命的神圣,用生命的毀滅鑄就通往拯救生命的希望之路。然而,即便是共同體沖突中的勝利者,在慶祝勝利的狂歡過后,當(dāng)其冷靜下來面對沖突中的失敗者時,復(fù)位的人性亦會讓自己對沖突中的暴力行為進(jìn)行反思,對失敗者的歉疚感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蔓延至整個共同體。可以說,每一次共同體沖突都是一次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生成。歷史上,因?yàn)閭?dǎo)致的道德債務(wù)不勝枚舉,如:基督教徒對猶太教徒的迫害,形成了基督共同體對猶太共同體的道德債務(wù);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暴力驅(qū)逐,形成了白人共同體對印第安人共同體的道德債務(wù)。因傷害形成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具有顯然的惡性特征,它不僅造成共同體之間的心理疏遠(yuǎn)與情感間離,而且可能為共同體發(fā)展設(shè)置難以逾越的倫理障礙,尤其在道德債務(wù)不能有效清償?shù)那闆r下,甚至可能惡變?yōu)楣餐w的歷史頑疾,成為共同體之間無休止血腥復(fù)仇的道德口實(shí)。就像當(dāng)今世界的恐怖主義,恐怖分子針對無辜平民的恐怖襲擊總是有一個冠冕堂皇的道德借口,似乎總想依靠恐怖襲擊實(shí)現(xiàn)某種道德債務(wù)清償,但恐怖主義實(shí)施的結(jié)果卻客觀上導(dǎo)致了新的道德債務(wù)的形成。
2.因奉獻(xiàn)而生成
共同體道德債務(wù)亦可能因奉獻(xiàn)而生成。奉獻(xiàn)是人的類本質(zhì)的善性表達(dá),是共同體之間愛的傳遞。奉獻(xiàn)過程中利益輸出與輸入的不平衡,亦可能導(dǎo)致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產(chǎn)生。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奉獻(xiàn)性道德債務(wù)也許產(chǎn)生于氏族和部落之中。摩爾根在考察古希臘人氏族繼承規(guī)則時發(fā)現(xiàn),財產(chǎn)“由同宗親屬按照與死者的親屬次序繼承,死者的子女是死者最親的同宗親屬,由此便獲得了獨(dú)占繼承權(quán)”②。當(dāng)子女從自己的父母那里獲得獨(dú)占繼承權(quán)時,客觀上是在享有來自父母的權(quán)利。按照已經(jīng)形成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對等觀念,子女必須給予父母相同的權(quán)利,才能達(dá)致內(nèi)心世界的道德平衡。然而,父母在子女有能力履行足夠的道德義務(wù)時已經(jīng)離開了這個世界。于是,子女作為共同體,父母作為共同體,未盡的道德義務(wù)客觀上成為子女共同體的道德債務(wù)。尼采清晰地看到了這一點(diǎn),并將先輩的奉獻(xiàn)性道德債務(wù)理解為一種永恒:“人們相信種族只有通過祖先的犧牲和功績才得以延續(xù),因此人們應(yīng)當(dāng)用犧牲和功績來回報祖先。人們甚至進(jìn)而承認(rèn)這樣一種仍然在持續(xù)增長的債務(wù),這就是祖先們在其強(qiáng)大精神的繼續(xù)存在中,從未停止從自己方面向他們的種族提供新的優(yōu)惠和作出新的預(yù)支。”③尼采的意思是,即便先輩已經(jīng)離世,但其犧牲精神仍然給后輩以恩惠,后輩將永遠(yuǎn)沉浸在先輩的奉獻(xiàn)性道德債務(wù)之中。當(dāng)然,奉獻(xiàn)性道德債務(wù)并不僅僅存在于血緣共同體之間,國家共同體、民族共同體等其他共同體之間也普遍存在。與傷害性道德債務(wù)相反,奉獻(xiàn)性道德債務(wù)是一種善性道德債務(wù),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彼此將對方視作目的性存在,道德債務(wù)的發(fā)生與道德債務(wù)的償還,處處體現(xiàn)著人性的高貴與德性的光輝。
3.基于身份規(guī)定而形成
人類歷史上還存在一種基于身份規(guī)定而非真實(shí)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而形成的道德債務(wù),我們可以稱之為先在性道德債務(wù)。宗教性道德債務(wù)即屬于此種債務(wù)。教徒從出生的那一刻起,道德債務(wù)就作為神圣性義務(wù)與生命相伴,并伴隨生命的流逝走向永恒。以基督教為例,按照《圣經(jīng)》的解釋,人類祖先亞當(dāng)和夏娃因?yàn)橥党陨茞簶渖系墓麑?shí)而對上帝犯有原罪,因此,人從出生開始就背負(fù)原罪。原罪是本體論意義上的道德債務(wù),是上帝給人賦予靈與肉的同時附加在人身上的精神桎梏。宗教性道德債務(wù)具有絕對性,是宗教共同體中所有信徒的神圣義務(wù),除非走出這一共同體,否則沒有人可以享受道德債務(wù)的豁免權(quán)。所以,宗教生活中的人,沒有人能夠擺脫宗教性道德債務(wù)的重負(fù),相反,背負(fù)宗教性道德債務(wù)恰恰是教徒獲得世俗社會主體資格的前提,只有當(dāng)教徒將道德債務(wù)理解為神圣之愛并心甘情愿地償還債務(wù)時,才能在真實(shí)世界里獲得虛幻的自由。宗教性道德債務(wù)本質(zhì)上是虛假債務(wù),因?yàn)槲覀冎荒苷鎸?shí)確認(rèn)作為債務(wù)人的教徒的主體資格,但不能確證債權(quán)人神(如基督教里的上帝)的主體資格的真實(shí)性,更不能提供人與神之間道德債務(wù)形成的本體論證明。可以說,先在性的宗教道德債務(wù)其實(shí)是宗教教義在世俗世界的倫理呈現(xiàn):“吠陀和基督教教義最終都?xì)w結(jié)為同樣奇怪的舉措:首先將全部道德準(zhǔn)則描述成債務(wù),但是接下來,他們這樣做的方式,卻表明道德準(zhǔn)則并不能真的被簡化成債務(wù)。”④
在世俗世界里,先在性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亦廣泛存在。其一,先在性道德債務(wù)可能因血緣身份而天然形成。如道教“承負(fù)”理論就認(rèn)為,“如果上輩人對自己的行為不負(fù)責(zé)任,就給后代留下道德債務(wù)”。⑤古代印度債法規(guī)定:“兒子、孫子在父親、祖父遠(yuǎn)走他鄉(xiāng)、去世或受不治之癥折磨時,有義務(wù)為之履行債務(wù)。”⑥這就是說,先輩的道德債務(wù)天然就是晚輩的道德債務(wù),基于血緣身份承繼先輩道德債務(wù)是個體擔(dān)當(dāng)共同體責(zé)任的基本形式。其二,先在性道德債務(wù)可能因政治身份而天然生成。強(qiáng)勢共同體為了實(shí)現(xiàn)對弱勢共同體的控制,故意制造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的不平衡,將非真實(shí)的道德債務(wù)強(qiáng)加給弱勢共同體,從而為強(qiáng)勢共同體的利益實(shí)現(xiàn)提供道德支持。例如,專制政體下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總是習(xí)慣于將被統(tǒng)治者的平凡生活標(biāo)榜為自己的“恩賜”,是統(tǒng)治者的特別付出成就了被統(tǒng)治者的幸福生活,因此,被統(tǒng)治者應(yīng)該對統(tǒng)治者表示感激。在日本,償還天皇的道德債務(wù)就曾經(jīng)是國民的天然義務(wù):“個人對天皇所欠之債,一個人必須以無限感激的心態(tài)來接受這種恩情債。日本人覺得當(dāng)個人為自己生于這個國家,得以如此生活,得到大大小小的關(guān)懷感到高興的時候,不可能不想到這一切都是天皇的恩惠。”⑦其實(shí),日本國民的生活永遠(yuǎn)由自己創(chuàng)造,是自己的勞動鑄就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日本天皇與日本國民之間并不存在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的道德關(guān)系。所以,基于政治身份形成的先在性道德債務(wù)本質(zhì)上也是虛假性債務(wù),是在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建立的主觀聯(lián)想。
三、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償還
有債必還,這是底線性的道德規(guī)定,是具有普世通約性的倫理常識。所以,共同體道德債務(wù)一旦形成,清償?shù)赖聜鶆?wù)就成為共同體不可推卸的道德責(zé)任,因?yàn)閺摹皞鶆?wù)中擺脫出來是人賴以從整體上獲得解放的前提”⑧。
1.物性償債
物性償債即債務(wù)人通過現(xiàn)實(shí)物質(zhì)利益對債權(quán)人進(jìn)行道德債務(wù)清償。盡管道德債務(wù)可能因各種不同原因而產(chǎn)生,但通過物質(zhì)利益償還道德債務(wù)永遠(yuǎn)是行之有效的償債方式。由于道德債務(wù)本質(zhì)上是利益關(guān)系的倫理呈現(xiàn),所以,以物性方式對債權(quán)人進(jìn)行利益補(bǔ)償,成為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償還的普遍選擇。比如,作為對猶太人道德債務(wù)的償還,德國從1952年簽署關(guān)于賠償受迫害猶太人的《盧森堡條約》開始,總共支付的賠償已逾700億歐元。⑨德國人的物性償債,給曾經(jīng)遭受傷害的猶太人以極大的精神撫慰。以物質(zhì)利益償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優(yōu)點(diǎn)在于,物質(zhì)利益是可以計量的,人們可以通過物質(zhì)利益數(shù)量的多少,窺見債務(wù)人償還道德債務(wù)的誠意,從而形成關(guān)于道德債務(wù)償還事實(shí)的清晰認(rèn)知。同時,由于物質(zhì)利益可以給債權(quán)人帶來真實(shí)性的生活改良,增加直觀性的愉悅體驗(yàn),客觀上淡化了債權(quán)人對債務(wù)人的道德積怨,有利于促進(jìn)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之間的道德和解。但是,道德債務(wù)畢竟并不是純粹的物性債務(wù),因此,物質(zhì)利益補(bǔ)償又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到底多少物質(zhì)利益才能對道德債務(wù)進(jìn)行對等補(bǔ)償,其實(shí)是一個沒有答案的道德懸問。
2.靈性償債
正是由于物性償債并不能從真正意義上實(shí)現(xiàn)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完全清償,因此,靈性償債即債務(wù)人通過源于心靈的精神性付出對債權(quán)人進(jìn)行道德債務(wù)清償,成為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償還的重要形式。
集體性道歉與集體性感恩是共同體道德債務(wù)靈性償還的基本方式。
集體性道歉主要適用于傷害性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靈性償還。道歉是以語言為載體將道德的自我譴責(zé)呈現(xiàn)于受害者的道德行動。集體性道歉的倫理意義在于,作為道德債務(wù)人的共同體以在場的方式平等面對債權(quán)人,表達(dá)了對債權(quán)人作為共同體的人格尊重;向債權(quán)人坦誠自己的道德過錯,將歷史傷害的道德責(zé)任歸咎于自身,還原了曾經(jīng)可能被扭曲的道德正義;以公開的話語方式昭示共同體的道德歉意,將債權(quán)人的共同體利益置于債務(wù)人共同體形象的優(yōu)先位置,顯示了債務(wù)人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正是通過集體性道歉,債權(quán)人感知到債務(wù)人的內(nèi)心真誠,進(jìn)而形成對債務(wù)人的情感性包容,債權(quán)人與債務(wù)人的道德債務(wù)在善性的道德諒解之中得以質(zhì)性遞減,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由此得到償還。作為集體性道歉的經(jīng)典案例,德國總理的莊嚴(yán)一跪成為靈性償債的范本。1970年12月7日,時任聯(lián)邦德國總理的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fēng)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jì)念碑前下跪謝罪,被譽(yù)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qiáng)烈的謝罪表現(xiàn)”⑩。下跪謝罪是德國人對猶太人表達(dá)歉意的極端舉動,但正是這一跪,化解了飽受納粹蹂躪的波蘭人民沉積在心底的憤怒,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得到了實(shí)質(zhì)性清償。
集體性感恩主要適用于奉獻(xiàn)性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靈性償還。感恩即債務(wù)人通過心靈的虔誠付出銘記債權(quán)人的道德恩惠并表達(dá)對債權(quán)人的道德敬意。由于奉獻(xiàn)性道德債務(wù)源于債權(quán)人的無私付出,集體性感恩就成為債務(wù)人償還道德債務(wù)的必然選擇。債務(wù)人通過對債權(quán)人內(nèi)心的道德尊重或言行的道德贊美,亦或通過“物化良心”的直觀展示,回報債權(quán)人曾經(jīng)給予共同體的道德恩惠。正如亞當(dāng)·斯密所說:“那個把溫和、仁慈和文雅等各種美德同偉大、莊重和大方等各種美德結(jié)合起來的人,肯定是我們最為熱愛和最為欽佩的自然而又合宜的對象”。?在債務(wù)人的心目中,債權(quán)人就是“最為熱愛和最為欽佩的自然而又合宜的對象”。當(dāng)債務(wù)人用虔誠與敬意表達(dá)對債權(quán)人的尊重時,債權(quán)人藉此獲得道德回報,曾經(jīng)的道德權(quán)利與道德義務(wù)的不平衡得以修正,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得以償還。所以,感恩與其說是人類道德高貴的倫理表征,毋寧說是人類平衡道德債務(wù)以尋求內(nèi)心安寧的倫理法器。無論怎樣解讀,感恩成為滋潤共同體關(guān)系的德性力量都是沒有疑義的。
3.生命償債
生命償債是以生命作為利益載體償還道德債務(wù),是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清償?shù)淖罡咝问健I鼉攤梢杂袃煞N解讀,其一是以直接的生命犧牲一次性償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其二是以終生的生命付出持續(xù)性償還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無論是哪一種形式,以生命償還道德債務(wù)均具有絕對性,體現(xiàn)出道德的極致境界。尼采就清楚地表述了生命的償債功能,他說:債務(wù)人“在自己不能償還債務(wù)的情況下,根據(jù)契約把自己尚且‘占有’的其他東西,還能支配的物品抵押給債權(quán)人,比如,他的身體,他的妻子,他的自由,或者他的生命”。?共同體成員作為債務(wù)人主動以奉獻(xiàn)生命的方式償還道德債務(wù)乃是道德上的至善之舉,但是共同體成員作為債務(wù)人被迫以犧牲生命的方式償還道德債務(wù)則是道德上的極惡之行。以生命償還道德債務(wù)的生活實(shí)景集中體現(xiàn)在宗教領(lǐng)域。例如,對基督徒而言,出生就意味著用生命清償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開始。耶和華對犯有原罪的亞當(dāng)說:“你必汗流滿面才得以糊口,直到你歸了土”。?亞當(dāng)?shù)拿\(yùn)客觀上成為基督共同體中每一個教徒的命運(yùn)。在上帝面前,教徒事實(shí)上已經(jīng)不再是獨(dú)立的存在主體,就像詹姆士·里德所說:“我們放棄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放棄我們從前的生活,努力去做上帝要求我們做的人,努力去做上帝要求我們做的事。”?基督教以剝奪自由的方式賦予信徒以信仰自由,讓教徒在對上帝的絕對信仰中喪失理性的判斷力,讓生命的延續(xù)過程成為對上帝的償債過程。
四、共同體道德債務(wù)的價值
由于道德債務(wù)需要共同體通過利益付出進(jìn)行清償,而利益付出可能消解共同體的有機(jī)活性,因此,人們習(xí)慣于將道德債務(wù)理解為共同體的負(fù)面資產(chǎn),共同體中的個體甚至可能“感覺自己就是一個背負(fù)道德債務(wù)的囚徒”?。然而,道德債務(wù)之于共同體卻并非絕對的熵性存在,作為實(shí)存的倫理資源,道德債務(wù)對維系共同體生存與發(fā)展亦具有積極的效用價值。
1.共同體凝聚
馬克思曾經(jīng)說:“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共同體之所以能夠成為個體生命的棲身之處并讓個人獲得自由,關(guān)鍵在于共同體是具有強(qiáng)大凝聚力的實(shí)體。道德債務(wù),恰好是增加共同體凝聚力的重要粘合劑。
道德債務(wù)之于共同體的凝聚價值在于,可以促進(jìn)共同體“集體意識”的形成,并通過集體意識實(shí)現(xiàn)共同體的精神集成。集體意識是“一般社會成員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總和”?,共同體道德債務(wù)一經(jīng)形成,償還道德債務(wù)就成為共同體成員當(dāng)然的道德責(zé)任,亦在精神世界匯聚成共同體的集體意識。道德債務(wù)通過對共同體成員利益共生關(guān)系的實(shí)質(zhì)性同構(gòu),達(dá)成了共同體成員的利益共識,基于道德債務(wù)的共同記憶讓共同體成員在情感上保持著歷時性的密切關(guān)系,避免了離散性的利益紛擾對共同體精神世界的空間擠壓,客觀上為“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的創(chuàng)建預(yù)制了條件。共同體成員清楚地知道,作為共同體中的個體,既然自己不能舍棄也不能獨(dú)立清償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就必須與共同體成員實(shí)現(xiàn)精神上的有機(jī)團(tuán)結(jié),通過尋求共同體的道德解放獲得個人自由。正是在踐行這一理念的過程中,共同體的凝聚力得以形成。況且,個體對共同體道德債務(wù)承擔(dān)責(zé)任的過程,本身也是對共同體表達(dá)道德忠誠的過程,就像邁克爾·桑德爾所說:“改正我的國家的過往錯誤,是一種確定我忠誠于它的方式。”?當(dāng)個體通過償還道德債務(wù)對共同體表達(dá)忠誠時,忠誠自然也就成為共同體凝聚力的價值源泉。
2.共同體動力
共同體的發(fā)展來自于個體力量的張揚(yáng)。盧梭曾經(jīng)說:人類“只能把他們分散在個體的力量聯(lián)合成一種強(qiáng)大到足以抵抗任何阻力的力量,并且利用一個唯一的動機(jī)調(diào)動它,從而使它能夠協(xié)調(diào)一致地行動”?。對共同體而言,道德債務(wù)顯然具有“唯一的動機(jī)”的協(xié)調(diào)功能,足以作為精神動力促成共同體一致行動。
道德債務(wù)帶來的集體性內(nèi)疚,是其作為共同體動力的原始依據(jù)。眾所周知,內(nèi)疚本身是一種蘊(yùn)涵痛苦與自責(zé)的情緒體驗(yàn),是作為主體的人對自己道德過失實(shí)施的精神上的自我懲罰。集體性內(nèi)疚實(shí)質(zhì)上是共同體對自身負(fù)性社會形象的接納與反思,共同體中的每一個體,只要“把自己歸于施害群體,承認(rèn)自己所屬群體的成員過去的所作所為威脅到了群體認(rèn)同,并且內(nèi)群體應(yīng)為之負(fù)責(zé),就會體驗(yàn)到群體內(nèi)疚”?。集體性內(nèi)疚可以催生共同體良心的自我發(fā)現(xiàn),為共同體的償債行動加注精神動力。同時,集體性內(nèi)疚強(qiáng)化了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紐帶關(guān)系,促進(jìn)了共同體意識的發(fā)育與生長,激勵個體將自己的情感、意志與勇力一并奉獻(xiàn)給共同體,從而在共同體內(nèi)部實(shí)現(xiàn)有效的社會動員,為共同體發(fā)展集聚最大化的主體動力。必須說明的是,道德債務(wù)作為共同體精神動力并不絕然是善性的存在,尼采曾經(jīng)警告:債務(wù)可能“讓債權(quán)人得到一種愉悅來作為還債和彌補(bǔ)——這種愉悅就是債權(quán)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向無權(quán)的人行使權(quán)威,就是‘從作惡中得到享樂’的縱欲放蕩,就是在強(qiáng)暴中獲得的滿足”。?所以,讓道德債務(wù)展示其善性的動力意義,避免惡性的動力展示,是共同體不可規(guī)避的道德責(zé)任。
3.共同體治理
通過制造道德債務(wù),為共同體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據(jù),幾乎是所有當(dāng)權(quán)者的政治本能。比如,美國總統(tǒng)布什對伊拉克宣戰(zhàn)時發(fā)表演講:“我們懷著對伊拉克以及他們偉大人民和宗教信仰的尊敬來到伊拉克。我們在伊拉克沒有任何的企圖,我們只是想摧毀一個威脅,使伊拉克人民恢復(fù)對國家的控制。”布什的演講將美國出兵伊拉克包裝成解放伊拉克人民的高尚之舉,本質(zhì)上是給伊拉克人民加載道德債務(wù),賦予美國以道德債權(quán)人資格,從而為美國政府的戰(zhàn)爭選擇加注合法性,同時為戰(zhàn)后美國利益的實(shí)現(xiàn)準(zhǔn)備道德資本。在這里,道德債務(wù)成為處理國家共同體關(guān)系的價值工具。
通過償還道德債務(wù),正面樹立共同體道德形象,為共同體治理提供道義支撐,亦是實(shí)施共同體治理的經(jīng)常性選擇。類似的道德案例隨處可見,比如,1997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為19世紀(jì)土豆饑荒餓死無數(shù)愛爾蘭人道歉,2008年美國眾議院代表美國人民為非洲裔美國人及其祖先所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法的折磨而道歉,2008年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代表政府向澳土著族群上百年來蒙受的苦難道歉。這些道歉實(shí)質(zhì)上是通過歷史道德債務(wù)的靈性償還,以政府名義樹立國家道德形象,客觀上有利于國家共同體的有效治理。
通過道德債務(wù)的“轉(zhuǎn)移”與“遺忘”,將道德債務(wù)作為共同體治理的技術(shù)性工具,也是司空見慣的為政之道。“轉(zhuǎn)移”是共同體作為債務(wù)人將道德債務(wù)移位于他主體的倫理行為,道德債務(wù)的轉(zhuǎn)移本質(zhì)上可以實(shí)現(xiàn)對痛苦道德記憶的選擇性遮蔽,從而獲得內(nèi)心世界的道德救贖。比如,將大饑荒歸咎于自然災(zāi)害而不是人為因素,本質(zhì)上是將對饑餓死亡者的道德債務(wù)從執(zhí)政共同體轉(zhuǎn)移至非主體的自然,可以實(shí)現(xiàn)執(zhí)政共同體道德責(zé)任的卸載與集體性愧疚感的緩釋,并有利于共同體道德形象的保全。“遺忘”則是對共同體道德債務(wù)進(jìn)行有意識的信息封存,人為制造共同體的集體失憶,試圖讓道德債務(wù)在時間的流逝中走向消亡,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共同體精神世界的道德救贖。盡管“轉(zhuǎn)移”與“遺忘”最多只是實(shí)現(xiàn)共同體“免罪認(rèn)知”的技術(shù)性手段,只能暫時規(guī)避共同體道德債務(wù),并不能實(shí)現(xiàn)道德債務(wù)的真正清償,但客觀上可以維護(hù)共同體的價值穩(wěn)定,為共同體治理提供精神性保護(hù)。
注釋:
①?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戴光年譯,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5頁。
② [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莼等譯,商務(wù)印書館2012年版,第267頁。
③?? [德]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謝地坤等譯,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43、43頁。
④ [美]大衛(wèi)·格雷伯:《債:第一個5000年》,孫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
⑤ 陳霞:《道教公平思想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社會公平》,《宗教學(xué)研究》2000年第1期。
⑥ 李啟欣:《外國法制史研究文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頁。
⑦ [美]露絲·本尼迪克特:《菊與刀》,田偉華譯,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頁。
⑧ [德]阿克塞爾·霍耐特:《分裂的社會世界:社會哲學(xué)文集》,王曉升譯,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頁。
⑨ 李超:《對歷史負(fù)責(zé)的又一證明》,《人民日報》2013年6月5日。
⑩ 《勃蘭特那“驚世一跪”》,《新華網(wǎng)》2013年5月14日。
? [英]亞當(dāng)·斯密:《道德情操論》,蔣自強(qiáng)等譯,商務(wù)印書館1998年版,第184頁。
? 《舊約·創(chuàng)世紀(jì)》第3章《違背主命》。
? [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觀》,蔣慶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33頁。
?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傷痕:美國的冷戰(zhàn)歷史觀與世界》 (上),郭學(xué)堂等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313頁。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頁。
? [法]雷蒙·阿隆:《社會學(xué)主要思潮》,葛智強(qiáng)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頁。
? [美]邁克爾·桑德爾:《公正:該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頁。
? 石偉、閆現(xiàn)洋、劉杰:《對不公正歷史事件的情緒反應(yīng)——群體內(nèi)疚》,《心理科學(xué)進(jìn)展》2011年第2期。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重點(diǎn)研究基地重大項(xiàng)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shí)踐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研究”(16JJD710016)
B82
A
(2017)11-0005-06
羅明星,廣州大學(xué)政治與公民教育學(xué)院教授,廣東廣州,510006。
(責(zé)任編輯 劉龍伏)
- 社會科學(xué)動態(tài)的其它文章
- 家庭抗逆力研究回顧與本土化發(fā)展趨勢展望
- 后發(fā)國家生態(tài)文明理論的一部力作
——《生態(tài)學(xué)馬克思主義與后發(fā)國家生態(tài)文明》評介 - 變遷中的社區(qū)與創(chuàng)新性的治理
——評覃國慈主編的《“村轉(zhuǎn)居”社區(qū)治理研究》 - 創(chuàng)新型國家建設(shè)指向的科技文化研究
——第十四屆全國科技文化與社會現(xiàn)代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綜述 - 國家所有權(quán)與國有企業(yè)治理體系現(xiàn)代化
——“2017中國國有經(jīng)濟(jì)發(fā)展論壇”綜述 - 1950年前美國涉足南海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