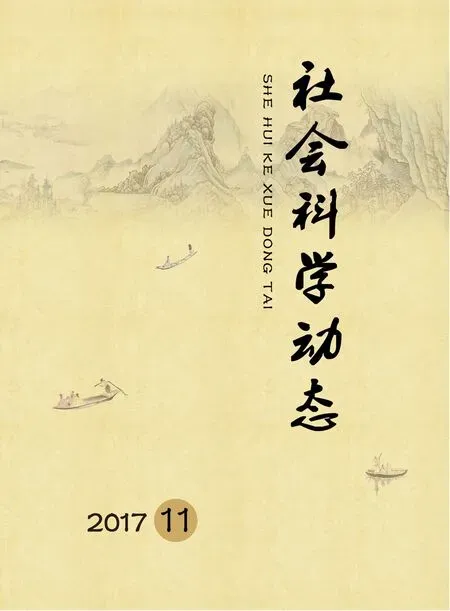國企分類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謝麗媛
前沿聚焦
國企分類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謝麗媛
在過去30余年的發展與改革中,國有企業依然未走出政府“父愛”的光環,未能實現政企分離、政資分離的改革目標,而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正是國有企業發展、改革中的核心所在。國有企業是政府在一般市場主體不愿或者是不能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領域內設立的企業,其本質上是政府職能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具有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屬性。正因如此,國有企業在發展中更易模糊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導致“國企失靈”,從而阻礙市場的發展。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改革的出發點,亦是提高經濟效率的重點。但過去“一刀切”的改革模式難以理順二者的關系,應當根據國有企業功能的不同分類治理才是界定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良策。具體言之,由于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特性,公益類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應由政府發揮主導作用;而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而言,政府應將其“還”給市場,由市場機制發揮決定作用。
政府;市場; 國有企業改革;公益類國有企業;商業類國有企業
一、引言
作為資源配置中最主要的兩種手段,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發展中歷久彌新且又無可避免的議題。從斯密提出的消極政府說,到米恩斯主張的政府全面干預學說,再到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市場自由運動,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于不斷被探索又一直未被厘清的過程。對于我國而言,從由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從提出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到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轉變,如何正確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始終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關鍵所在。
國有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關乎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好壞。科斯認為一般的企業是市場的替代物,而國有企業因其承載實現政府政治、經濟、社會目標的職能,同時又是政府的替代物,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的這種雙重性及其重要性使得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為模糊與復雜。在過去30余年的發展與改革中,國有企業依然未走出政府“父愛”的光環,未能實現政企分離、政資分離的改革目標,而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正是國有企業發展、改革中的核心所在。因此,本文認為在過去單一改革模式未見成效的情況下,應結合此次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根據國有企業不同的功能分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二、國企改革過程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變遷
1.國企改革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失衡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學領域一個經久不衰、爭論不休的話題。一般而言,二者之間是“失靈與干預”關系,市場在其發展過程中會因為某些原因而出現“失靈”,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則會干預市場活動;若政府發生“失靈”,則市場也會反過來予以干預。古典自由市場經濟學認為政府在干預市場時僅能作為“守夜人”,應當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最小化。而現代宏觀經濟學則是認為應當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政府的強干預能夠彌補市場失靈,同時亦能促進經濟的有效發展。當代市場經濟理論認為政府在干預市場時也會出現“失靈”,在政府失靈的情況下則需要重新引入市場機制。而施萊弗則是將政府比作為三只手,一是“看不見的手”,即政府提供最小化的公共產品并在法律的規制下保障契約的履行;二是“援助之手”,即是指政府促進商業繁榮,超越法律的規制保障契約的履行;三是“攫取之手”,即政府破壞了市場環境與契約的履行①。這些學說所爭議的焦點在于對政府干預市場時政府與市場邊界的界定不同,以及對政府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的認識不同。而這些學說對二者的關系存在一個共識,即政府的干預是為了彌補市場失靈,而國有企業正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一項制度安排。
國有企業大規模出現是在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一般的壟斷進入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市場經濟中的不正當競爭使得社會出現不穩定,國家開始對市場經濟活動進行全面的干預,并基于特定的社會目的設立了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為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而設立的企業。在政府的主導下,國有企業承擔起一般企業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從事的又關乎國民生存、社會經濟發展的生產經營活動,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從產權理論解釋,國有企業產生的原因是私有的產權交易成本過高而不能使其權利保持排他性,并且也有設立國有產權的必要,如社會的公共福利,此時則可以利用國有產權來替代市場在配置資源時產生的缺陷②。國有企業的產權特征就在于是由政府支配全部剩余收入,控制企業的生產決策③。國有企業是政府職能在經濟領域內的體現與延伸,它既具有一般企業的性質,又承載了政府職能,使得國有企業具有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屬性,由此社會經濟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反映在國有企業之中。
國有企業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者與市場的關系;二是政府作為監管者與市場的關系④。一方面,政府作為國有資本的所有權人,是市場的參與者,理應遵循市場規則;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的監管者,以謀求社會公共福利為目的,利用行政權力直接或者是間接干預市場來滿足公眾的需求。經濟主體與行政主體身份的碰撞,行政權與所有權的混合難分,使得國有企業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為模糊與復雜。國有企業出現的初衷是為了社會公眾的利益,彌補市場的缺陷,但由于在發展過程中政府無法準確界定與市場的邊界,導致國企壟斷、人員腐敗等不良現象出現。此時,國有企業不但不能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甚至還會阻礙市場的健康發展,即出現“國企失靈”。
國企失靈出現的原因在于政府未能準確定位自己所有者與監管者的身份,模糊了國有企業內政府與市場的界限,過多干預或者是錯誤干預市場。具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點:(1)政府錯位與缺位導致的資源配置不當。政府的錯位是指政府不正當地干預了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之一,政府本應在宏觀的層面干預資源配置,而微觀層面則是交給市場決定。而作為國企所有者,政府為國有企業的發展與運營直接干預市場活動,甚至不惜破壞市場規則,這種過度干預的行為扭曲該領域內的資源配置。相反,在本應由國企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的領域,由于政府的不作為或者是消極行為等“缺位”現象而導致資源配置的不利。(2)承載太多政府職能使得國企經濟效率低下。施萊弗認為國有企業是政府實現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國有企業對政治目標的過度追求導致了政府資源配置的不當⑤。作為企業,市場對其資源配置是以提升企業效率為目標,而國有企業因為具有經濟性的同時還具有政治性,過多承受政府職能會使得國有企業效率較低,難以在市場中繼續運營。政府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則會超越所有者的權限,利用行政權力不正當地干預市場。(3)缺乏激勵機制,企業運行代理風險增大。一般而言,國企的管理者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并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國企管理者是由政府官員兼任,國有企業無法根據自身運營情況擇優選擇管理者。由于缺乏對管理者的激勵機制,管理者任命的行政意義大于經濟意義,因此而產生的代理風險則需要由所有者和出資人承擔,對市場運行產生的潛在風險也需要其他市場主體共同分擔。鮑默爾則是從國有企業提供商品性質的角度,認為若公共產品交由私人企業提供,則會在追求個人利潤與社會利益之間產生生產者的道德風險,而國有企業是平衡這種風險的次優制度安排,因此會產生國有企業的低效率與弱激勵⑥。
2.國企分類而治是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良策
正如諾斯提出的國家悖論所言,政府既能夠通過產權保護促進經濟發展,亦能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⑦。國有企業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職能的體現,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因政府的不正當干預使得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發展的屏障。國企失靈并不意味著國家不需要國有企業,正由于在私人企業不能或者不愿但又關乎社會生計的公共產品、服務時,政府才出于公眾利益的考量設立國有企業。并且,國有企業還承擔著作為政府穩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渠道的職能。因此從市場發展、民生需求、社會穩定等多角度衡量,即使存在失靈的現象,市場中仍需要國有企業的參與,彌補國企失靈的路徑應當是通過國企的改革探索出能夠平衡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健康發展之路。
國有企業改革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世界各國至今不存在一個統一模式。以我國為例,國企改革先后經歷了“放權讓利”、“兩權分離”、“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調整國有企業經濟布局”等四個階段的改革⑧。我國國企改革雖然是以“建構性放權”為主要基調,試圖用市場構建來代替政府的直接管理,但予以細究之后可發現國企改革實際上是一個政府在“放權”與“收權”中多次搖擺不定的過程⑨。在國有企業發展中,政府意識到不應當將國企與市場隔離開完全握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應當還原國有企業“經濟主體”的本質,讓國有企業回歸市場,將國企打造為現代化企業,實現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這也就是政府“放權”的過程。但是在恢復國有企業“經濟主體”屬性的時候,特別是國企回歸市場后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進行的短期投資、重復建設、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質量下降等行為使政府感到不安,于是政府企圖通過“收權”對這些行為進行校正⑩。在“放權”與“收權”之間反復,不僅不利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更不利于市場的發展,而政府在國企改革中搖擺不定的行徑正是由于未能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所致。
在國企改革中,應當如何重新構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再像過去二分法將政府與市場放在對立面那樣簡單,國企改革不是簡單地將政府的權力過渡到市場,也不是簡單地構建“強市場與弱政府”的模式。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均存在有效與失靈的可能性,國企改革應當是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保證政府的干預是有益于利益均衡,兼顧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正如查爾斯·沃爾夫提出的“真實世界的經濟應是不完全市場和不完全政府之間的不完全結合”?。國企改革中理想的狀態是國有企業既能作為一個市場主體參與并促進市場的發展,又能繼續承擔政府的社會職能為社會提供能夠滿足需求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為了實現這一狀態,應當重新劃分政府與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活動范圍,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通過建立一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來轉變政府的職能,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建立一種市場與政府相互協調、相互均衡的改革模式?。
首先,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追逐的利益本位不同,承擔的社會功能與追求的經濟效益方面存在著差異。公益類國有企業主要是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是以社會利益為企業發展的利益本位;而商業類國有企業存在于充滿競爭的領域,它們相較于公益類國有企業,無需承擔過多的政府職能,而是需要通過追逐經濟效益完成國有資本增值保值的任務。
其次,不同類型國有企業所涉及的領域中市場作用不同。公益類國有企業存在的領域因為是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而具有特殊性,不存在或是鮮有商業競爭,難以形成市場價格,市場對于這類企業而言很難發揮出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根據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國有企業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有效形式,只有在市場失靈或者是市場不足的領域內才應該設立國有企業。我國的國有企業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力量,幾乎存在于各個行業領域。除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行業外,其他行業領域的市場能夠形成有效競爭與市場競價機制,除市場失靈以外政府不應當過多干預。因此,在競爭領域內存在的商業類國有企業遵循市場規律,由市場決定其資源配置。
最后,根據社會分工的有關理論,應當對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分類而治。阿林·楊格提出社會分工與市場規模是相互影響、雙向動態對稱的關系,市場規模的大小推動了社會分工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程度也決定了市場規模的大小?。我國國有企業的龐大規模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細化,社會分工的發展又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特點。不同特點的國企會逐漸演變為功能不同的國企,根據不同功能可以劃分為不同類型的國企,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所需要的市場化的程度亦不相同,因此,需要對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分類而治。
三、公益類國有企業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有三個:一是保護社會不受侵犯;二是保護社會上的個人不受侵害;三是建設并維護某些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公益類國有企業正是政府提供公共事業及設施的職能在經濟領域內的延伸,是為了在公共產品與服務領域內彌補市場缺陷而存在的。公益類國有企業是以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為主要經營活動,接受政府特殊制約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國有企業?。政府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公益類國有企業是政府實現該項職能的直接渠道,該類企業從根本上反映了國企的本質,以保障社會經濟發展,滿足國民生活生產需求為己任,以社會利益為本位,不追求經濟效益,這也將公益類國有企業與商業類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1.公益類國有企業應由政府主導
公益類國有企業本身不是市場的產物,是政府在市場自身功能失效的情形下為滿足公眾生活的需求,穩定社會的需要而設立的特殊企業,在該類企業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同于一般企業,政府對該類企業的干預強于其他企業,而市場在該類企業中不能發揮其資源配置的作用。
第一,公共產品的特性決定公益類國有企業應受政府的主導。首先,公共產品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是指“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等特征的產品”,消費的非排他性是指不能排除他人消費公共產品,非競爭性是指每增加一個消費者時,邊際成本為零?。正是由于這兩個特性,薩繆爾森也進一步提出與純粹私有產品的效益不同,公共產品的效益涉及到一人以上且不能分割的外部消費效果,常常要求集體出動,不應由私人提供?。其次,在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中認為公益類國有企業是在水電氣熱、公共交通與公共設施等行業和領域內提供產品與服務,這些行業內的產品與服務無不關乎國民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穩定。再者這些公共產品與基礎服務設施等投資回報的周期長且回報率較低,如果交由市場完全決定則可能會出現公共產品質量低、供給不足等情況,待市場失靈時再由政府介入干預的話,就意味著要動搖國民賴以生存的基礎,甚至需要付出社會混亂的代價。最后,政府主導該類企業能帶來規模效益。公共產品除了是國民日常生活所必須之外,也是提升整個社會生產經營效率的基礎。相較于市場,由政府主導能夠更好實現該類企業的社會效益,由國家經營公共產品與服務可以獲得規模效益,同時降低經營成本?。
第二,在公益類國有企業中市場不能發揮其作用。一方面,市場不是萬能的,在公益類國有企業涉及的領域內,由于周期長、回報率低等原因一般的市場主體不會主動愿意生產經營相關的產品與服務;或是因為關乎社會發展、國家安全的基礎,一般的市場主體不存在生產經營的能力。一般的企業不愿或者是不能從事生產或經營,政府則代替市場設立公益類國有企業彌補一般企業的空缺,公益類國企從根本而言不是市場的產物。因此很難在相關的領域內形成有效的市場機制,市場難以調節企業的運行,發揮其配置資源的作用,也就是說在這些領域內市場是失靈的。另一方面,相較于競爭,公益類國企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壟斷。由于提供產品與服務的特殊性,一般企業不存在從事相關行業領域的意愿或者能力,再從保障國民生活與社會穩定發展的方面考慮,通常由政府設立該類企業。公益性要求該類企業對社會效益的追求高于經濟利益,導致市場定價機制的失效,往往是由政府決定產品與服務的價格,經常會出現政策性虧損,一般的企業難以承擔。因此,在這些領域內一般企業難以與公益類國有企業形成有效競爭,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壟斷了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行業。但是這些壟斷都不是一定的,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開始有私人資本參與到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行業領域內。設立企業的資金來源,除由政府通過財政撥款、政策性銀行貸款等方式外,還可以通過PPP項目等方式向社會籌集私人資本?。
2.公益類國有企業中政府干預的維度
公益類國有企業雖然是由政府主導的企業,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對該類企業是完全主導,市場是完全失效的?。公益類國有企業中社會目標高于其經濟目的,但不能否認其經濟性的存在,也不能完全漠視市場的作用,過度夸大政府的權力。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界定其實是政府權力應當如何界定的問題,公益類國有企業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就取決于政府對該類企業生產經營的參與程度和控制程度。
首先,政府對公益類國有企業應當是以宏觀調控為原則,僅在特定方面施加強干預。政府的干預需要為該類企業確立以保障國民生活、社會發展等社會效益為首要目標,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基本原則,以確保企業提供的公共產品、服務的質量滿足需求為政府干預的出發點,制定公益類國有企業提供的公共產品、服務的質量標準。
其次,該類企業的進入與退出市場應由政府管制。在市場經濟中,企業進入或者退出市場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作為監管者一般很少干預。因涉及到社會公眾的利益,此類企業的準入與退出應當受到政府的特別管制?。不是任何企業都具備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與資格,政府作為“把關者”應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來確保接受委托的國有企業有能力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
再次,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定價權應當歸屬于政府。一般而言,決定產品的價格是企業享有的自主權力,企業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自行決定。但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公共產品與服務被壟斷了,市場在不能發揮其調節作用的同時定價機制也失效了,為避免濫用壟斷地位肆意抬高或者是制定不合理價格的現象發生,政府應當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價格實行嚴格的管制。
最后,公益類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命也應受到政府的管制。由于企業特性使然,該類企業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是更加注重社會效益,相比于市場化的人事任命,由政府直接任命或罷免企業負責人更有助于公益類國有企業職能的實現。除此之外,政府不應當在其他方面實施強干預,應由企業根據市場的調節自主決定。
公益類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應由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強化政府的干預,而不是交由市場決定。但是政府的強干預不能是任意的,亦不能沒有限度,政府對公益類國有企業干預的范圍應當通過法律法規來予以規范和約束。但是由于公益類國有企業的特殊性,現行立法模式下的公司法、行政法、企業法均難以兼容,應當在單獨立法設計公益類國有企業相關制度時明確政府干預的限度。
四、商業類國有企業改革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1.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
國有企業的另外一種類型是商業類國有企業,該類企業以營利為目標,主要在競爭領域內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國有資本的增值保值。西方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認為在競爭領域內不應存在國有企業,而由于特定的經濟發展背景,我國在大量的競爭領域內設立了國有企業。與公益類國企不同的是,商業類國企并未承擔過多的政策目標,它設立的目的在于追求經濟利益,而不是社會效益。換言之,商業類國企的存在并非是政府職能的延伸,此時政府與企業之間應當是一種單純的投資關系,政府不應對其有任何的政策優惠或者是施加任何的政策負擔。商業類國有企業與一般企業無異,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生產經營,參與市場競爭,接受市場的調節。對于這類國有企業,政府只能是基于出資人的身份參與其經營管理,而不能使用行政權力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對于商業類國企而言,它的雙重屬性中的經濟屬性占有主要地位,而承載的社會政治屬性則被弱化。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將該類企業“還”給市場,使其逐漸回歸市場主體的本質,按照市場化的模式實行商業化運營,自主生產經營,根據市場的規則實行優勝劣汰,有序地進入或者是退出市場,政府不應當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運營。
2.國企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設立有助于理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正如上述,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的運營,市場應當發揮決定作用,而政府不應利用其行政權力干預,而對于公益類國企應由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但由于我國國有企業發展過程中政府一直是將公益類國企與商業類國企混合治理,政府直接參與到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雖一直進行政企分離、政資分離的改革,但也未見其成效。政府的干預對所有國有企業而言已是屢見不鮮,政府要將商業類國有企業歸還給市場需要有一條有效的路徑,否則也只是一紙空談。
商業類國企的市場化首先則是需要在政府與企業之間設立一個中介機構,將政府與企業分離,企業的生產經營交由市場調節,而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無疑是一個適當的中介分離機構。公益類國企中由于自身的特性,需要政府的強干預,采用的是政府直接管理的模式,因此不宜設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在商業類國企中引入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構建政府出資人代表—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具體企業的三層結構。在此結構中,政府不再參與國有企業的運行,由國有投資運營公司代替政府作為出資人參與企業的運營,而被投資的國有企業則負責具體的生產經營?。國有投資運營公司作為一個緩沖機制,能夠減少政府不正當的過度干預與監管,減少政府對這一領域內市場機制的扭曲與破壞。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中介機構,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將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行政權力轉變為它對國有企業產生的市場權力,從而理順商業類國企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商業類國企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與一般企業無異,應遵循市場的調節,政府不應使用行政權力過多干預。經過長期政企難分的發展后,政府要將商業類國企“還”給市場并非易事,應引入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中介結構,在分離政府與企業的同時理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學界爭論不息的焦點,亦是組織市場活動的起點。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是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而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厘定國有企業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僅關乎國有資本的增值保值,更能對國民生活、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的穩定產生重大影響。國有企業既是從事生產經營的經濟主體,又是政府職能在經濟領域內的延伸,這種雙重屬性導致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更為復雜,傳統“一刀切”的發展模式更是無法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根據國有企業功能的不同分類而治才是界定二者關系的良策。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而言,政府應當進行有限度的強干預,由政府主導企業的生產經營;而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而言,政府應當將企業“還”給市場,由市場機制發揮決定作用。
注釋:
① T.Frye and A.Shleifer: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2),pp.354-358.
② 寧金成:《國有企業區分理論與區分立法研究》,《當代法學》2015年第1期。
③ 雅諾什·科爾奈:《社會主義體制》,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版,第68—126頁。
④ 劉尚希、吉富星:《公共產權制度:公共資源收益全民共享的基本條件》,《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4年第5期。
⑤Shleifer Andrei,Robert W.Vishny,Politicians and Firm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pp.995-1025.
⑥W.J.Baumol,Toward a Theory of Public Enterprise,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1984,12(1),pp.13-20.
⑦ 道格拉斯·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54—165頁。
⑧? 陳其霆:《中國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 95—116頁。
⑨ 蔡長昆:《從“大政府”到“精明政府”:中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邏輯——交易成本政治學的視角》,《公共行政評論》2015年第2期。
⑩ 顧功耘、胡改蓉:《國企改革的政府定位及制度重構》,《現代法學》2014年第3期。
? 李東升、杜恒波、唐文龍:《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利益機制重構》,《經濟學家》2015年第9期。
? 查爾斯·沃爾夫等:《市場,還是政府:不完善的可選事物間的抉擇》,重慶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 鄔德政、劉鴻淵、段龍龍:《政府職能轉型視角下國企改革的目標價值取向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
?A.A.You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Economic Journal,1928,38(152),pp.527-542.
?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 1997年版,第252—253頁。
?P.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36(4),pp.387-389.
?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 (上),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4頁。
?駱梅英:《民營化后公用事業企業的性質之辨——基于案例的比較觀察》,《法治研究》2015年第1期。
? 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新時期新國企的新改革思路——國有企業分類改革的邏輯、路徑與實施》,《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7年第5期。
?W.Friedmann,The Legal Status and Organizaiton of the Public Corporation,Law and Contemporary,1951,16(4),pp.576-593.
? 胡改蓉:《論公共企業的法律屬性》,《中國法學》2017年第3期。
? 程民選、王罡:《關于公益性國有企業的理論探討》,《當代經濟研究》2014年第3期。
? 王曙光、王天雨:《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人格化積極股東塑造及其運行機制》,《經濟體制改革》2017年第3期。
? 柳學信:《國有資本的公司化運營及其監管體系催生》,《改革》2015年第2期。
F271
A
(2017)11-0035-05
謝麗媛,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上海,201620。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