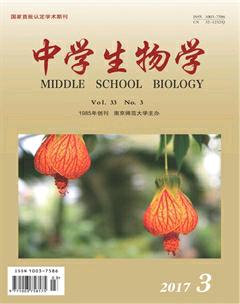再談從“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
顧軍
“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是新課程改革以來的一個(gè)時(shí)尚用語。一直以來,課程專家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教材編制的目的不是為教師提供“法定”的文件,讓教師屈從于教材的要求,而是為教師提供可利用的課程資源。細(xì)究一下,教教材和用教材教的內(nèi)涵,許多教師說不清也道不明,于是帶來的結(jié)果便是:“用教材教”成了一句時(shí)髦用語,“教教材”卻是“桃花依舊笑春風(fēng)”。
“用教材教”就是教師依據(jù)課程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自身的實(shí)踐與研究,自主領(lǐng)會(huì)、探討課程與教學(xué),把教材作為一種重要的“媒介”加以利用的教學(xué)行為。因此,教材是教師要去加工和創(chuàng)造的材料,只有根據(jù)學(xué)生的學(xué)情和教師對(duì)教材的深切領(lǐng)悟進(jìn)行再度開發(fā),才能找到適合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切入點(diǎn)。下面結(jié)合案例分析,再談從“教教材”走向“用教材教”。
1 “用教材教”的方式
1.1 精心組織學(xué)生與文本的“對(duì)話”
“對(duì)話是優(yōu)秀教學(xué)的一種本質(zhì)性標(biāo)識(shí)”,新課程認(rèn)為“對(duì)話”是教學(xué)活動(dòng)的重要特點(diǎn)。實(shí)施“用教材教”,就要求教師精心組織學(xué)生與文本展開“對(duì)話”,以使靜止的知識(shí)素材成為學(xué)生建構(gòu)的真正知識(shí)。教師可以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優(yōu)質(zhì)資源,創(chuàng)設(shè)情境,引導(dǎo)激發(fā)學(xué)生與教材“對(duì)話”的興趣和需要,使之樂于“對(duì)話”。
例如,人教版必修2教科書中“遺傳因子的發(fā)現(xiàn)”一節(jié)教學(xué),通過“孟德爾一對(duì)相對(duì)性狀的遺傳試驗(yàn)結(jié)果、對(duì)分離現(xiàn)象的解釋、測(cè)交試驗(yàn)驗(yàn)證、基因分離定律的本質(zhì)、分離定律在實(shí)踐中的應(yīng)用”等內(nèi)容的學(xué)習(xí),使學(xué)生了解科學(xué)研究的一般思路就是:觀察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提出假說—設(shè)計(jì)實(shí)驗(yàn),驗(yàn)證假說—分析歸納,尋找規(guī)律。同時(shí),讓學(xué)生懂得孟德爾成功歸因于篩選實(shí)驗(yàn)材料、選擇研究方法,使學(xué)生認(rèn)識(shí)到孟德爾使用豌豆之魅力:自然狀態(tài)為純種,雜交實(shí)驗(yàn)既可靠,性狀又易于區(qū)分;而且先從一對(duì)相對(duì)性狀入手,以便在紛繁復(fù)雜的局面中覓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并用統(tǒng)計(jì)學(xué)的方法對(duì)實(shí)驗(yàn)結(jié)果進(jìn)行分析。教師也要讓學(xué)生了解孟德爾所處時(shí)代的理論基礎(chǔ)和技術(shù)條件,以及孟德爾研究歷程中的挫敗感。
學(xué)生在與文本的對(duì)話中被“激活”,并以學(xué)習(xí)主體的角色參與到教學(xué)活動(dòng)中去。同時(shí),師生之間、生生之間、師生與文本之間展開“對(duì)話”,以達(dá)到平等的溝通、知識(shí)的分享、深入的思考,最后實(shí)現(xiàn)“共同的了解”。
1.2 對(duì)教材加以適當(dāng)?shù)摹稗D(zhuǎn)化”
教材僅是“范例”,只是為教學(xué)提供了藍(lán)本,要達(dá)成教學(xué)目標(biāo),就還需要教師的教學(xué)活動(dòng)來加以“轉(zhuǎn)化”。有時(shí)學(xué)生在閱讀教材時(shí),可能會(huì)感到不易理解,而教材本身在反饋、調(diào)整等功能設(shè)計(jì)上有缺陷,這就要求教師靈活地調(diào)整教學(xué)內(nèi)容和講授技巧,使教材上的知識(shí)變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例如,人教版必修1教科書“細(xì)胞器——系統(tǒng)內(nèi)的分工合作”一節(jié),教材列出若干個(gè)細(xì)胞器的彩圖,僅配以簡(jiǎn)單的文字說明,內(nèi)容抽象,記憶瑣碎枯燥。教學(xué)中我們學(xué)科組老師將幾種細(xì)胞器自編原創(chuàng)成趣味謎語,讓學(xué)生猜測(cè)它們各是哪種細(xì)胞器。例如,“身披兩層膜,內(nèi)膜面積闊;分解有機(jī)物,產(chǎn)能特別多”(線粒體);“由膜圍成網(wǎng),面積它最廣;還有附著體,有粗也有光”(內(nèi)質(zhì)網(wǎng));“由膜構(gòu)成囊,層層堆疊放”(類囊體);“兩組小短棒,相互垂直放;動(dòng)物細(xì)胞有,植物看情況”(中心體)。學(xué)生在趣味語言情景中掌握細(xì)胞器的名稱和相關(guān)功能。
1.3 啟發(fā)學(xué)生主動(dòng)參與,讓思維“活化”
任何教材在講述知識(shí)時(shí),往往只能從某一個(gè)角度、某一種視野來進(jìn)行敘述與分析,但是真正的活的知識(shí),是需要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去分析、掌握和運(yùn)用。因此,教師在講授時(shí),就可以考慮“另辟蹊徑”,多換幾個(gè)角度,既能防止思維定勢(shì),也能逐步提升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能力,讓思維“活化”。
例如,人教版必修3“種群數(shù)量的變化”一節(jié)的復(fù)習(xí)課教學(xué),嘗試建構(gòu)種群增長(zhǎng)的數(shù)學(xué)模型。教材從問題探討欄目“細(xì)菌的增長(zhǎng)規(guī)律”引入,闡述“J”型曲線的形成到數(shù)學(xué)模型構(gòu)建的程序的呈現(xiàn)。其實(shí),教材內(nèi)容并未真正意義上建構(gòu)種群增長(zhǎng)的Nt=N0λt這一數(shù)學(xué)模型。在理想狀態(tài)下,由一個(gè)細(xì)菌開始繁殖,種群數(shù)量呈指數(shù)形式遞增,公式表示為Nt=2n。在細(xì)菌實(shí)際的種群中,起點(diǎn)數(shù)量不是一個(gè),而是多個(gè)時(shí)的公式如何?細(xì)菌的增長(zhǎng)率為100%時(shí),公式又是如何?其他種群的增長(zhǎng)率不是100%,而是β時(shí)(β表示增長(zhǎng)率=出生率-死亡率),公式又是如何?學(xué)生在討論的基礎(chǔ)上分別得出:Nt=2n→Nt=N02n→Nt=N0(1+100%)n→Nt=N0(1+β)n。圍繞Nt=N0(1+β)n這一公式,學(xué)生熱烈討論β值不變時(shí),種群的數(shù)量以一定的倍數(shù)增長(zhǎng),第二年是第一年的λ=1+β倍,t年后該種群數(shù)量的公式模型就可以表示為Nt=N0λt。教師轉(zhuǎn)換思維角度,通過討論質(zhì)疑、探究數(shù)學(xué)規(guī)律、解決實(shí)際問題,以全新思路嘗試建構(gòu)種群數(shù)學(xué)模型的修訂方法,讓學(xué)生體驗(yàn)由具體到抽象的思維過程。
1.4 了注意教學(xué)知識(shí)的延伸與拓展,回歸“生活化”
新課程教學(xué)應(yīng)突破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教材教學(xué),必須注意開發(fā)與利用多種多樣的課程資源,比如充分發(fā)揮學(xué)校實(shí)驗(yàn)室、專用教室的作用,教師在教學(xué)過程中積極引導(dǎo),就學(xué)生感興趣、且能夠探究的一些學(xué)習(xí)內(nèi)容,組織學(xué)生深入地研究,利用資料搜集、觀察實(shí)驗(yàn)、走訪調(diào)查、外出實(shí)習(xí)等方法,使學(xué)生的理解更加深刻透徹,進(jìn)一步培養(yǎng)他們的學(xué)習(xí)興趣甚至是對(duì)未來的職業(yè)規(guī)劃。
例如,筆者的學(xué)校IB課程班的學(xué)生在完成教材《生殖與胚胎》的學(xué)習(xí)后,來到婦幼保健院的檢驗(yàn)科、B超科甚至產(chǎn)科實(shí)習(xí)體驗(yàn)。B超可以直觀地反映胎兒在媽媽肚子里的情況,使醫(yī)生了解胎兒階段性的生長(zhǎng)情況。跟隨醫(yī)生的主要工作內(nèi)容是做孕婦排畸檢查,目的是觀察寶寶五官、四肢以及內(nèi)部器官有無異常。同時(shí)需要記錄寶寶的各項(xiàng)指標(biāo),比如雙頂徑、頭圍、羊水指數(shù)等詳細(xì)的數(shù)據(jù)。學(xué)生如此近距離地參與到醫(yī)護(hù)人員的工作中,他們會(huì)更多地了解到醫(yī)生的不易、白衣天使用自己的付出和敬業(yè)踐行著自己的使命。基于學(xué)生已有的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又實(shí)踐所學(xué)的知識(shí)技能,與新課程倡導(dǎo)的教學(xué)理念一脈相承。
2 “用教材教”遵循的基本原則
2.1 尊重教材的基本框架
教材是眾多專家依據(jù)課程標(biāo)準(zhǔn)編寫的嘔心力作。生物學(xué)科的內(nèi)容大體是闡述生物學(xué)現(xiàn)象和事實(shí)、生物學(xué)概念、原理以及相關(guān)的科學(xué)方法,并形成一些至關(guān)重要的觀點(diǎn)和態(tài)度。所以尊重并理清教材的脈絡(luò)尤為重要,便于教師在內(nèi)容上整體概括,并對(duì)整個(gè)教材體系了然于胸,也便于學(xué)生建構(gòu)本模塊的知識(shí)系統(tǒng)。
例如,人教版《選修1·生物技術(shù)實(shí)踐》從教材目錄上可以看出,本模塊的內(nèi)容脈絡(luò)非常清晰,可以概括為: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從生活到科學(xué)、從微生物到動(dòng)植物、從培養(yǎng)技術(shù)到生化分析。從每一個(gè)專題內(nèi)容的結(jié)構(gòu)分析,可以看出每部分的課程追求和編寫意圖:“課題背景”引領(lǐng)學(xué)生聯(lián)系技術(shù)與生產(chǎn)生活;“基礎(chǔ)知識(shí)”呈現(xiàn)原理與方法;“實(shí)驗(yàn)設(shè)計(jì)”為學(xué)生自行設(shè)計(jì)實(shí)驗(yàn)提供基本信息資料,“操作提示”指導(dǎo)實(shí)驗(yàn)操作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分析評(píng)價(jià)”倡導(dǎo)多元性評(píng)價(jià)和理性反思,“課題延伸”進(jìn)行知識(shí)與技能的縱向提升等。
2.2 “用教材教”的關(guān)鍵是“用”
“用教材教”首先是“用”,而不是拋開教材另搞一套。教材是最基本的課程資源,是課堂教學(xué)的藍(lán)本和基本素材。若教師能深度解讀。教師用好教材會(huì)更遵循和貼近學(xué)情,從而促進(jìn)教學(xué)的有效。那么,如何“用”教材?教師要努力理解和領(lǐng)會(huì)教材的設(shè)計(jì)理念及教學(xué)思想,把握其特點(diǎn),使教材所潛藏的資源得到較好的挖掘。
例如,有關(guān)“轉(zhuǎn)錄”的過程,教材主要是以“DNA為模板轉(zhuǎn)錄RNA的圖解”呈現(xiàn),以圖解方式,分步注解過程,教材有很明確的闡述。教學(xué)過程中,教師利用教材強(qiáng)調(diào):所謂“轉(zhuǎn)”是指DNA上堿基的特定排列順序反映到了RNA上;所謂“錄”是指刻錄忠實(shí)于原來的遺傳信息。基因表達(dá)的嚴(yán)謹(jǐn)是受模板的制約、RNA聚合酶的催化、嚴(yán)格的堿基互補(bǔ)配對(duì)原則的限制,確保了遺傳信息傳遞的準(zhǔn)確無誤,從而造就了基因表達(dá)過程的有序并創(chuàng)造出絢麗多彩的生命體。
2.3 “教”的方式仍以“講授”為主
《基礎(chǔ)教育課程改革綱要》客觀指出,教學(xué)“要處理好傳授知識(shí)與培養(yǎng)能力的關(guān)系”。在“用教材教”中,如果說“用教材”是手段的話,那么“教”應(yīng)該就是目的。因此最主要、最適合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教”的方式還是教師的“講授”。事實(shí)上,“講授”與“探究”并不矛盾,高明的“講授”必含有“探究”的成分,而科學(xué)的“探究”也離不開教師的“講授”。
教材中出現(xiàn)的概念、術(shù)語,往往給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帶來不少的困難。課程標(biāo)準(zhǔn)中規(guī)定的生物核心概念、容易混淆的原理,必須通過教師的講解,讓學(xué)生進(jìn)行辨析,明確概念原理的內(nèi)涵,如細(xì)胞周期、光合作用、植物向光性原理、cDNA文庫與基因組文庫、啟動(dòng)子與終止子等;對(duì)于教材中表述模糊的問題,講清概念的實(shí)質(zhì),如單克隆抗體制備過程中雜交瘤細(xì)胞融合培養(yǎng)兩次篩選的目的、受精及受精完成的標(biāo)志等。
強(qiáng)調(diào)“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并不是要將兩者截然對(duì)立起來。“用教材教”的理念至少表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教材仍然是教學(xué)的重要“媒介”;教材還是要教的,如果盲目追求“自主學(xué)習(xí)”或“超越文本”,教師不注重帶領(lǐng)學(xué)生走進(jìn)教材,這樣的教學(xué)態(tài)度并不可取,也是對(duì)“用教材教”理念的誤讀。
參考文獻(xiàn):
[1] 李鋼.從“教教材”到“用教材教”[J].廈門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5,7(4):69.
[2] 蘇軍.“教”教材與用教材“教”[J].上海教育,2003,(7B):50.
[3] 吳舉宏.“選修1·生物技術(shù)實(shí)踐”的教學(xué)建議[J].生物學(xué)通報(bào),2009(6):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