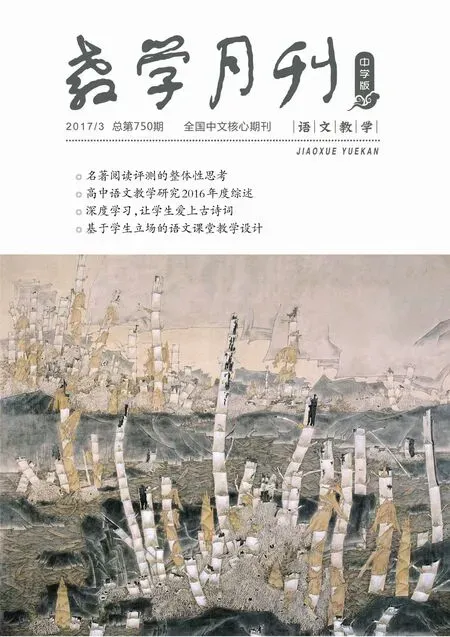名著閱讀評測的整體性思考
章新其
(杭州市江干區教育發展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20)
名著閱讀評測的整體性思考
章新其
(杭州市江干區教育發展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20)
編者按:名著閱讀教學的真正落實和語文核心素養的真正落地,有賴于有效的名著閱讀測評方法的導引和教師閱讀指導的切實有效。本期“專題”聚焦名著閱讀的評測與教學指導,對基于現實情境的名著閱讀評測途徑和方法、中考名著閱讀試題的命制導向、高效名著閱讀指導應具備的要素等問題作了深入闡述。
以當前的教學邏輯,用名著閱讀的評測來撬動閱讀教學的改進,可能是條面向現實的好途徑。名著閱讀的評測應站在“閱讀”的角度去審視,要體現閱讀追求、注重閱讀指導、關注文本特質,并倡導“主題閱讀”。基于閱讀的本質及其表現的特征,結合當前我國學業評價的基本狀況,名著閱讀評測可以從表現性評價和應試型評價兩個維度去考慮。
名著閱讀;閱讀評測;閱讀教學
語文核心素養的實現,有賴于名著閱讀(或稱“整本書閱讀”)的推進,這應該毋庸置疑。然而,當前社會對語文學科存在的諸多質疑中,考試評價首當其沖;又以名著閱讀難以評測,不能有效進入考試試卷而無法導向語文教學,更成為人們詬病的焦點。
因此,基于現實情境探索名著閱讀的有效評測途徑和方法,以確保名著閱讀教學的真正落實和語文核心素養的真正落地,是語文教學實踐的關鍵性任務。對廣大語文教師來說,這其中要解決包括目前的單篇閱讀評測有哪些欠缺、為什么要倡導整本書閱讀、名著閱讀評測有哪些類型以及該如何評測等多方面的問題。
一、教學導向的現實必要
名著閱讀評測淪陷在教學的現實困境里。當前的語文測試中,名著閱讀內容的評測應該說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分值普遍不高,品質也良莠不齊;屬于語文能力關鍵性維度的閱讀能力的測試,往往借助于課外短篇閱讀材料。反映到教學中,為獲得考試的現實效益,普通語文教師自然會覺得整本書的名著閱讀過程欠簡約,且效果未必明顯,于是,“千字文”理所當然成為學生閱讀和練習的主要類型。況且教科書也以語文知識和能力來串聯若干短小篇章組成單元,因教學指向考試評測的緣故,教師就會簡單追求單篇短文的精細解讀。這樣,課堂強調單篇課文的精讀,加上課外閱讀試題的套路化訓練,極大地消耗了學生語文學習的時間和精力,更遑論整本書的名著閱讀了。
當前閱讀評測的命題局限于單篇短文,這種精致化的閱讀測試從測量效果來看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精致化的短篇閱讀測試是典型化閱讀測試,所選文本是命題者精心挑選、能體現命題者意圖的,有時為了測試方便,命題者還會對文章加以改編,這與生活中的真實閱讀不完全等同;而生活的常態閱讀,特別是整本書的名著閱讀,中間的過程要復雜得多。盡管精致化的測試型閱讀包含了閱讀的一些基本技能,但它畢竟無法涵蓋長篇巨著所體現的多樣性和綜合性。另一方面,名著閱讀過程所表現出來的閱讀習慣、閱讀方法、閱讀意志力以及閱讀思維力,都是精致化短篇閱讀無法企及的。
缺乏實質性的名著閱讀測試,對當前的閱讀教學產生了令人遺憾的負面導向;沒有充分的整本書的名著閱讀經歷,極大地限制了學生閱讀能力的發展。《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一再強調要“擴大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1]十幾年來,這樣閱讀的大好局面總是難以形成。美國學者斯蒂芬·克拉生通過大量實踐研究得出這樣的觀點:閱讀得比較多的人,閱讀力和寫作力都比較好,并且愛閱讀的人比較善于思考。[2]根據曹勇軍老師的美國教育考察交流報告,美國學生3~4周要完成一本書的閱讀[3],而這是我們普遍沒有做到的。2016年秋季使用的“部編”語文教科書格外注重往課外名著閱讀延伸,建構了由教讀到自讀再到名著閱讀的“三位一體”的閱讀課程結構,為語文教學指出了一條明晰的路徑。葉圣陶先生曾經對教材是用“單篇短章”還是用“整本的書”作過透徹而清晰的分析,最后總結道:
國文教材似乎該用整本的書,而不該用單篇短篇,像以往和現在的辦法。退一步說,也該把整本的書作主體,把單篇短章作輔佐。……就學生方面說,在某一時期專讀某一本書,心志可以專一,討究可以徹底。在中學階段內雖然只能讀有限的幾本書,但是那幾本書是真正專心去讀的,這就養成了讀書的能力;憑這能力,就可以隨時隨地讀其他的書以及單篇短章。并且,經常拿在手里的是整本的書,不是幾百言幾千言的單篇短章,這么習慣了,遇見其他的書也就不至于望而卻步。還有,讀整部的書,不但可以練習精讀,同時又可以練習速讀。如此說來,改用整本的書作為教材,對于“養成讀書習慣”,似乎切實有效得多。[4]
以當前的教學邏輯,用名著閱讀的評測來撬動閱讀教學的改進,可能是條面向現實的好途徑。盡管有教師認為,學生的大量名著閱讀應該轉化成真實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然后在我們的測試中展現這種能力,但這種說法偏離了我們今天探討的話題,因為它既不能導向我們的名著閱讀教學,也無法推動考試命題的發展。因此,作為語文教育的研究者和實踐者,我們絕對不能回避名著閱讀的評測問題,更應該迎難而上,在努力地探索中尋出可行之路,讓語文教學更加健康地發展。
二、評測應該遵循的原則
名著閱讀的評測工具應該如何制作?這是一個困擾很多語文教師的關鍵問題,它直接指向閱讀教學的形態和效益。名著閱讀評測的困難,既有作品長度、厚度的因素,也有規定的閱讀數量多、試題命制本身復雜等因素。但既然把名著閱讀放在“閱讀”的范疇,把名著閱讀評測放在考查學生“閱讀能力”的目標下,我們就應該站在“閱讀”的角度去審視。
(一)名著閱讀評測要體現閱讀追求
當前的名著閱讀內容在主要的測試工具中,其地位稍顯尷尬。多數試卷把名著閱讀的考查內容放在“知識積累”中,這就涉及考查的目的到底是不是指向“閱讀能力”的問題。客觀分析,放在“知識積累”板塊并非完全不能考查學生的閱讀情況,但終究沒有完全觸及“閱讀”的根本屬性。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一些試卷過于注重對名著表層信息的識記性考查。應該說,名著閱讀中如主要人物、關鍵情節等一些重要的表層信息,是學生深入閱讀的基礎,理應成為考查的內容。但一味考查這些內容,容易將學生的閱讀導向膚淺的死記硬背,這不僅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也偏離了閱讀的本質。
美國的艾德勒和范多倫在《如何閱讀一本書》中清楚地指出:“不管你學到的是有關這本書的知識或有關世界的知識,如果你運用的只是你的記憶力,其實你除了那些訊息之外一無所獲。你并沒有被啟發。”[5]14因而,基于對名著閱讀理解基礎上的體驗、感悟、思考,應該是文學名著閱讀的價值追求,也是名著閱讀評測的基本方向。下面這道2016年溫州市中考題較為典范:
在《三國演義》中,劉表和呂布對劉備有不同的評價,你更贊成誰的觀點?結合小說相關情節回答。
①玄德仁人也。——劉表
②是兒最無信者!——呂布
該題考查學生對《三國演義》中“劉備”這一重要人物形象的理解把握,不瑣碎,不機械,特別是利用作品中其他人物對于劉備的對立性觀點作為切入點,能引發學生沉入作品進行全方位地分析和評價,其中滲透著學生主動參與的批判性思維。對文本信息的認知、理解、歸納等是閱讀能力最基礎的部分,不過更重要的是閱讀者對作品的獨立反思及在此基礎上所作出的自主性和批判性表達。據了解,《PISA2018設計草案》就在原本強調“閱讀參與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批判性閱讀”與“批判性思考”等概念,這將會越來越深刻廣泛地影響全球語言教育和語言測試。閱讀是讀者主動與作品建立起價值聯系的一種持續的活動過程,是讀者基于其獨特生命體驗與文本信息開展積極互動和交流的精神現象。在這個過程中,閱讀個體彰顯其獨立思考的自覺意識和自主表達的重要能力。名著閱讀的評測尤其要關注這一點。
(二)名著閱讀評測要注重閱讀指導
某些反對將名著閱讀內容納入評測范疇的人士認為,閱讀是學生自己的事情,只有閱讀者主動開展的閱讀活動才能體現閱讀的真正價值;評測以試題(或稱學習任務)的形式呈現,干擾了學生的閱讀主動性,或將扼殺學生的閱讀興趣。其實這是無稽之談。《如何閱讀一本書》中就特別強調:“自我發現的學習方式就是沒有老師指導的方式,而被引導的學習就是要旁人的幫助。不論是哪一種方式,只有真正學習到的人才是主動的學習者。”[5]15簡單地將“自我發現的學習”認作是主動的,“被指導的學習”是被動的,很可能會造成謬誤。
其實,我們的初中學生仍然是初級閱讀者,他們還不知道如何做一個自我要求的閱讀者,不知道如何將精神集中在他們所閱讀的作品上,他們即使有意愿保持主動的閱讀,卻缺乏技巧與能力。幾次閱讀敗下陣后,學生就會在挫敗中感到沮喪,進而開始厭倦閱讀。所以,介入學生的閱讀,以一定的方式開展閱讀指導,是學生迫切的需求,其中最常見的閱讀指導方式就是教師開發的“閱讀任務”。學生因為有具體的閱讀目標,所以才會聚集閱讀的精神;閱讀任務會無形地提示閱讀路徑和序列,所以學生閱讀時會收獲閱讀技巧。這樣,學生就自然能保持主動的閱讀,開展與文本之間的互動交流。思考本身就是主動閱讀的一部分!而名著閱讀評測中的試題,說到底是“閱讀任務”的一種情境體現。它的意義不僅是評測學生的閱讀情況,更大的意義在于指引我們的名著閱讀教學以“閱讀任務”指導、促進學生如何開展深入閱讀。關于這一點,我們做得比較普遍,這里只是強調以科學性試題(或閱讀任務)來評測名著閱讀的合理性。
關于名著閱讀評測,我們還要特別注意往閱讀策略和方法上去探索。葉圣陶先生、王榮生教授對閱讀策略、方法都相當重視,后者更是用簡明扼要的語言指出:閱讀能力的核心就是閱讀方法。[6]閱讀教學要將閱讀策略和方法放在焦點位置,相對應地,名著閱讀評測也應該要指向閱讀策略和方法,這方面一直是我們的薄弱環節。最新使用的“部編”初中語文教科書的閱讀課程結構,就以閱讀策略和方法為其中的一條線索,這也觸發了語文教師對名著閱讀評測的再思考。某地七年級的期末名著閱讀測試,考查學生對《朝花夕拾》的閱讀情況,首先引導學生明確回憶性散文的閱讀要關注文中的兩個“我”——寫作時“現在的我”與回憶中“過去的我”,然后要求學生閱讀節選篇章、回答相應題目,命題者設置了一道引導學生探討閱讀策略、方法的試題:
讀《朝花夕拾》里的文章,有時會讀到一個天真的小魯迅,有時會讀到一個深沉的大魯迅。請你參與“探究《朝花夕拾》中‘小魯迅·大魯迅’”的專題閱讀活動,幫助設計閱讀方案,把下面表格填寫完整。

閱讀任務選篇閱讀小組交流過程記錄[談發現] ·小明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發現:百草園之趣、三味書屋之趣讓小魯迅擁有快樂的童年。·諾諾讀《無常》,發現:孩子對活無常的喜愛,讓“大魯迅”從中看到了人間公道的缺失,引發了他對“正人君子”的諷刺。·我讀《 》,發現:從篇到本探究魯迅[提建議]要探究《朝花夕拾》中“小魯迅·大魯迅”,閱讀時,從內容和方法上我有以下建議:
這道試題明顯有別于傳統的閱讀理解類試題,不僅考查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和感悟,還考查學生是否掌握閱讀這部作品的技術方法——這才是閱讀能力的集中體現,可以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測學生閱讀能力的未來發展。
(三)名著閱讀評測要關注文本特質
關注文本特質是文本解讀的基礎。名著閱讀的評測要緊緊把握作品的體式特征,評測的重心要落在這一類作品閱讀的關鍵點上。比如對《駱駝祥子》和《朝花夕拾》的評測,前者是小說,從人物角度考查學生對形象的把握無可非議,但對于后者,如果要求學生談談“范愛農”這個人物的特點就值得商榷了。《朝花夕拾》是散文,“范愛農”是魯迅眼中的“范愛農”,魯迅在范愛農身上傾注了復雜的情感,這才是學生需要把握的關鍵點;范愛農并非一個客觀的形象,引導學生分析人物特點以理解、感受文本,實在緣木求魚了。
王榮生教授曾經多次強調要把小說當小說讀,把詩歌當詩歌讀,把散文當散文讀。這個觀點當然也適用于評測。比如下面這道閱讀《水滸》第二十六至三十回的評測試題:
閱讀下面文字,結合原著評價這兩位英雄好漢的做法。
武松到了孟州牢城以后,差撥見武松沒有來行賄他,將他大罵一頓,武松回敬過去:“要錢沒有,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里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不成!”差撥大怒而去。林沖到了滄州城以后,差撥見林沖沒有來行賄他,將他大罵一頓,林沖等他罵完,取出五兩銀子,賠著笑臉說:“這是給差撥大哥的薄禮。”又拿出十兩銀子,請差撥交給管營。差撥馬上就變笑臉走了。
該題巧妙地扣住兩位好漢對于索賄的不同態度設題,學生需要從人物的背景、性格、遭遇等方面對兩人進行有理據地分析,既把握了章回小說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特質,又扣住了人物的個性特點,是很值得稱道的。
但我們的有些名著閱讀評測試題卻沒有引導學生去作這樣的閱讀。我們有些命題者固守自己錯誤的閱讀經驗,打著“尊重學生,多元解讀”的旗幟,采取一種奇特的閱讀取向,有意對作品作出一些曲解,還謂之以“個性化閱讀”,這是很值得警惕的。當然,更多的命題者是因為自己專業閱讀知識陳舊或不足,總是拿著一套模式去觀照每部作品,比如考查小說閱讀情況就陷在人物、環境、情節的三要素里無法自拔,評測試題缺乏作品個性,有時還不能指向作品的核心價值,這對于名著閱讀教學的導向也是沒有益處的。
從評測的角度來說,命題者是一個文本研究者,要借助理性反思把握文本的核心價值,其中包括語言、人物、主題、審美、文化等等;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對閱讀知識除舊納新,吸收相關研究成果,實現專業發展。
(四)名著閱讀評測要倡導“主題閱讀”
曹勇軍老師在美國教育考察時看到,教室中央的小桌上放著十幾本書,有胡賽尼的《追風箏的人》、戈爾丁的《蠅王》等,都是教師上“戰爭文學”這個主題時指定學生讀的,教師要求“不一定本本精讀,但至少要選讀其中若干章節”。曹老師對此很驚嘆,因為在中國學校的語文課上很少能看到這樣的情景。[3]
這就是典型的“主題閱讀”教學,學生就某一個研究“主題”,閱讀兩種以上的作品。我們的評測要想辦法引導名著閱讀教學往這個方向發展。其實這些年來,有些地方的語文評測專家已經在思考和探索了。比如2015年臺州市中考卷的現代文閱讀分別節選了《老人與海》和《海明威創作漫談》中的片段進行組合閱讀,測試題的作答不只限于節選片段的內容,學生必須聯系整部作品才能完成闡述。節選文字就相當于“引子”,測試的重心在《老人與海》這部學生必讀作品。這樣的實踐當然只能算是主題閱讀的初級產品,但已經有了“主題閱讀”的影子。只要我們再往前走一走,就能帶動“主題閱讀”的發展,進而改變閱讀教學和評測的生態。
主題閱讀的評測,相當于給了學生研讀思考的立足點和聚焦點,學生以此在不同文本之間就某一話題作出分析、綜合、評價,甚至創造出屬于自己的個性新觀點。就評測來說,這樣的試題對學生的思考研究有所依,有所指,思維層級和閱讀要求都比較高,有助于考查學生發展的核心素養。2016年浙江省質量監測卷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有評論家認為,《水滸》中的很多人物,都有《三國演義》的影子,如關羽和關勝,諸葛亮和吳用,張飛和林沖,等等。請選擇一組人物,結合原著的具體內容,說說兩個人物的共同點。
試題要求學生從兩部作品中比較研究相關人物,思考主題提示了研究的重點和方向。評測的形式表明了閱讀的過程就是研究的過程,對于名著閱讀教學具有積極的導向作用。就初中名著閱讀教學來說,主題閱讀更宜以小說作品來開展,借助小說開展讀寫活動,通過閱讀研究提高思維能力,讓學生發現自我,質疑社會,認識人生。
目前,這方面的評測罕有表現,對冒出的些許“新芽”,我們要好好呵護。《如何閱讀一本書》中將主題閱讀定義為“最復雜也最系統化的閱讀”,認為“卻可能是所有閱讀活動中最有收獲的”。[5]21因此,通過主題閱讀的評測,倡導這樣一種名著閱讀的行為,是一種莫大的功德。
三、名著閱讀評測的類型及要求
基于閱讀的本質及其表現的特征,結合當前我國學業評價的基本狀況,名著閱讀評測可以從表現性評價和應試型評價兩個維度去考慮,在實際操作中,可以有機地將兩者結合評測。
(一)表現性評價
對于名著閱讀的評測,表現性評價有其獨特的優勢。表現性評價在接近于現實的情境中實施,讓學生面對真實的問題,綜合運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來解決問題。它強調學生的“真實性學習”,“任務(或活動)”成為課堂教學的中心。關于名著閱讀,其表現性評價一般有三種形態。一是研究一個書面性任務并建構答案。比如閱讀《三國演義》第七十五至八十五回,要求學生模仿諸葛亮吊孝時的悼詞,從關羽、曹操、張飛、劉備等人中選擇一個,結合具體情節評價人物,完成一份悼詞;閱讀《水滸》第二十三至三十二回,教師從武松入獄后金圣嘆連用25個“妙”和12個“奇”入手,要求學生試著在本次閱讀相關段落上,以“奇”“妙”為核心詞寫一段“才子點評”。二是創作一項實踐活動性作品。比如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給《紅巖》寫一段推薦語制成腰封或書簽,向學弟學妹們推薦這本書;閱讀《三國演義》第三十四至五十回,以小組為單位,為電視劇《舌戰群儒》配音,或選擇一個故事改編成劇本,在班級表演。三是進行一項論證。比如關于《水滸》,我們可以設計一場辯論:有學者認為,水滸英雄的悲劇結局是宋江經各種思想雜糅之后所承載的矛盾之必然結果,對此你是否認同?
分析上面的三種形態可知,表現性評價特別注重學生閱讀的過程及其產生的結果。對于名著閱讀來說,其評測持續于教學、學習的過程之中,而不止在教學、學習終結之后實施。名著閱讀的評價活動本身就是教與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課堂中的表現性評價不僅服務于教師的教學,更重要的是促進和改善學生名著閱讀的表現。學生必須要有充裕的時間開展自主探究性閱讀,從而獲得自主建構意義的機會,并公開陳述他們的研究結果。
表現性評價在許多國家、地區以及國際評價項目中被廣泛應用,其開發和運用也日趨完善成熟。2016年9月20日公布的中考改革指導意見,將綜合素質評價作為升學的一個重要考量。綜合素質評價顯然無法完全借助于傳統的紙筆測試,可能最終將依賴于表現性評價。名著閱讀、綜合素質評價、表現性評價三者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語文教師可以以此為契機認真開展研究。
(二)應試型評價
名著閱讀進入應試型評價領域已是常態,而且很有現實的必要。這種評價既要考慮紙筆測試的需要,也一定要注意遵循閱讀的基本規律。在實踐操作中,名著閱讀的應試型評價要特別注意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盡可能摒棄有關表層信息的識記類試題;當然,作品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是學生應該了解的,但命制試題要避免直接考查。第二,即使是應試型試題,也要盡可能往表現性任務這邊靠,強調模擬情境中現實問題的解決;當然一定要注意紙筆考試的便捷性操作,要盡量簡約,不要過于復雜。第三,試題不能指向簡單的結論,而是仍然要體現學生閱讀的過程,考查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若導向學生只讀故事梗概、名著提要就能解決問題,那將是名著閱讀的浩劫。第四,名著閱讀內容不能僅僅局限在文學文本內,而應從培養學生發展核心素養的角度呈現多樣化內容;當然,考慮到初中教學的現實,仍應以文學著作為主,適度向其他領域延伸,如《浙江省初中畢業升學考試說明》就推薦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等歷史、哲學名著。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3.
[2][美]斯蒂芬·克拉生.閱讀的力量[M].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2:36.
[3]曹勇軍.我們欠學生真正的閱讀課[N].中國教育報,2016-10-24(9).
[4]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5:60.
[5][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爾斯·范多倫.如何閱讀一本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6]王榮生.閱讀教學教什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13.

(責任編輯:方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