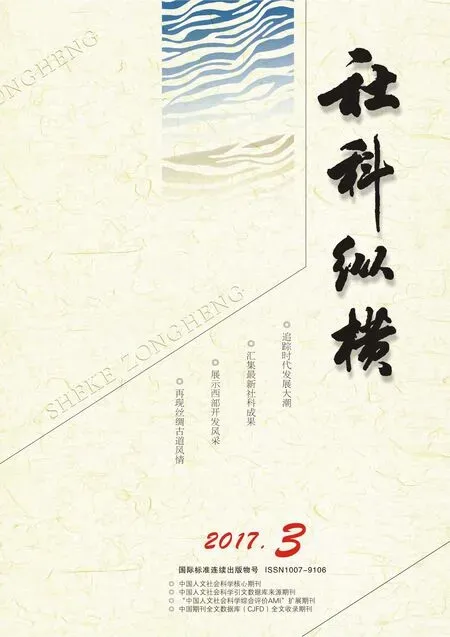日本加入三國同盟與昭和天皇的態度
龔娜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政治與行政·
日本加入三國同盟與昭和天皇的態度
龔娜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天津 300191)
二戰爆發后,德國的勝利刺激了日本的野心。對南進一直采取觀望態度的昭和天皇也開始轉向支持締結三國同盟,幻想搭上德國的便車,實現對亞太全境的控制。在昭和天皇的主導下,日本邁出了南進步伐,并締結了三國同盟,最終走向了日美戰爭。
昭和天皇 三國同盟 日美戰爭
對于三國同盟,日本顧忌德、日、意軍事同盟將惡化日本同英、法、美的關系,所以希望三國軍事同盟是三國“反共協定”的發展,并不針對英、法、美。日本堅持三國同盟以“蘇聯”為對象,目的在于使德國在歐洲牽制蘇聯,配合日本在遠東對蘇聯進行軍事挑釁,以便集中力量侵華,利用“反蘇”、“北進”,虛張聲勢,麻痹英、法、美,伺機南下東南亞和太平洋。然而諾門坎戰役①的失利粉碎了日本的反蘇冒險行動。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更使日本“以蘇聯為對象”的三國計劃受挫,談判一度擱置。
一、天皇從觀望到支持締結三國同盟
20世紀40年代初,在歐洲局勢尚未明朗以前,昭和天皇致力于指導軍部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他對于日德意結盟并不感興趣。昭和天皇主張堅持與英、美協調的方針,對南進與否采取了一種觀望態度。
1940年,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為深陷中國戰場、難以抉擇究竟是北進②還是南進③的日本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日本統治層決意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在日本國內,依靠德國的這股侵略勢力,趁機奪取英國、法國和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的想法急速增長。南進論逐步占據了主導地位,日德意軍事同盟論再次抬頭。昭和天皇也被德國暫時取得的輝煌業績深深吸引,一心想建功立業的他也開始轉向支持締結與德國的同盟關系。
同年7月17日,日本組成了第二次近衛內閣。26日,近衛內閣決定了以“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根本的《基本國策綱要》。其中明確寫道:“現今世界處于歷史重大轉變之機,出現了以幾個國家集團的產生與發展為基調的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皇國也面臨著有史以來的重大考驗。值此之秋,真正實現基于皇國建國大精神之國策,則要以把握上述世界史發展的必然動向,對各種庶政迅速加以根本革新,排除萬難,完成國防國家體制為眼前緊急要務。”[1](P436)這是日本政府從建設“東亞新秩序”向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轉變的明確表示。
7月27日,日本戰時大本營和政府聯席會議決定了《隨著世界形勢演變處理時局綱要》。進一步提出:“帝國對應世界形勢的變化,要在改善內外形勢,迅速促進解決支那事變的同時,要捕捉良機,解決南方問題。……要以對德、對意大利、對蘇聯的施策為重點,但要迅速強化與德國和意大利的政治團結,謀求迅速調整對蘇關系。”[1](P437)此時,日本政府已把本國侵略東亞的進程,與德意法西斯在歐洲的戰爭進程,相互密切地結合起來了。
9月9日至10日,經昭和天皇批準,外相松岡洋右和德國特使斯塔瑪舉行會談并達成協議。協議內容為:日本對德、意在歐洲,德、意對日本在東亞,各自“建設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予以承認和尊重;日、德、意三國中的任一國家受到“尚未參加正在進行著的歐洲戰爭或日中糾紛的一國的攻擊時,三國應以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所有方法進行互相援助”。[1](P459)協議表明日本放棄了“反蘇”三國同盟,將目標指向了美國。9月14日,在大本營和政府的聯席會議上,政府和統帥部一致通過了《日德軍事協定草案》。9月16日,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上確定的《關于強化日德意軸心文件》中寫道:“強化日、德、意三國合作之形勢,最近頗為強勁,可以認為此時已經到了三國之間需要急速會談的時機。對此,應按照以下基本綱要,與德、意進行最后談判。”其中,在有關軍事同盟的交涉綱要中明確提出:“日本及德、意兩國不能容忍美國逸出西半球及美國領地之外,為了維護兩者政治及經濟利益,要相互合作。在其中的一方與美國處于戰爭狀態時,另一方要以各種方法予以援助。日本及德、意兩國在中南美洲的施策上要緊密合作。”[1](P448-450)
從明治初年以來,雖然日本偶爾或與英美反目,但總體上一直保持合作的關系,這次與英、美公然發展為敵對關系,是日本重大的國策轉變,所以昭和天皇很擔心與美國開戰。9月16日,天皇向近衛首相表達他的擔憂:“現在締結日德軍事同盟實出無奈。可是萬一同美國交手,海軍怎么樣?聽說海軍大學的海上作戰經常敗于美國,不要緊吧?我很擔心這個時局,萬一日本成為戰敗國時,總理是否愿意與我共患難?”近衛首相表示,日俄戰爭時,伊藤博文奉答明治天皇:“萬一戰敗,將辭退爵位等,為國捐軀。”而今自己“也決心竭力奉公盡職”。[2](P480-481)昭和天皇盡管意識到了危機,但在得到近衛的保證后,還是決定放手一搏,支持締結三國同盟。
二、天皇經過深思熟慮批準加入三國同盟
1940年9月19日,昭和天皇召開了第三次御前會議,會議反復討論和分析了締約后對中國戰場的影響、與美英關系、戰略物資特別是石油的獲得等問題。雖然與會者已經認識到,與德國同盟將會破壞同英、美的貿易關系,影響戰略物資的進口,甚至導致持久戰爭,但到最后仍作出了與德意結盟的決定。昭和天皇親臨會議,表示同意。之后不久,他就批準了協定。
據內大臣木戶幸一回憶,21日,他向昭和天皇建議說:“若是同德、意締結軍事同盟,那就明顯地要同英、美對抗。因此,有必要及早調整同中國的關系。”[3](P114)天皇表示他曾詢問過近衛和松岡:“締結三國同盟最后會不會發生日美戰爭?”對此,兩人表示:“此同盟的目的在防止日美戰爭,如果不簽訂這個同盟,爆發太平洋戰爭的危險性更大。”[4](P108)
盡管昭和天皇完全意識到對德同盟很有可能引發日本同英、美的沖突,但是他更愿意相信搶先行動可以帶來更多的利益,實力的提高不僅能夠增加防范戰爭的能力,更可以降低戰爭發生的風險。
昭和天皇經過深思熟慮后批準了三國同盟。但他對近衛和松岡強調的三國同盟不是為了對美戰爭而是防止戰爭的說法還持有懷疑,因此深感不安。9月24日,昭和天皇對木戶說:“締結日英同盟(1901年)時,在宮內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可是這次不能像締結日英同盟時那樣只是高興,萬一形式變化有可能面臨重大危急局面,所以我想親自到賢所(祭祀天皇祖先諸神)禮拜告察,同時祈求神靈保佑,你看怎么樣?”木戶回答說:“同宮內大臣商量,盡力按照天皇的心意去安排。”[5](P825)
雖然昭和天皇對締結日德軍事同盟感到不安,但他更幻想通過日德合作,不用戰爭就使美國屈服。在批準三國同盟上,天皇絕不是被迫同意,他完全擁有否決權。
9月27日,日本政府與德、意在柏林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約定:“日本國承認且尊重德國及意大利有關在歐洲建設新秩序的指導地位;德國及意大利承認且尊重日本國有關在大東亞建設新秩序的指導地位;日本國、德國及意大利約定,基于上述方針,努力相互合作,特別是三締約國中的任何一國,受到現今沒有參加歐洲戰事或日支紛爭的一國攻擊時,三國約定,應以政治、經濟及軍事的方法相互援助……日本國、德國及意大利確認,上述各條款不影響三締約國各自對蘇聯現存的政治狀態。”[1](P459)
同日,昭和天皇發布詔書,向國內外宣布承認三國軍事同盟。詔書宣稱:“弘揚八纮一宇之大意,乃皇族皇宗之大訓,朕夙夜眷眷,不敢忘懷。而今,世局動亂,不見休止。人類蒙難,不可限量。朕誠愿早日勘定,恢復和平。故命政府商議與意圖相同德意兩國合作之事宜。于此,親見三國條約成立,朕甚感欣慰……”[2](P487)
三國同盟的確立使美國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因此,美國總統羅斯福于1940年9月28日在白宮召開了由國務卿和三軍首腦參加的高級決策會議,確定了具體的對日策略:“……對日本要維持我們的一切權利和原則,繼續我們的經濟壓力,援助中國,但不把日本推到使它的軍方要求戰爭的地步;讓日本了解我們在太平洋是強大的,而且正在總體上加強力量;不能讓日本得到這樣的印象,即在需要時我們不會使用我們的力量。但在同時,克制與它的爭吵,讓討論和協議之門敞開。”[6](P146)美國決定加緊援助中國抗戰的同時,加強對日經濟制裁,進行對日談判,實施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
德意日簽署三國同盟協定后,日本的南進政策最終定下了基調。三國同盟結成后,日美雙方的戰略地位與戰略環境嚴重惡化。日本軍令部長永野修身指出:“有了三國同盟,就不可能調整對美邦交,從而石油來源斷絕。……與其這樣,莫如馬上動手,除此別無他途”。[7](P895)
與此同時,昭和天皇擔心一旦日美開戰,由皇族繼續擔任陸海軍統帥機關的首腦,將來會承擔開戰的責任,并有可能由皇族波及到皇室、進而危及到自己。為了逃脫戰爭責任,天皇主動提議免去閑院宮載仁的陸軍參謀總長和伏見宮的海軍軍令部總長職務。10月3日,閑院宮辭職,推薦自己的心腹杉山元繼任參謀總長。1941年4月,伏見宮辭職,由永野修身繼任。
在三國同盟問題上,從最初商議到簽訂盟約長達三年之久。昭和天皇有足夠的時間去了解和思考其重大意義,其中包括三國同盟肯定會使日本喪失外交彈性,永遠地失去與英美合作的機會,甚至爆發日美戰爭。雖然昭和天皇反對與美英為敵,對前景甚為擔憂,但他最終同意了三國同盟協定的簽署,這是機會主義的冒險行為。昭和天皇態度的轉變是日本歷史上一個重要拐點,帶來了日美戰爭的可能性。
注釋:
①1939年5—9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偽滿洲國邊境諾門坎地區發生的蘇軍和日軍的局部戰爭。蘇軍以優勢兵力將日軍切斷包圍,予以重創,蘇德簽訂不可侵犯條約,國際局勢發生變化。9月15日在莫斯科簽訂停戰協定。
②北進戰略即大陸政策,主張在發動對中國的侵略后首先進攻蘇聯,以“解決北方問題”。
③南進戰略即海洋戰略,強調在發動對中國的侵略后首先南下進攻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以實現對整個亞太地區的控制。
[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下卷[M].東京:原書房,1965.
[2][日]中尾裕次編集.昭和天皇發言記錄集成上卷[M].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3.
[3][日]井上清.天皇的戰爭責任[M].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
[4][日]栗原健著,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備忘錄[M].臺北:國史館,2000.
[5][日]木戶日記研究會.木戶幸一日記下卷[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
[6][日]由井正臣.太平洋戰爭——日本近代史要說(第二十章)[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
[7][日]日本國際政治協會編.走向太平洋戰爭的道路(第七卷)[M].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
K313.46
A
1007-9106(2017)03-0083-03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編日本史”(項目編號:13&ZD106);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日本的戰爭責任與歷史觀研究”(項目編號:TJSL16-002)的階段性成果。
龔娜(1981—),女,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本皇室、日本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