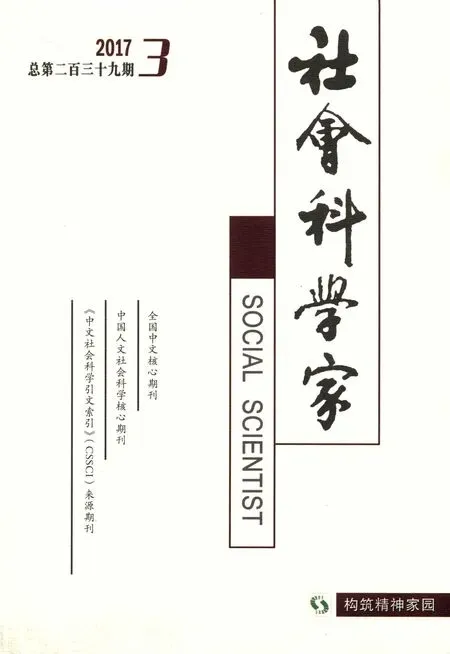晚清民國(guó)親屬相奸罪存廢所體現(xiàn)的親屬法倫理變遷
張亞飛
(1.華東政法大學(xué),上海 201620;2.山西師范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山西 臨汾 041000)
晚清民國(guó)親屬相奸罪存廢所體現(xiàn)的親屬法倫理變遷
張亞飛1,2
(1.華東政法大學(xué),上海 201620;2.山西師范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山西 臨汾 041000)
晚清民國(guó)時(shí)期中國(guó)刑法中親屬相奸罪之變遷,乃親屬法倫理在家族主義與個(gè)人主義博弈的結(jié)果。清末修律時(shí)期“禮法之爭(zhēng)”中對(duì)“親屬相奸”罪的存廢進(jìn)行了激烈的爭(zhēng)論,最終被保留下來(lái)。北洋政府時(shí)期、南京國(guó)民時(shí)期繼續(xù)延續(xù)此罪,但經(jīng)常出現(xiàn)反復(fù),在進(jìn)與退之間尋找平衡。司法實(shí)踐中,各個(gè)時(shí)期最高審判機(jī)關(guān)不斷彌補(bǔ)與立法之間的斷裂,試圖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倫理綱常與近代西方法學(xué)思潮的融合。縱觀當(dāng)前中國(guó)刑法典缺失親屬倫理?xiàng)l款,如尊老愛(ài)幼、親屬間互助等,更有甚者當(dāng)前社會(huì)中“親屬相奸”現(xiàn)象沒(méi)有明文規(guī)定,故“親屬相奸”條款應(yīng)入刑法典,且加重處罰,實(shí)現(xiàn)親屬倫理與刑法的完美結(jié)合。
親屬相奸;禮法之爭(zhēng);親屬法倫理
奸非罪在古代是一項(xiàng)很古老的罪名,因?yàn)樾允羌榉亲锼址傅膶?duì)象,性可以使人發(fā)生強(qiáng)烈的刺激,從而一定程度上會(huì)引發(fā)社會(huì)秩序混亂。故在遠(yuǎn)古時(shí)代,人們就開(kāi)始對(duì)性行為有禁忌,即對(duì)時(shí)間和地方進(jìn)行限制。婚姻制度是人類社會(huì)產(chǎn)生較早的社會(huì)制度,而婚姻制度下的性關(guān)系是合法的性關(guān)系,而違反婚姻制度之外的性關(guān)系,就是非法的性關(guān)系,“公然猥褻亦即妨害風(fēng)化實(shí)是歷史上最古老的罪名。”[1]故從遠(yuǎn)古社會(huì)開(kāi)始,對(duì)性關(guān)系有嚴(yán)格的限制,延至后世,隨著婚姻制度的產(chǎn)生,繼而有了家庭制度的建立,親屬制度在此背景下自然誕生了,于是親屬之間的性禁忌變得忌諱,歷代法律對(duì)非法的性關(guān)系處分極重。
和奸罪的相關(guān)罪名包括“親屬相奸”、“無(wú)夫奸”、“通奸”、“誘奸”、“私奸”等罪名從唐律開(kāi)始,一直到清代律典均保持了一致的條文,僅是刑罰輕重發(fā)生了變化。到1902年清末修律開(kāi)始,隨著對(duì)《大清新刑律草案》關(guān)于廢除親屬相奸、“無(wú)夫奸”、“通奸”的規(guī)定,禮教派與法理派展開(kāi)了激烈的爭(zhēng)論,最終當(dāng)《欽定大清刑律》頒布時(shí),沒(méi)有采納禮教派的觀點(diǎn)。自此,和奸的相關(guān)罪名變?yōu)榧榉亲铮?jīng)《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刑法第一次修正案》、《刑法第二次修正案》、《刑法草案》、《改定刑法第二次草案》、1928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1933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修正案》、1935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一直在發(fā)生變化,故有必要對(duì)“親屬相奸”的罪刑變遷進(jìn)行分析。
另一方面,清末修律時(shí)期,由于禮教派與法理派針對(duì)《大清新刑律草案》中“親屬相奸”的存廢進(jìn)行了激烈的爭(zhēng)論,被李貴連教授稱為:“從文化上說(shuō),是外來(lái)法文化與傳統(tǒng)法文化之爭(zhēng)(或者說(shuō),是工商文化與農(nóng)業(yè)文化之爭(zhēng));從制度上說(shuō),是舊法與新法之爭(zhēng);從思想上說(shuō),是家族倫理與個(gè)人自由權(quán)利之爭(zhēng)(或者說(shuō),是國(guó)家主義與家族主義之爭(zhēng))。”[2]親屬相奸”進(jìn)入了《欽定大清刑律》,禮教派勝利。
“親屬相奸”在《欽定大清刑律》延續(xù)下來(lái),說(shuō)明法律在轉(zhuǎn)型之初,封建倫理對(duì)立法影響巨大,雖清廷想實(shí)現(xiàn)中華法系的轉(zhuǎn)型有很大的障礙。故清廷在立法過(guò)程中持有一種矛盾的心態(tài),一方面想維護(hù)瀕臨倒臺(tái)的統(tǒng)治,惟有通過(guò)變法;來(lái)適應(yīng)社會(huì)的發(fā)展;另一方面,社會(huì)不接受國(guó)家自上而下的變法,尤其是清廷統(tǒng)治者中禮教派極力維護(hù)封建倫理,保護(hù)其集團(tuán)利益,生怕受到侵蝕,禮教派極力反對(duì)廢除封建倫理的法條。
一、清末修律時(shí)期:立法與司法實(shí)踐的斷裂
(一)立法:固有法的延續(xù)
光緒三十四年,《大清新刑律》草案已經(jīng)擬定完畢,上交各省督撫簽注。但由于新刑律需在新憲法施行之才能頒布,正式立憲又在多年之后,且新刑律頒布尚需時(shí)日。舊律又不適用于社會(huì),故對(duì)《大清律例》修改迫在眉睫。沈家本上書(shū)“舊律之刪訂,萬(wàn)難再緩”,并決定四項(xiàng)辦法,一是刪除總目,由于現(xiàn)行官職已經(jīng)改革,故刪除按照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類的刑律總目。二是修訂刑名,廢除封建五刑之笞、杖、徒、流、死,改用死刑、安置、工作、罰金四項(xiàng)。三是采用新章刑法。“惟自同治九年以來(lái)垂四十年,通行章程,不下百有余條”[3],經(jīng)過(guò)甄別,決定其存廢。四是采用簡(jiǎn)易例文。針對(duì)二千余條例文,將已經(jīng)不符合當(dāng)時(shí)情形的,或另訂新章,例文成為虛設(shè),“或系從前專例無(wú)關(guān)引用者”,或例文互有矛盾者,均加以刪并,改為簡(jiǎn)易例文。即經(jīng)過(guò)修改、修并、續(xù)纂、刪除四項(xiàng)具體措施。經(jīng)過(guò)一年多,于宣統(tǒng)元年二月二十九日,《現(xiàn)行刑律》初稿修改完成,沈家本、俞廉三上書(shū),共計(jì)編訂律文414條,例文1066條。清廷交憲政編查館審核,又勘正261條,于宣統(tǒng)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奏。又因?yàn)樵谛y(tǒng)元年三月十六日通過(guò)《法院編制法》,“奏準(zhǔn)變通秋審舊制,所有審判之覆核京控,秋審之會(huì)錄解勘與從前辦法不同,均照新章更正,計(jì)修改五十七條,刪除十條,加具案語(yǔ),另繕清單進(jìn)呈外。”[4]最終《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于宣統(tǒng)二年四月初七日頒布。
“親屬相奸”條是明朝順治三年增修的,雍正三年修改,乾隆五年又重新修訂,而到《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增加了部分規(guī)定,即增加了養(yǎng)子?jì)D、義妹、義女、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等。《大清律例》規(guī)定義子?jì)D女比照奸緦麻以上親之妻律,杖一百,徒三年。奸乞養(yǎng)子?jì)D,比照奸前夫之女律,杖一百,徒三年。奸義女,比照妻前夫之女律,杖一百,徒三年。奸義妹,比照奸同母異父姊妹律,杖一百,徒三年。“親屬相奸”條到《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改為奸同宗無(wú)服之親及無(wú)服親之妻者,處十等罰,“親屬相奸”亦分為三類:奸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妾;奸從祖伯叔母,姑從夫姊妹母之姊妹及兄弟妻兄弟子妻者;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huà)D兄弟之女,增加了奸義子?jì)D、義女、義妹、同母異父姊妹的定罪量刑。
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分則第23章“關(guān)于奸非與重婚之罪”,均規(guī)定和奸罪、重婚罪,因?yàn)楹图橹袨槭嵌Y教與輿論足以可以遏制,而不用刑法來(lái)制裁,故《大清刑律草案》廢棄舊律中奸非之條,僅規(guī)定單純奸非罪。奸非之罪自元代以后逐漸加重,均處重刑。《大清刑律草案》中僅有第278條和奸罪,而第272條猥褻之行為、第273條、第274條、第275條奸淫之罪。
在《大清刑律草案》頒布伊始,引起眾多非議,在這些爭(zhēng)論中,主要出現(xiàn)了禮教與法理兩派,由此開(kāi)始了清末的“禮法之爭(zhēng)”。這一場(chǎng)爭(zhēng)論是傳統(tǒng)法文化與西方法文化之爭(zhēng),家族主義與個(gè)人主義之爭(zhēng),固有法與移植法之爭(zhēng)。禮教派維護(hù)家族本位立法原則,維持封建制度為目的。而法理派是維護(hù)“人權(quán)”,堅(jiān)持法理本位,進(jìn)而以個(gè)人主義立法原則,建立君主立憲制,實(shí)現(xiàn)新政。在整個(gè)爭(zhēng)論過(guò)程中,禮法兩派都絕對(duì)地主張法理或禮教,法理派雖主張以西方法律思想和價(jià)值為價(jià)值判斷,制定新律,但亦不拋棄大多數(shù)禮教條文。
高漢成先生再現(xiàn)了中央各部院、各省督撫的簽注意見(jiàn),其幾乎一致肯定了此次刑律草案的成績(jī),僅是對(duì)部分不合中國(guó)風(fēng)俗和禮教的條款提出異議[5],尤其是第23章奸非罪的異議,針對(duì)和奸罪不及無(wú)夫之?huà)D(處女)、孀婦,有壞禮防,突破男女之別,有損中國(guó)本土風(fēng)俗。針對(duì)親屬相奸亦不屬于和奸罪,亦屬于破壞家庭倫理,離間親屬之間的親密關(guān)系,破壞封建禮教,與中國(guó)風(fēng)俗相背馳,使得忠孝觀念敗壞,禮義廉恥觀念喪失殆盡,中國(guó)幾千年來(lái)的封建禮教在刑律草案中幾乎沒(méi)有體現(xiàn)。為此,各省督撫、中央各部院一致認(rèn)為須恢復(fù)親屬相奸罪,更須將寡婦、處女均列為和奸罪的處罰對(duì)象。
清廷將中央部院、各省督撫的簽注意見(jiàn)反饋給修訂法律館和法部,沈家本與修訂法律館迫于禮教派反對(duì)意見(jiàn),而采取“于有關(guān)倫紀(jì)各條,恪遵諭旨,加重一等”,然后送交法部。法部在《大清刑律草案》后加《附則五條》,明確規(guī)定親屬相奸條有關(guān)倫理禮教,不能隨意廢棄。經(jīng)過(guò)這次修改,定名為《修正刑律草案》,于宣統(tǒng)元年(1909年)由廷杰、沈家本聯(lián)名上奏。
《修正刑律草案》上奏后,不但沒(méi)有平息爭(zhēng)論,反而激起更大的風(fēng)浪。禮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已經(jīng)過(guò)世,勞乃宣成為禮教派的領(lǐng)頭人,與法理派展開(kāi)人激烈的爭(zhēng)論。勞乃宣針對(duì)《修正刑律草案》提出了反對(duì)意見(jiàn),認(rèn)為其違反倫理,著成《修正刑律草案說(shuō)貼》向憲政編查館,對(duì)“親屬相奸”條做出“古稱內(nèi)亂禽獸刑。在中國(guó)習(xí)俗,為大犯禮教之事。故舊律定罪極重。在德國(guó)法律,亦有加重之條。若我刑律不特立專條,非所以維倫紀(jì)而防篤亂也。[6]”故“今擬其文曰‘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huà)D、兄弟之女者,處死刑、無(wú)期徒刑。其余親屬相奸者,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6]
沈家本反駁勞氏學(xué)說(shuō),“新草案和奸有夫之?huà)D,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較原案又加一等者,原包親屬相奸在內(nèi),但未明言耳。此等行同禽獸,固大乖禮教,然究為個(gè)人之過(guò)惡,未害及社會(huì),舊律重至立決,未免過(guò)嚴(yán)。究之,此等事何處無(wú)之,而從無(wú)人舉發(fā),法太重也。[6]”故不應(yīng)給予重罰,即使重罰,“間有因他事?tīng)窟B而發(fā)覺(jué)者。辦案者亦多曲聲敘,由立決改為監(jiān)侯。使非見(jiàn)為過(guò)重,何若是之不憚煩哉?[6]”大多數(shù)因?yàn)樾谭ㄌ兀瑹o(wú)法實(shí)行,此罪則形同虛設(shè);如果法太輕,則人可以承受,受到懲戒則可起到警示效果。故此類案件處罰二等有期徒刑,與舊律刑罰相當(dāng),沒(méi)有寬縱之嫌。“應(yīng)于《判決錄》詳定等差,毋庸另立專條。”
后勞乃宣收回“親屬相奸”的修正意見(jiàn),只對(duì)“無(wú)夫奸”和子孫違反教令進(jìn)行爭(zhēng)論。后《大清新刑律》附加《暫行章程》五條于1910年12月由資政院通過(guò),于1911年1月25日頒布。“親屬相奸”入律,外表看似禮教派獲得了勝利,并不代表法理派真正地被打敗。實(shí)質(zhì)上是中西兩種法律文化之間的較量,西方個(gè)人主義法文化和中國(guó)傳統(tǒng)家族法文化的較量。但禮教派與法理派的出發(fā)點(diǎn)都是為了清廷搖擺不定的統(tǒng)治,希望通過(guò)國(guó)家上層建筑——修律和憲政,來(lái)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自上而下的變革。但腐朽的清王朝已經(jīng)不能阻止歷史的腳步,上層建筑的改變不足以維持社會(huì)有效運(yùn)行。
(二)司法實(shí)踐:固有法的延續(xù)
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設(shè)立修訂法律館開(kāi)始,到宣統(tǒng)二年(1910年5月15日)《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頒布,在這期間,司法實(shí)踐中所適用的是《大清律例》的律條,而從1910年5月15日,經(jīng)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1日開(kāi)始,到1912年2月12日結(jié)束,在這不到兩年司法實(shí)踐中,適用《大清現(xiàn)行刑律》來(lái)審判案件。因此,在清廷最后的十余年中,司法實(shí)踐中呈現(xiàn)出兩個(gè)階段,一是古代律學(xué)《大清律例》,二是作為1911年11月25日《欽定大清刑律頒布》中間過(guò)渡形態(tài)《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的適用。故清末修律時(shí)期刑事司法實(shí)踐中亦有兩個(gè)階段:第一是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到宣統(tǒng)二年(1910年),這一時(shí)期還是適用《大清律例》,第二是1910年5月15日《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頒布到清廷滅亡,雖然1911年1月15日頒布了《欽定大清刑律》,但是沒(méi)有用于司法實(shí)踐中。這兩個(gè)階段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律學(xué)向近代刑法的轉(zhuǎn)變,所體現(xiàn)出來(lái)對(duì)固有法的延續(xù)和繼受法的初步移植,使得兩種法律文化在司法實(shí)踐中呈現(xiàn)出激烈的碰撞,在縣級(jí)、省級(jí)、國(guó)家三級(jí)審判機(jī)關(guān)中均呈現(xiàn)此種特點(diǎn)。
清末修律時(shí)期的“禮法之爭(zhēng)”表明立法上一直移植西方刑法,借以改造中國(guó)傳統(tǒng)律學(xué),而禮教派又不甘心全部西化,竭力要保持“無(wú)夫奸”這一體現(xiàn)禮教的條文,法理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妥協(xié),使得《欽定大清刑律》盡快頒布。而司法實(shí)踐中,清廷適用的是《大清律例》和《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在光緒朝適用的還是《大清律例》的封建五刑,而在宣統(tǒng)朝適用了《大清律例》和《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的刑罰,沒(méi)有適用《欽定大清刑律》,故清末修律時(shí)期親屬相奸的立法和司法實(shí)踐是斷裂,立法一直趨向于西方刑法典內(nèi)容,以日本刑法典為模板指定新刑法典,而司法實(shí)踐中依然適用的是舊律中的罪刑。這種情況到北洋政府時(shí)期逐步緩解,立法和司法實(shí)踐逐步開(kāi)始融合。
二、北洋政府時(shí)期:固有法與繼受法的沖突和融合
(一)立法層面:刑罰的確定化
北洋政府時(shí)期,袁世凱將《欽定大清刑律》簡(jiǎn)單修訂后,命名《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關(guān)于親屬相奸條文直接沿用《欽定大清新刑律》。到1915年《修訂刑法草案》第306條:“本宗緦麻以上之親屬相奸者,處四等有期徒刑。有夫之?huà)D女,處三等有期徒刑。其知情相奸者,亦同。[7](P717)”本條較《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第290條第一款沒(méi)有變化,只是對(duì)有夫之?huà)D女相奸者,加重到三等有期徒刑(三年至六年),刑法加重一等。《修訂刑法草案》刪除了“無(wú)夫奸”條。
再到1918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16章妨害風(fēng)化罪第239條親屬相奸條:“四親等之內(nèi)宗親相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7]本案對(duì)親屬范圍和親屬種類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親屬范圍與舊律服制圖的范圍相似,改為寺院計(jì)算法下的四親等內(nèi)的宗親,如發(fā)生相奸者,處1-7年有期徒刑,較《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和《修正修法草案》的刑罰都發(fā)生了變化,不再區(qū)分幾等有期徒刑,而是直接規(guī)定刑罰年限。到1919年《改定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第16章妨害風(fēng)化罪第250條“四親等內(nèi)之宗親相和奸者,處一年以下,七年以下有期徒刑。”[7]本條延續(xù)了1918年《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的原文。綜觀北洋政府時(shí)期的刑事立法,“親屬相奸”延續(xù)了《欽定大清刑律》的規(guī)定,一直向西方刑法典靠攏,但同時(shí)亦不廢除舊律中事關(guān)倫紀(jì)的條文。北洋政府時(shí)期刑事立法一直在舊律和新律之間權(quán)衡。
(二)司法實(shí)踐:對(duì)親屬相奸罪的補(bǔ)充和擴(kuò)張
北洋政府時(shí)期的司法實(shí)踐中運(yùn)用的是《中國(guó)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大理院判決例、解釋例來(lái)指導(dǎo)審判工作。大理院受到兩方面的挑戰(zhàn),一方面是紛繁復(fù)雜、無(wú)所適從的法律,另一方面是新觀念沖擊影響下的各種新案件。進(jìn)退維谷的大理院一方面要堅(jiān)持舊律中的有關(guān)法律,又要?jiǎng)?chuàng)制性地制造判決例和解釋例,供下級(jí)司法機(jī)關(guān)運(yùn)用,作為判決的依據(jù),彌補(bǔ)立法的不足和疏漏。這一舉措不但彌補(bǔ)了西方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則,而且彌補(bǔ)了舊律與司法實(shí)踐的差距。
在大理院解釋例有妾與家長(zhǎng)通奸,和奸之人在服制圖內(nèi)屬于無(wú)服親屬,仍應(yīng)以普通和奸罪論(七年上字第759號(hào))。[8]這是因?yàn)樾搪裳a(bǔ)充條例第12條對(duì)于刑律第82條第2項(xiàng)及第3項(xiàng)第1款,雖有稱妻者,于妾準(zhǔn)用之。如妾與家長(zhǎng)兄弟無(wú)服,如果二者相奸,應(yīng)以普通和奸在罪論,而不予以親屬相奸論。又有與再?gòu)男值苤尴嗉椋荒軜?gòu)成親屬相奸(九年上字第503號(hào))[8]。上告人與某人系同曾祖,則上告人系某人再?gòu)男值埽渑c某人之妻某氏,但并無(wú)服制,不能算作親屬相奸。上述兩個(gè)解釋例說(shuō)明實(shí)際案件中,對(duì)暫行新刑律第289條的親屬范圍進(jìn)行進(jìn)一步限制,妾與家長(zhǎng)兄弟相奸,與再?gòu)男值芷尴嗉椋紝儆跓o(wú)服親屬,故不是屬于親屬相奸。
又有一案宜城縣知事朱介曾詳稱一國(guó)之法律,必與本國(guó)歷史相關(guān)。中國(guó)古代刑律凡關(guān)于服制罪名,無(wú)不特別加重,即暫行新刑律無(wú)夫奸不為刑事犯。而第290條親屬相奸罪的處罰較第289條有夫奸罪重。“誠(chéng)以為倫常為人生大本,懸法宜嚴(yán)。查前清現(xiàn)行律娶親屬妻妾者,以服制之輕重定罪刑之輕重。今民法未頒,婚姻制防,前清現(xiàn)行刑律當(dāng)然繼續(xù)有效。惟有效者僅制防其婚姻,設(shè)于成婚后告訴,在審判衙門(mén)當(dāng)然不認(rèn)為其婚姻成立,男女間是否仍獨(dú)立為奸非罪。照新刑律第290條辦理,大有疑義。”[9]有兩種處理意見(jiàn),甲說(shuō)認(rèn)為婚姻制防,男女間媾和,即屬奸罪。乙說(shuō)認(rèn)為雖然犯婚姻聯(lián)防,男女間究因?yàn)榛橐鰲l件而媾和,只能撤銷其婚姻,不能認(rèn)為其犯奸罪。最終大理院認(rèn)為中國(guó)最重人倫,社會(huì)上兄亡以嫂為妻,弟婦為妻者,此類惡習(xí)者,應(yīng)禁止親屬相奸罪,以甲說(shuō)為準(zhǔn)。此解釋例是對(duì)《暫行新刑律》和《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補(bǔ)充條例》親屬相奸罪的補(bǔ)充和完善。傳統(tǒng)舊律中娶親屬妻妾的行為,根據(jù)服制遠(yuǎn)近來(lái)確定罪刑輕重。基于兩個(gè)原因認(rèn)定這個(gè)行為在民國(guó)初年為親屬相奸行為,一是北洋政府初期沒(méi)有頒布民律,而運(yùn)用前清刑律,故娶親屬妻妾的行為是親屬相奸罪。二是民國(guó)建立伊始,西方法律的個(gè)人主義思潮與傳統(tǒng)律學(xué)中的家族主義處以一種對(duì)立和融合的狀態(tài),大理院一邊想廢除“無(wú)夫奸”的罪名,但又不得不面對(duì)中娶親屬妻妾的這一廣為存在的現(xiàn)實(shí),故對(duì)傳統(tǒng)律學(xué)做出了妥協(xié),承認(rèn)親屬相奸罪。
北洋政府時(shí)期是一個(gè)舊勢(shì)力沒(méi)有完全被消滅,而新生力量也沒(méi)有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時(shí)期,這種新舊之間的沖突在親屬相奸罪中表現(xiàn)尤為明顯。大理院對(duì)普通和奸罪給予了多方面的擴(kuò)展和補(bǔ)充,使得親屬相奸罪符合近代西方刑法理論,變通《中華民國(guó)暫行新刑律》一些不適應(yīng)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法律條文。大理院解釋例和判決例對(duì)親屬相奸罪也作了進(jìn)一步的變通和擴(kuò)張,同時(shí)也為維護(hù)了傳統(tǒng)律學(xué)。
三、南京國(guó)民政府時(shí)期: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
1928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第15章妨害風(fēng)化罪第245條:“四親等內(nèi)之宗親相和奸者,處一年以下、七年以上有期徒刑。”[8]本條沿用了1919年《修正第二次刑法修正案》第250條的規(guī)定,到1933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修正案初稿》第16章妨害風(fēng)化罪第218條:“直系或三親等內(nèi)旁系血親相和奸,處五等有期徒刑。”[8]這一修正案中親屬相奸的范圍發(fā)生了變化,現(xiàn)在為直系或三親等內(nèi)旁系血親,而且刑罰變?yōu)槲宓扔衅谕叫獭SH屬種類從“宗親”變?yōu)椤把H”,范圍從“四親等內(nèi)”變?yōu)椤爸毕祷蛉H等內(nèi)的旁系”。到1934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修正案》第16章妨害風(fēng)化罪第225條:“直系或三親等內(nèi)旁系血親相和奸者,處五等有期徒刑。”[8]這一案延續(xù)了1933年的規(guī)定。到1935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第16章妨害風(fēng)化罪第230條:“直系或三親等內(nèi)旁系血親相和奸者,處五等以下有期徒刑。”[8]1935年《中華民國(guó)刑法》一直延續(xù)了1933年《中華民國(guó)修正案初稿》的規(guī)定。
在南京國(guó)民政府時(shí)期,最高法院在司法實(shí)踐中一直致力于趨近近代西方刑法理論,試圖擺脫民初大理院在審理案件處于傳統(tǒng)律學(xué)與近代刑法之間的進(jìn)退維谷境地,拋棄古代律學(xué)的罪刑,并逐漸縮小與當(dāng)時(shí)刑事立法的差距,逐步融合。
1932年11月11日刑事非字第150號(hào)所記載的案例中[10]“刑法第245條之規(guī)定,以相和奸之人屬于四親等內(nèi)之宗親為限,隨母改嫁之子,對(duì)于繼父不得認(rèn)為刑法上直系尊親屬,則對(duì)于繼父一方之親族,即不生宗親關(guān)系,加有和奸行為,自不構(gòu)成前項(xiàng)法條之罪。”周全梅自幼隨母嫁入周維昌為子,以其義父之胞弟周于香作鄰居。當(dāng)周全梅后與其義叔母周江氏通奸,周于香發(fā)現(xiàn),告到法庭,是否認(rèn)定親屬相奸。法律原規(guī)定繼母都不是刑法上之尊親屬,而繼父之胞弟更不是其直系親屬,故周全梅與繼父之胞弟妻子周江氏通奸,不是四親等內(nèi)之宗親,不屬于親屬相奸罪。
綜上所述,南京國(guó)民政府時(shí)期,最高法院一直致力于彌合刑事立法與司法實(shí)踐中的斷裂,親屬相奸罪亦一直延續(xù)下來(lái),親屬范圍由“四親等內(nèi)之宗親”,后來(lái)改為“直系或三親等內(nèi)旁系血親”,相奸罪的親屬范圍沒(méi)有太大的變化。司法實(shí)踐中,和奸罪依然是較親屬相奸罪處刑較輕,親屬之間的和奸罪處罰重于凡人相奸罪。但是隨著受到近代西方刑法的影響,即罪刑法定原則,亦受到近代平權(quán)立法思想影響,親屬相奸罪的罪刑也逐漸減輕。
四、結(jié)論——親屬法倫理徘徊在家族主義和個(gè)人主義之間
縱觀近代中國(guó)刑法中親屬相奸罪之變遷,均有親屬相奸罪重于凡奸罪,足見(jiàn)其重視倫理綱常,維系家族和睦,嚴(yán)厲打擊威脅家族秩序的行為,進(jìn)而維持社會(huì)穩(wěn)定。親屬相奸律亦是秦律有相關(guān)規(guī)定,進(jìn)而到漢律詳細(xì)記載,至唐律分為三條“奸緦麻以上親及妻”、“奸從祖祖母姑”、“奸父祖妾”。宋亦沒(méi)有太多變化,明清律對(duì)親屬相奸進(jìn)行更為詳細(xì)補(bǔ)充和完善,從而使親屬相奸罪成為特殊凡奸罪中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
通過(guò)比較分析,發(fā)現(xiàn)清律親屬相奸罪較唐代處罰較為嚴(yán)重,都旨在維持家庭秩序,保持親屬關(guān)系的和睦,利用嚴(yán)峻刑罰營(yíng)造一種男尊女卑的社會(huì)秩序,使人們生活在家族主義之中,一切均由家長(zhǎng)和族長(zhǎng)做決定,極力壓制個(gè)人主義,使其處于統(tǒng)治者所營(yíng)造的社會(huì)秩序之中。但通過(guò)對(duì)清末修律時(shí)期的司法實(shí)踐可以發(fā)現(xiàn),因普通和奸罪和凡奸罪的案件發(fā)生命案如此之多,對(duì)清代統(tǒng)治者所宣揚(yáng)試圖創(chuàng)立尊卑有別的社會(huì)秩序產(chǎn)生懷疑,即親屬關(guān)系并不是十分和睦,而是一種對(duì)立,或者說(shuō)一種仇視。
到“禮法之爭(zhēng)”,針對(duì)“親屬相奸”發(fā)生激烈的爭(zhēng)吵,法理派認(rèn)為奸罪是依靠教育可以解決問(wèn)題,而不是刑法所管轄的范圍。禮教派認(rèn)為如果不讓奸罪入律,則難以維持尊卑有別、長(zhǎng)幼有序的禮法,則有損于家庭秩序,造成淫風(fēng)大勝,國(guó)家失德。二者在立法上的爭(zhēng)執(zhí)主要體現(xiàn)在家族主義與個(gè)人主義。但最終和奸罪之“無(wú)夫奸”和“親屬相奸”律最終入律,可見(jiàn)到1911年《欽定大清刑律》一方面繼承了中國(guó)家族主義的立法,嚴(yán)守中國(guó)“男女之別”傳統(tǒng)社會(huì)秩序,嚴(yán)禁禽獸之“無(wú)夫奸”。另一方面,繼受了近代西方刑法的立法指導(dǎo)思想,完全借鑒日本刑法典的體例,同時(shí)亦參考了德意等國(guó)刑法典。清末立法者在固有法與繼受法之間平衡,尋求最合理、最完備的立法技術(shù),立法者最終一直試圖擺脫傳統(tǒng)律學(xué)的束縛,企圖用近代西方刑法理念來(lái)改造中國(guó)傳統(tǒng)律學(xué),短時(shí)間內(nèi)融入世界發(fā)展的大格局之中。這也是造成清末修律“禮法之爭(zhēng)”一開(kāi)始的大爭(zhēng)論,而親屬相奸罪延續(xù)數(shù)十年,尤其是在民國(guó)時(shí)期一直處于反復(fù)之中。
中國(guó)傳統(tǒng)律學(xué)有關(guān)禮教與倫理的規(guī)定,一直流淌在中國(guó)人的血液之中,一直在國(guó)人心中留下了印象,人們依然注重家庭,家庭和睦在國(guó)人心理依然占有重要位置。但近五十年中國(guó)刑法近代化過(guò)程中,一直通過(guò)立法的技術(shù)層面和司法實(shí)踐的操作層面,來(lái)改造中國(guó)傳統(tǒng)律學(xué)。而近代西方刑法一直注重個(gè)人主義的立法指導(dǎo)思想,這就與中國(guó)重視家族主義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不符合。由此看出,單方面拋棄中國(guó)傳統(tǒng)律學(xué)或完全繼受西方刑法,均不可取,即不能單方面堅(jiān)持家族主義或個(gè)人主義,只有學(xué)貫中西,充分融合,方能實(shí)現(xiàn)二者有效地結(jié)合。考察當(dāng)前中國(guó)刑法中缺乏“親屬相奸”的規(guī)定,常常造成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中大量親情倫理犯罪的尷尬境地,較常人相奸并沒(méi)有區(qū)別,使得審判處于窘境,且在當(dāng)前刑法典中無(wú)“親屬相奸”條款,故“親屬相奸”條款應(yīng)入刑法典,加重處罰,實(shí)現(xiàn)親屬倫理與刑法的完美結(jié)合。因此,有效借鑒近代中國(guó)刑法比變遷的歷程,來(lái)為當(dāng)前中國(guó)刑事立法提供參考,擺脫僅通過(guò)改造立法和司法實(shí)踐的指導(dǎo),來(lái)實(shí)現(xiàn)改造社會(huì)的目的。
[1]蔡樞衡.中國(guó)刑法史[M].北京: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5.129.
[2]李貴連.沈家本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97.853.
[3]故宮博物院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9.
[4]故宮博物院:欽定大清現(xiàn)行刑律[Z].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5]高漢成.簽注視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N].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7.67-168.
[6]李貴連.沈家本傳[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12312;315;315.
[7]黃源盛.晚清民國(guó)刑法史料輯注[Z].臺(tái)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849.
[8]郭衛(wèi).大理院判決例全書(shū)[Z].臺(tái)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506;506;979;979;1131;1131.
[9]郭衛(wèi).大理院解釋例全文[Z].臺(tái)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264.
[10]郭衛(wèi),周定枚.最高法院刑事判例匯刊(第11期)[Z].上海:上海法學(xué)書(shū)局,1934.38-40.
D929;K249
A
1002-3240(2017)03-0101-05
2017-01-18
張亞飛,華東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后流動(dòng)站研究人員;山西師范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副教授,法學(xué)博士。
[責(zé)任編校:周玉林]
- 社會(huì)科學(xué)家的其它文章
- 國(guó)際化背景下大學(xué)英語(yǔ)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與模型構(gòu)建
- “全面二孩”政策對(duì)高校女教師職業(yè)生涯發(fā)展的影響
- 旅游公共服務(wù)供給評(píng)價(jià)研究
——以京津冀地區(qū)游客為例 - 關(guān)于休閑旅游產(chǎn)品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的若干思考
- 績(jī)效考核取向及其影響效果的實(shí)證研究
- 中美食品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溝通的維度對(duì)比
——企業(yè)網(wǎng)站數(shù)據(jù)的內(nèi)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