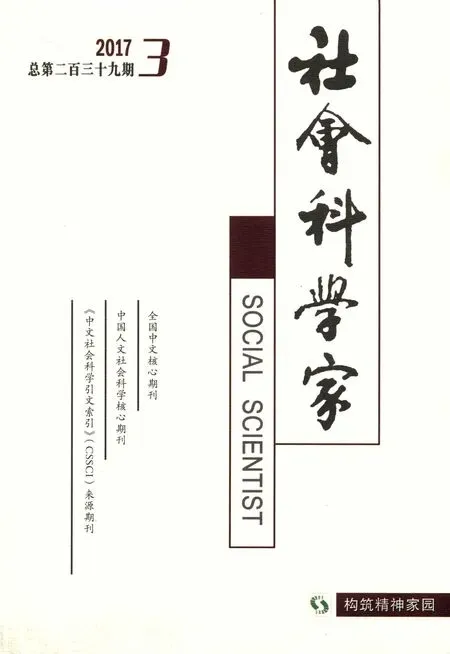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網絡社會治理的并行路徑
楊唯希
(山東大學 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網絡社會治理的并行路徑
楊唯希
(山東大學 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互聯(lián)網的高速發(fā)展推動新興社會形態(tài)的產生,人類進入網絡社會發(fā)展階段。當前,我國網絡社會治理面臨多重障礙,傳統(tǒng)社會治理模式不能適應網絡社會的治理需求,民主、開放、多元共治的治理機制亟待構建。法律規(guī)制和社會文化塑造是網絡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二者相互交融、互為促進。法律規(guī)制需要順應社會文化發(fā)展趨勢,網絡文化發(fā)展強調法律意識強化,促使制度的外部約束內化為社會個體的內心認知并主動接受,構建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良性互動的機制。
網絡社會治理;法律規(guī)制;文化
網絡最初被視為技術乃至傳播媒介而存在,在不斷的社會滲透過程中改變社會存在狀態(tài)和運行機制,成為社會轉型的推動力,由此展現(xiàn)了全新的社會圖景。網絡社會對傳統(tǒng)社會形成全方位的沖擊,傳統(tǒng)社會中基于財富、職業(yè)、教育、知識、文化等要素形成的社會階層分布、權力格局逐漸消解。在信息技術變革為先導的新型網絡社會,信息傳播、交流突破傳統(tǒng)地域邊界暢通無阻,呈現(xiàn)出流動性的顯著特征。網絡社會的復雜性、多元性對網絡社會治理提出了挑戰(zhàn),迫切需要建立開放、互動的治理模式,其中,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是相輔相成、互為作用的基本途徑。
一、網絡社會治理:基于風險社會理論的視角
關于網絡社會內涵存在三種不同觀點,大體包括:(1)虛擬社會說,即網絡社會是完全由硬件、軟件和信息網絡形成的純虛擬世界;(2)現(xiàn)實社會的延續(xù)說,否定網絡社會的獨立存在,將網絡社會視為現(xiàn)實社會的折射和反映;(3)混合形態(tài)說,認為網絡社會是虛擬網絡和現(xiàn)實社會的共生態(tài),是較為折衷的觀點。[1]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論著中所描繪的網絡社會即是虛擬社會和現(xiàn)實社會交融的新型社會形態(tài)。卡斯特認為,網絡社會是一種新社會形體,與工業(yè)社會在農業(yè)社會中的崛起具有同樣重要意義。[2]筆者亦同意“混合形態(tài)說”,同時對于網絡社會治理也采納廣義概念,即網絡社會治理是在網絡社會形態(tài)下,借鑒現(xiàn)代社會治理的價值理念、模式手段、體系建構,建立開放透明、多元互動的治理體系,由政府、企事業(yè)單位、社會組織以及個人等多方主體參與治理,綜合運用法律制度、社會規(guī)范、行業(yè)準則進行規(guī)制,積極推動社會文化發(fā)展,實現(xiàn)促進網絡社會文明進步的治理目標。
物質文明高度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科技使人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高質量生活,但也使社會暴露在巨大風險當中。風險社會理論創(chuàng)始人貝克教授指出:“風險是現(xiàn)代化的風險,是工業(yè)化的一種大規(guī)模產品,而且系統(tǒng)地隨著它的全球化而加劇。風險首先是指完全逃脫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氣、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隨的短期和長期的對植物、動物和人的影響。”[3]環(huán)境污染、全球氣候等問題成為人類生存的巨大威脅。互聯(lián)網跨越地理界限將全世界連接成為了地球村,信息傳播的便捷是過去所無法企及,但同時帶來虛假信息泛濫、隱私暴露、網絡暴力等困擾,大大加劇了社會風險。網絡打破了傳統(tǒng)媒體壟斷傳播渠道的信息傳播模式,從傳統(tǒng)社會話語權的高度壟斷到傳播平臺的不斷開放,激發(fā)了普通民眾參與網絡表達的熱情,尤其是發(fā)表政治見解的熱情。當民意沒有得到重視,民眾的反對、抵觸情緒匯集并放大,形成公共輿論,可能釀成群體性事件,危及社會穩(wěn)定和長治久安。
網絡時代各種風險加劇、交織使傳統(tǒng)社會調整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傳統(tǒng)的社會管理模式被不同理念、導向的社會治理所替代。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是新形勢下社會調整模式變革的客觀需要,政府從高高在上的命令發(fā)布者轉變?yōu)樯鐣卫淼膮f(xié)同參與者。傳統(tǒng)社會管理是單一、機械、縱向的管理模式,網絡社會治理則需要開放、互動模式,社會治理強調依法治理、系統(tǒng)治理,是一種雙向、互動、協(xié)同的治理模式。
二、從法律與文化的關系看法律規(guī)制與文化塑造的可融合性
法律規(guī)定社會行為規(guī)則,維護社會秩序,社會的進化與法的進化如影相隨。法律規(guī)制是網絡社會治理的有效途徑,離開法律規(guī)制,社會將陷入混亂無序狀態(tài)。但如果制度規(guī)范無法得到普遍認同并嚴格遵守,則是形同虛設。法律制度在網絡社會面臨的治理困境,顯示單一治理模式失靈。網絡社會意識的流動性,凸顯思想、意識在虛擬環(huán)境下無孔不入的能量,網絡社會治理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通過文化建設、傳播樹立全民信仰,通過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的互為支持和交融,實現(xiàn)網絡社會治理目標。
(一)法律與文化的關聯(lián)
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是指在一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基礎上精神財富的總和。[4]黃柟森先生認為,對文化作狹義理解具有普遍的趨勢。法律和文化都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法律與文化相互交融、互為作用。法律文化是文化的一種具體形態(tài),反映法律生活中群體化的思想觀念、理想人格、情感傾向、行為趨向。[5]從義務本位法律文化到權利本位法律文化,是奴隸制文化、封建文化到現(xiàn)代資本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遷移、更替在法的領域的反映,體現(xiàn)社會發(fā)展和文明進步的普遍趨勢。人格獨立、契約自由、關注人權、法治民主等現(xiàn)代法律制度中蘊含的精神,構成了現(xiàn)代文化的內核并推動文化的升華和發(fā)展。
法律與文化屬于上層建筑不同范疇:法律屬于政治上層建筑,是制度范疇;文化屬于思想上層建筑,包括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非社會意識形態(tài)。二者存在顯著差異:二者存在的形態(tài)不同,法律主要以成文法或判例法的形態(tài)存在,通常具有物質載體,因而較為直觀,文化主要存在于精神領域,主要指精神現(xiàn)象和精神產品,具有隱蔽性;再次,一國的法律體系往往是統(tǒng)一的,國家實行統(tǒng)一的法律制度,一國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地域性、多樣性使文化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的面貌;最后,發(fā)生作用的方式不同。法律是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文化則是以價值觀的滲透為主要形態(tài),在“潤物細無聲”中使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發(fā)生漸變,一般是無形、非強制的。法律與文化相互交融,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是網絡社會治理需要綜合運用的手段。同時,法律與文化存在狀態(tài)、作用方式等差異,顯示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途徑的相互補充和不可替代。
(二)法律與文化的交互作用
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孕育的法律制度體現(xiàn)不同的文化內核。以身份等級為基礎、貴賤尊卑作為身份標簽的專制社會,滋養(yǎng)權力服從、個人權威凌駕法律的人治文化,與之匹配的是義務本位、法刑合一的律法型法律。社會的發(fā)展歷經特權到平等,專制到民主的進化路徑,平等、獨立、自由的現(xiàn)代文化意識,將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深深植根于現(xiàn)代法律體系,是民主政體的文化源泉。社會文化對于法律的認同決定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民主傳統(tǒng)的社會更加尊重、崇尚法律,法律具有權威性。民主社會比其他社會更需要權威,因為在民主社會,每個人都有自由表達和投票的權利,如何凝聚共識、避免分裂,就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6]以人治、等級觀念為核心的社會文化導致法律虛無主義,規(guī)則價值被輕視并被踐踏,法律淪為工具而喪失了應有的正義的標尺。網絡社會下文化具有更加廣泛的影響力和深刻的社會根源,法律對于網絡社會的規(guī)范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通過主流文化的傳播使法律價值得到普遍認同和尊重,并有效提升法律實施效果。
文化的歷史早于法律的歷史,法律制度深刻體現(xiàn)文化的要素,同時以強大的作用力影響文化的塑造。法律作為強制性社會規(guī)范長期作用于社會群體,形成了關于法律的觀念意識、理想人格、行為和情感傾向,構成法律文化。法律將法治、人權、民主以制度形式確定下來,并通過制度使現(xiàn)代文化意識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法律發(fā)展推動社會文明進步,梅因在《古代法》中關于法律發(fā)展、社會進步規(guī)律做出了經典的闡述,“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7]從身份法到契約法的變遷,實際是專制文化、人治文化被民主文化、法治文化逐漸替代的社會進程。
三、當前網絡社會治理模式下法律規(guī)制與文化塑造的疏離
(一)網絡社會法律規(guī)制現(xiàn)狀
我國現(xiàn)有網絡立法主要涵蓋以下領域:網絡安全法、網絡權利法、電信法、電子商務法、信息網絡傳播法。我國網絡立法相對比較分散,缺乏系統(tǒng)性立法,網絡社會治理規(guī)定散見于各種形式的法律當中。
目前的網絡立法不能適應網絡社會治理的需求。一是從立法效力來看,網絡立法層級較低。規(guī)制互聯(lián)網的專門法律較少,《電子簽名法》(2005)、《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lián)網安全的決定》(2000)、《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2012)是具有較高層級的法律,也多是原則性規(guī)定,其他絕大多數(shù)是部門規(guī)章和地方性法規(guī)。二從立法內容看,權利文化、契約精神在立法中沒有被充分吸納,個人權利保護不足,法律對于權利文化、契約精神的塑造功能實現(xiàn)仍有較大欠缺。例如,2012年12月頒布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雖然規(guī)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和企事業(yè)單位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的義務和責任。但該法多是原則性、禁止性規(guī)定,涉及網絡服務提供者不作為或侵權法律責任的規(guī)定則較為籠統(tǒng)概括,個人信息被侵犯尋求法律救濟缺乏法律依據(jù)。契約精神是現(xiàn)代社會的基石,互聯(lián)網產業(yè)發(fā)展初期的混亂、缺乏監(jiān)督約束機制埋下了隱患,網絡欺詐、不正當競爭、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屢屢被詬病,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嚴重滯后,法律對于契約精神保障不足。三是從監(jiān)管體制的角度來看,網絡監(jiān)管體系混亂,監(jiān)管職權沖突。公安部、工業(yè)和信息化部、國家版權局根據(jù)法律授權具有相應的網絡管理權限。這種多頭管理的體制,易使規(guī)范性文件之間的內容產生沖突,各監(jiān)管部門職權交叉重疊,導致執(zhí)法過程中的爭執(zhí)或推諉。多頭管理體制與民主、開放、協(xié)調、互動等網絡社會治理理念相背,是傳統(tǒng)社會管理模式的后遺癥。四是從立法時效性來看,存在立法滯后問題,缺乏前瞻性和進取性。現(xiàn)有的網絡立法容量有限,可操作性不強。我國電信立法進程緩慢,電信法早已提上立法日程,但卻始終未能面世。2000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不能適應這個新興產業(yè)發(fā)展的制度需求,綜合性、統(tǒng)一的具有較高法律層級的電信法的制定迫在眉睫。此外,信息網絡傳播領域立法存在較大空白,立法缺失導致信息傳播監(jiān)管乏力,造就傳播內容粗制濫造、暴力泛濫的網絡環(huán)境。
(二)網絡文化發(fā)展過程中法律的隱退
我國網絡文化尚處在發(fā)展階段,表現(xiàn)出凝聚力不足、價值觀斷裂、不穩(wěn)定、多元化等特點。法律對于文化塑造的重要作用被忽視,在網絡文化形成和發(fā)展進程中法律時而缺席。
在社會急速轉型過程中,文化建設、信仰問題遭到漠視,傳統(tǒng)價值觀斷裂,社會文化激蕩演變。網絡社會文化自發(fā)成長,缺乏主流價值觀的引導,娛樂至上的思想充斥著網絡社會,人格修養(yǎng)和道德自審被放棄。“三俗”文化流行不僅顯示社會文化價值取向的偏離,更折射出個體迷茫、信仰缺失的心理狀態(tài)。在網絡事件中,人們往往機械地選擇價值觀陣營,通過網絡宣泄個人情緒,而鮮有去追問社會現(xiàn)象的本質原因以及公民責任。2006年的“彭宇撞人案”、2007年的“華南虎”事件、2015年成都毆打女司機案都顯示了網絡輿論的非理性和法律在網絡環(huán)境下的尷尬。在這些網絡事件中,道德與法律產生激烈的碰撞,在網絡激辯中產生的理性呼吁“讓道德的歸道德,讓法律的歸法律”,恰恰揭示了網絡環(huán)境下道德與法律界限不清,部分網絡群體以道德的名義實施侵權行為。規(guī)則價值被輕視,法律意識淡薄,網絡社會的法治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網絡為民眾表達民意提供了便捷的途徑,民眾參政議政的意愿強烈。網絡社會新形態(tài)對于政府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強調政府依法行使職權。如果政府面臨社會危機采取消極行政態(tài)度,容易引發(fā)網民的非理性情緒,經由網絡發(fā)酵、放大,釀成網絡輿論事件。政府部門的消極不作為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并可能異化為社會對立面而存在。民眾的不信任感強化而演變成民眾對政府的習慣認知和行為趨向。政府實施網絡治理容易招致民眾的慣性抵觸,導致政令不通。
四、網絡時代社會轉型陣痛:以個案窺見網絡社會治理現(xiàn)狀
網絡社會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帶來社會轉型的痛楚,傳統(tǒng)社會結構分解并重構,社會文化意識呈現(xiàn)碎片化、斷裂化趨勢,多元價值觀充斥并交織,部分網絡事件顯現(xiàn)網絡社會下法律規(guī)制的不足以及網絡非理性意識的沖擊力。
2006年“彭宇撞人案”——一起普通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受到社會普遍關注,彭宇將倒地老人徐壽蘭送往醫(yī)院后,雙方對于是撞倒后相扶還是做好事各執(zhí)一詞。經過媒體宣傳和網絡發(fā)酵,媒體和公眾一邊倒地認定彭宇是被冤枉。在類似的“小悅悅”事件發(fā)生后,“彭宇案”反復被提及視為道德之殤的源頭。案件審判過程中,法官利用經驗法則進行事實推定的論證引發(fā)爭議。司法審判上的經驗法則是法官根據(jù)自身學識、親身生活體驗或被公眾所普遍認知與接受的公理經驗作為法律邏輯的一種推理定式。[8]法官根據(jù)“經驗”和“情理”,分析彭宇“如果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根據(jù)社會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并讓原告的家人將原告送往醫(yī)院,然后自行離開,但被告未作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9]判決中以“人性惡”作為推理前提,進行的不適當推理被大眾作為法院錯判的標靶。二審過程中雙方達成和解,并約定不再公開事實內情。5年之后,南京市政法委書記劉志偉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表示,輿論和公眾認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實真相,并解釋2006年11月20日,彭宇確實是與徐壽蘭相撞后將其扶起。彭宇在事發(fā)幾年后承認,徐壽蘭確實與其相撞。[10]
網絡輿論在這一事件中對公眾形成錯誤的引導。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判決書中“人性惡”為前提的推理,違背了社會普遍認同的助人行善的道德理念,損害了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法律的效用被減損。媒體不辨真?zhèn)蔚拇笏列麄髌鸬酵撇ㄖ鸀懙淖饔茫诠娪^念中形成“做好事反被誣”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并引發(fā)公眾對于道德滑坡、社會冷漠的憂慮。此案例應當引起深思,當個人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發(fā)生沖突的情況下,個人隱私權是否可以加以限制,司法部門是否可以在衡量社會公益得失之后公開真相。司法部門在這個事件中沉默的消極態(tài)度放任了輿論的錯誤導向,對于網絡輿論的社會影響力缺乏提前預判和效果評價。政府在網絡社會如何引導網絡輿論、實施有效治理不可回避,正確適應法律并以法律引導公眾意識才是應對公眾信任危機、輿論困局的應有態(tài)度。
五、網絡社會治理需要建立網絡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的互動融合機制
法律規(guī)制和文化塑造是制度約束和文化浸潤的結合。當法律制度得到普遍認同和推崇,就具有了實施的土壤。制度約束內化為個體內心認同,那么法律執(zhí)行程度、實施效果將大為改善。因此,網絡社會治理工程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同時需要凝聚、整合、強化社會認同,使網絡社會治理獲得文化認同,構筑網絡社會治理的社會文化根基。
(一)文化塑造以完善的法律制度及有效實施為保障
網絡安全需要提升到戰(zhàn)略高度,我國需要制定綜合性的統(tǒng)領信息化發(fā)展的統(tǒng)一立法。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草案)》突出國家對于網絡安全的全面監(jiān)控,管制色彩濃厚,服務內容較少。政府及主管部門在網絡安全方面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仍不太明確,行政主體的職權劃分仍然較為模糊,存在權力交叉等問題。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和公民權利需要劃定邊界,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應在合法、合理、必要的范圍內實施,不能逾越公民權利的紅線。突發(fā)社會安全事件臨時限網措施涉及對于公民言論、信息傳播等權利的限制,為防范行政權力僭越、凌駕法律的風險,立法應嚴格限定此非常措施的適用前提,并規(guī)定嚴格的適用程序和濫用行政權力的法律責任。
網絡法律規(guī)制不能僅僅強調網絡秩序維護,更要注重權利保障。網絡社會治理立法應與權利意識、言論自由、民主主義的社會文化相契合,體現(xiàn)人權、平等、自由思想之精髓。個人信息安全是網絡主體權利體系的基礎權利,個人信息保護的欠缺導致個人權益極易被侵害,因此加強個人信息保護非常必要。應從私法角度明確個人信息權利內容,例如信息決定權、信息保密權、信息查詢權、信息維護權、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11]公民享有網絡言論自由,但應以不侵害他人權益為前提。立法需要明確網絡言論自由與侵權的界限,建立網絡侵權的追責制度,同時構建受侵害者權利救濟機制。
信息網絡傳播法律規(guī)制是網絡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信息網絡傳播處于無序狀態(tài),傳播內容良莠不齊,信息網絡傳播立法滯后。文化部于2011年發(fā)布修訂的《互聯(lián)網文化管理暫行規(guī)定》,該法強調公權管制,建立互聯(lián)網文化單位行政審批制度,并對互聯(lián)網文化產品內容進行規(guī)制,禁止違背法律、道德風俗和主流價值觀的內容上線傳播。文化屬于精神領域范疇,網絡文化發(fā)展體現(xiàn)出自發(fā)性、開放性、多元化等特征。立法需要適應網絡文化發(fā)展的特點,因勢利導,引導主流文化的發(fā)展壯大,并抑制消極文化。單純的行政管制模式難以實現(xiàn)對文化引領的立法初衷,因而需要建立政府引導、行業(yè)自律、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社會監(jiān)督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文化發(fā)展架構。
(二)促進文化建設為法律規(guī)制奠定良好的文化根基
網絡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和民族屬性。在互聯(lián)網的沖擊下,社會文化發(fā)展遭遇多種作用力并隨著時代的潮流而遷移,新興網絡文化因具有時代適應性而成為流行文化。社會快速發(fā)展所引起的文化斷裂需要緩沖,弘揚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是保持網絡文化的健康發(fā)展的根本。禮儀文化、道德文化是我國幾千年來傳承的優(yōu)秀文化,是民族的精神結晶,古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理想,懷揣濟世救國之家國情懷。在信仰缺失的網絡時代,傳統(tǒng)文化彌足珍貴。大力倡導傳統(tǒng)道德、禮儀,引導、規(guī)范網絡行為,營造和諧、純凈的網絡空間。
立法滯后、維權成本高、侵權難追責等問題,造成了目前網絡環(huán)境下侵權頻發(fā)的局面。法律缺位、監(jiān)管機制的失靈必然會導致管理漏洞,給違法者留下了可乘之機。違法侵權行為在網絡中普遍存在并被視為合理,法律意識淡薄在網絡環(huán)境下更加凸顯。網絡不能成為“法外之地”,法律應具有最高的權威性,通過嚴謹?shù)牧⒎ā栏竦膱?zhí)法、公正的司法實現(xiàn)。權利文化、契約精神是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源泉,在虛擬化網絡社會中更需要以此建構社會的信任機制,保障網絡社會有序運轉。針對網民法律意識淡薄的狀況,廣泛宣傳法治理念,傳播法治思想,使法治觀念在網絡社會扎根并成為社會固本之源。
[1]何哲.網絡社會的基本特性及其公共治理策略[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4,(3):56-66.
[2]劉少杰.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3.
[3](德)烏爾里希.貝克,何博聞.風險社會[M].譯林出版社,2004.18-20.
[4]車文博.心理咨詢大百科全書[M].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217-218.
[5]徐顯明.法理學教程[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91.
[6]黃曉峰.季衛(wèi)東:民主社會比其他社會更需要權威[N].東方早報,2014-03-17.
[7](英)梅因,沈景一.古代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97.
[8]孫道萃.“彭宇案”的證據(jù)法理分析——以經驗法則為視角[DB/OL].北大法律信息網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43230.shtml.
[9]李麗.法學專家詳解彭宇案為何會被“誤讀”[N].中國青年報,2012-01-18.
[10]彭宇案真相再調查[DB/OL].http:/news.163.com/12/0118/03/7O17ENEJ00014AED.html
[11]吳文嬪.立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N].人民日報,2014-04-30.
D920.0
A
1002-3240(2017)03-0106-05
2017-02-01
濟南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互聯(lián)網時代網絡社會治理研究”(JNSK15C30)
楊唯希(1979-),女,四川宜賓人,山東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專業(yè)博士在讀,研究方向:經濟法學,
[責任編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