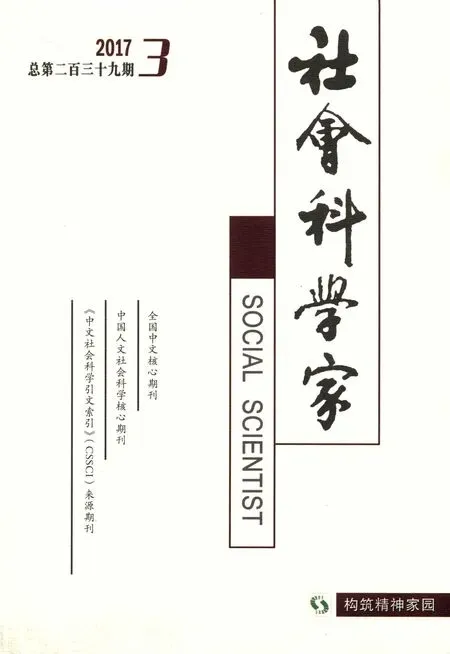現(xiàn)代化轉型中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蛻變
——對改革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種觀照
張 勇
(湖南理工學院 中文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0)
現(xiàn)代化轉型中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蛻變
——對改革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種觀照
張 勇
(湖南理工學院 中文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0)
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轉型是改革題材小說發(fā)生的內在動力,也是這一題材小說走向復雜和多元的深層原因。80年代前期的國企改革文學表征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愿望和理想,而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則對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民族文化心理有更多的反思和批判。90年代中期的“新現(xiàn)實主義”小說由于認同了現(xiàn)代化語境中的欲望敘事法則,呈現(xiàn)出較為鮮明的自然主義特征,而世紀之交的改革題材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則重新借用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敘事規(guī)則。改革是中國現(xiàn)代化繼續(xù)前進的根本,在新的價值立場上,改革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應該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表達一種整體關懷。
改革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化
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是前蘇聯(lián)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基本方法,中國作家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創(chuàng)作歷程中接受了這一方法。1953年9月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被正式確認為指導“我們文藝界創(chuàng)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和“根本方法”。然而,“由于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強調‘正確的世界觀’對于藝術創(chuàng)作的決定作用,要求把關于未來的完滿構想加于嚴峻的客觀現(xiàn)實之上,以至于把政治的、道德的說教加于生活的真實之上,因而它本身就存在著偏離現(xiàn)實主義的傾向。”[1]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用社會主義限定現(xiàn)實主義,強調理想性和傾向性,強調文藝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學化。“文藝的政治化,即指把文藝納入政治體制內,文藝從題材、主題到手法、形式都必須遵循政治的要求,為政治需要服務……政治的美學化,即指政治以理想化的形態(tài)通過文藝形象(形式)的途徑來表現(xiàn)、實施。”[2]文藝為政治服務,在那個年代具體而言就是為階級斗爭勝利的需要服務。總體而言,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過于注重先驗理性和理想,強調用先驗主題規(guī)制現(xiàn)實生活,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由此而來,而這顯然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創(chuàng)始人的初衷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認為,作家的傾向(觀點)應當從場面和情節(jié)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是專門把它表達出來,他在《致瑪·哈克奈斯》一文中指出:“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就愈好。我所指的現(xiàn)實主義甚至可以違背作者的見解而表露出來。”[3]強調真實性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而不是用先驗的觀念、理性來規(guī)定生活的真實性。
由此可見,80年代前期的國企和城市改革文學確實具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特征,主題先行,先驗理性,政治斗爭模式,改革英雄典型形象的塑造,革命浪漫主義的激情都使得這種類型的文學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相去不遠。在筆者看來,這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改革文學畢竟是在改革開放相對自由的語境中作家自主選擇創(chuàng)作方法的結果,而“文革”的文化專制主義則讓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成為唯一的選擇;另外,經(jīng)歷過“文革”階級斗爭以及新時期啟蒙思潮洗禮的作家們對人性的復雜內涵也有了更多自覺的體悟和認識,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物的簡單化和臉譜化傾向。
有意味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出現(xiàn)的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和上述的城市和國企改革文學在創(chuàng)作的精神意向和審美選擇上是有相當大的區(qū)別的。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比城市和國企改革文學能更深入地貼近生活,更具有生活的質感和實感,理念化的色彩相對較弱,對文化、歷史和日常生活也有更深刻的發(fā)現(xiàn)和感悟。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賈平凹的《商州系列》等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傾向于貼近普通中國人在改革中的現(xiàn)實生活,反映在時代變革中普通農(nóng)民心理的變化,表達他們生活的愿望,再現(xiàn)他們的努力與追求,對社會變革的艱難和農(nóng)民文化心理痼疾也多有揭示和反思,因而從整體上呈現(xiàn)為一種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風格。這些農(nóng)民不是什么改革的英雄,他們沒有豪氣干云的宏偉抱負,有的只是改善自己生活、改變自己命運的樸素愿望,在時代的變革中也表現(xiàn)出自身與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不無關系的缺陷和毛病,這些都顯得真實可信。如高曉聲的短篇小說《陳奐生上城》將改革初期農(nóng)民經(jīng)濟地位的變化帶來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變化生動真實地揭示出來,同時也揭露和批判了農(nóng)民文化心理結構中固有的茍且、自欺的劣根性。
在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研究者看來,“以追求社會生活的真實性為核心,現(xiàn)實主義形成了三個基本特點: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現(xiàn)實關懷、以科學——理性精神為基礎的典型化手法,以及建立在這兩個特點之上的現(xiàn)實批判精神。”[2]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核心是真實的社會生活,而不是先驗的理念和預設的理想,從理念和理想出發(fā)來進行想象性的寫作終究和現(xiàn)實生活是“隔”著的。作家刻畫真實的社會生活是出于對社會現(xiàn)實的整體關懷,希望這個社會更加人道、文明和美好,可見現(xiàn)實主義精神本身是包含了理想成分的;而科學和理性的精神又使得作家不得不正視社會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弊病并對其進行揭露和批判。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80年代中期出現(xiàn)的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理念先行、先驗理性的缺陷,而回歸了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即批判現(xiàn)實主義。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和前述大致屬于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城市和企業(yè)改革文學雖然都是屬于現(xiàn)實主義范疇的創(chuàng)作,但是二者又確實大不一樣。在筆者看來,城市和企業(yè)改革文學體現(xiàn)的是那一時代的人們急于呼喚改革精神和改革英雄,宣揚改革理念,表達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理想和愿望,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忽視了從現(xiàn)實生活出發(fā)來創(chuàng)作的原則。當然,80年代中期的農(nóng)村題材改革小說仍然具有80年代理想化的整體色彩,仍然顯得不夠深刻,這或許是因為80年代的改革成就是主要的,還沒有產(chǎn)生那么多現(xiàn)實的問題和困境,作家也不能完全超越他那個時代,看到更深層次的問題。
二
90年代以來,改革事業(yè)繼續(xù)深入,然而,此時的中國社會已經(jīng)失去了80年代那種對現(xiàn)代化的理想化想象,現(xiàn)代性的后果已經(jīng)充分顯現(xiàn)。因此這一時期寫實性的文學作品中似乎出現(xiàn)了兩個“中國”社會,一個是由高尚住宅、白領、老板、酒會、豪車構成的都市風景線,而另一個則是下崗、貧困、疾病、企業(yè)改制構成的中國底層社會。其實這正是現(xiàn)代化的后果之一——社會的分化和分層。很顯然,面對著90年代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嚴肅的作家總會勇于擔當,關注和描繪中國社會改革困境和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就成了很多作家的選擇。90年代中期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又被稱之為“新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潮流重返現(xiàn)實主義,《大廠》、《鄉(xiāng)關何處》、《年前年后》、《分享艱難》、《窮縣》、《大雪無鄉(xiāng)》等一批作品引起了文壇的強烈反響。作家用自己的創(chuàng)作表達了對現(xiàn)實的關注與擔當,這本是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突出特點,我們也應該高度評價這些作家重建歷史的努力。然而,如果我們用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的原則來觀照這一次重返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卻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的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特征已經(jīng)模糊不清。有批評家就認為,所謂的新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一方面對轉型期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丑惡現(xiàn)象采取某種認同態(tài)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和人文關懷;另一方面,這些作品的作者雖然熟悉現(xiàn)實生活的某些現(xiàn)象,但他們對現(xiàn)實缺少清醒的認識,尚不足以支撐起真正的歷史理性精神。[4]
也就是說,90年代中期的所謂新現(xiàn)實主義不具備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的某些基本要素和根本原則。如《分享艱難》中的地痞洪塔山強奸了西河鎮(zhèn)黨委書記孔太平的表妹,本應該將其繩之以法,但是這個洪塔山卻是個暴發(fā)戶,決定著整個鎮(zhèn)子的經(jīng)濟,為了挽救全鎮(zhèn)經(jīng)濟,孔太平甚至向舅父下跪,請求他不要追查這個流氓;而《大廠》中的呂建國為了維持工廠局面而四處求情,以苦苦的哀告、懇求、流淚來獲得人們的同情,使問題得以解決或暫時停息。這些基層單位的管理者哪里還有80年代前期改革文學中“喬廠長”那樣的改革家的英雄氣概和強者風采?面對著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和野蠻,他們也缺少那種不妥協(xié)的批判和反抗精神,他們所關注的就是利益的分配和欲望的滿足,在利益的沖突和欲望的矛盾中捉襟見肘,勉強支撐。因此,這些作品引起了前述批評家的批評也就是必然的了。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深究,這些作品或許就是中國社會現(xiàn)代性歷史進程中復雜性和多元性的表征。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性轉型和改革事業(yè)的艱難性、曲折性和復雜性遠遠超過了我們原來的設想和預計。“過多的東西尋求斷裂性的變化,歷史的時間序列改變成共時性的空間狀態(tài)。結果,被稱之為‘現(xiàn)實’的那種東西,堆積著過多的不相協(xié)調的因素。”[5]因此,作者的曖昧態(tài)度不過是現(xiàn)實曖昧性的翻版而已。如果現(xiàn)實本身都變得無比多元龐雜而曖昧不清,那我們又如何能要求作家能夠完全穿透現(xiàn)實呢?泛政治意識形態(tài)在這個時代已經(jīng)顯得可疑,不再能成為敘事的可靠基礎,而新的現(xiàn)實也還沒來得及建構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基礎。
在這種情況之下,作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欲望敘事的法則。現(xiàn)代化已經(jīng)充分顯示了自身的后果,時代的發(fā)展對每個處于經(jīng)濟困境中的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在這些作品中,考量這些基層管理者和改革者的不再是銳意改革的精神、大刀闊斧的魄力、推動歷史進步的宏大抱負,而是他們如何謀取地方和企業(yè)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利益,如何帶領百姓和員工走出經(jīng)濟困境,在艱難中負重前行,理想主義的光彩消失殆盡。能夠與時代的世俗利益追逐和欲望法則相抗衡的只是基層改革者或者管理者個人的道德和人格,而這也顯得那么卑微和可憐,只是在這種沉重而艱難的底色中偶爾閃現(xiàn)某些光彩和亮色。當經(jīng)濟和利益、物質和欲望的追逐成為時代的重心之時,我們看到的是生存本身的灰色和主體精神的暗淡。在這個意義上,90年代中期的所謂“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作品或許在主觀上試圖以整體關懷精神重建反映改革現(xiàn)實的宏大敘事,但是現(xiàn)實本身的多元混雜使得這種目標不再可能。“這些作者在藝術上秉承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但已經(jīng)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前提可以依靠,這就使他們的歷史沖動與他們的具體敘事必然產(chǎn)生抵牾。企圖建構這個時期總體性的歷史敘事,都顯得力不從心,歷史的目的論總是在‘歷史過程’中被解構。”[5]
既然在形而上層面缺乏真正的思想力量穿透混雜多元的現(xiàn)實,就只能在形而下層面認同時代的欲望敘事法則,因此,這些所謂新現(xiàn)實主義作品既沒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那種雄視古今的自信,也缺少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對當下現(xiàn)實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作品呈現(xiàn)出自然主義文學的某些特征。除了上述原因,這或許也受到了80年代后期的“新寫實主義”小說寫作態(tài)度和文學觀念的影響。“新寫實主義”小說解構了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執(zhí)著于對“原生態(tài)”生活的描繪,而所謂的“原生態(tài)”生活不過就是人們的世俗欲望和因為欲望的爭奪和受挫而帶來的丑惡和煩惱,抹平了深度,放棄批判精神。很顯然,“新寫實主義”小說的自然主義色彩頗為濃厚,而認同了時代欲望敘事法則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的中短篇小說同樣具有敘事的平面化特點,缺乏歷史理性和批判精神。如前所述,《分享艱難》中的洪塔山是野蠻的資本原始積累的發(fā)家致富者,他強奸了鎮(zhèn)黨委書記孔太平的表妹,而孔太平為了鎮(zhèn)里經(jīng)濟的發(fā)展,置法律和正義而不顧,反而放過了洪塔山;而《大雪無鄉(xiāng)》中的陳鳳珍為了鎮(zhèn)里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不得不依靠暴發(fā)戶潘老五。
面對世俗化生存現(xiàn)實,放棄對某種政治意向和理想、先驗精神和理念的承諾和表達,成為新的歷史時代里文學創(chuàng)作的趨勢。“就此而言,應當充分認識到新的寫作趨向的必然性和積極意義。然而,新的寫作趨向同時暴露出了相應的問題。這就是,在張揚個性的同時,放棄了對社會整體的關注;在肯定感性(情感和欲望)價值的時候,否定了精神價值;在追求真實的表現(xiàn)的時候,喪失了理想表達的能力。”[2]今天我們仍然不得不反思和追問,在發(fā)展經(jīng)濟、獲取利益和堅守價值、維護公正之間孰輕孰重?或者在社會改革中這兩者就必然是矛盾和沖突的?高爾基當年在談到對自然主義的認識的時候指出:“當然,這是真實,是十分齷齪的、甚至令人痛苦的真實,必須同這種真實進行斗爭,一定要無情地把它消滅掉……但是自然主義這個手法,并不是同那應該消滅的現(xiàn)實進行斗爭的手法。”[6]盡管社會改革和轉型中確實存在這種丑惡現(xiàn)象,但作品態(tài)度的曖昧和立場的失據(jù)卻傷害了其自身應該具有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批判精神。
三
世紀之交,改革題材的長篇小說大量涌現(xiàn),代表作品有《車間主任》、《人間正道》、《天下財富》、《中國制造》、《抉擇》、《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等。這批長篇小說因為產(chǎn)生時間和“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或新現(xiàn)實主義)相去不遠,并且也同樣關注改革進程和現(xiàn)代化轉型中經(jīng)濟困境的現(xiàn)實,因此也曾經(jīng)被納入90年代的“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小說范圍,但在筆者看來,世紀之交的改革題材長篇小說和“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潮流中的中短篇小說還是有很大不同的。這種區(qū)別并非僅僅表現(xiàn)在小說的篇幅上,而是長篇小說這種文體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社會全景式的整體關懷和重建宏大敘事的努力,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其基礎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重新認同。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認定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上,才能完成長篇小說的宏大敘事建構和現(xiàn)實整體關懷的目標。那么問題的關鍵是,這一次宏大敘事的建構所依據(jù)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是什么呢?“能夠把這些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提出來討論的是,它們共同具有某些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這一曾經(jīng)作為社會主義中國主流文化樣式——的修辭特征:以戲劇性沖突組織起來的問題性事件、以‘英雄’形象負載某種價值功能的典型人物、以具有地域色彩或社群特征的具體空間作為基本環(huán)境。”[7]也就是說,這些改革題材長篇小說在敘事策略和意識形態(tài)實踐上都一定程度上回歸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當然要區(qū)別的是,世紀之交的改革題材長篇小說雖然一定程度上回歸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但和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學那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書寫很不一樣,這些改革題材長篇小說更直接正視了改革進程中艱難曲折的現(xiàn)實,更加接近改革生活的實際。
沒有人可以否認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現(xiàn)代化和城市化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然而,在如此美好的現(xiàn)代化圖景中,我們往往忽略和遮蔽了另一幅社會圖景和社會現(xiàn)實,即社會的分化和貧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弱勢群體,沉默的大多數(shù),底層社會,是我們對這一現(xiàn)象的命名。面對經(jīng)濟改革和社會轉型帶來的創(chuàng)傷和陣痛,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對諸般社會現(xiàn)實表達自身的整體關懷,建構文學世界的形象體系,也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撫平創(chuàng)傷,重新喚起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在當下文化整體結構中的力量也在于此。然而,市場化、城市化改革帶來的社會階層的分化中,利益受損害群體卻主要是工人和農(nóng)民——這一在經(jīng)典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意識形態(tài)實踐中居于歷史主流地位的主體,這些人物在紅色經(jīng)典小說敘事中,絕對是居于主導地位的,但是這一次他們卻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如張宏森的《車間主任》表現(xiàn)了北方重型機械廠以車間主任段啟明為主的一個車間工人從秋入冬幾個月的生活。工人劉義山因公受傷只能在家病休而不能得到治療,李萬全因為太窮而偷賣工廠的舊機器,女工人肖嵐被到美國讀研究生的男友拋棄……企業(yè)改革和社會變革過程中階層的分化更加明確了小說人物的階級身份和意識,然而,這一次他們卻是作為利益被損害的階級出現(xiàn)。
有意味的是,在這里,伴隨著利益受到損害而明確的階層和階級意識并非要導向過去年代曾經(jīng)有過的階級仇恨和斗爭,而是要重新喚起這些工農(nóng)群體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規(guī)約下的主人翁意識和道德情感。盡管他們的利益受到了損害,盡管他們身陷貧困,但是作品試圖通過借助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將這些工人塑造成為新的改革時代的主體。因此,他們不應該再計較自己的生存困境和利益受損,而是繼續(xù)無私奉獻,兢兢業(yè)業(yè),把自己的全部獻給工廠。于是,在張平的長篇小說《抉擇》中出現(xiàn)了這樣一個可以作為典范的老工人形象——夏玉蓮,她任勞任怨,不計名利,身體虛弱,臥病在床,但堅持不要工廠的醫(yī)藥費補助,甚至以死阻擋工人到市政府門前示威。這些作品包含的道德化情感和意識形態(tài)內涵是顯而易見的。“它建立在一種重新敘述的集體認同之上,并由此抹去被管理者、利益受損害者的怨憎,并吁求他們再度心甘情愿地付出。這一新的集體認同或現(xiàn)實敘述,由此成為重新整合‘現(xiàn)實’的有效意識形態(tài)實踐。”[7]事實上,喚起集體認同,抹平現(xiàn)實矛盾,將新的現(xiàn)實在想象中給予合法化,這本身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當年對自然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文學流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首先提出了“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關注是“人的完整性”這樣一個重要的觀點。“當時的盧卡契真誠地希望,作為現(xiàn)代文學主要形式的小說,仍能像以往的史詩那樣,承擔起調和物質與精神、生活與本質的關系,實現(xiàn)原先那種意義與生活不可分割的烏托邦理想。”[8]賦予生活以意義,重建個體與社會的聯(lián)系,在時代改革和社會轉型的艱難歷程中獲得一種整體感和認同感,這或許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努力的方向。然而,僅僅依靠重新借助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似乎并不能真正地獲得一種表意和穿透現(xiàn)實的有效話語和思想力量,文學需要不斷創(chuàng)新和超越。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國社會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改革題材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應該能夠找到新的觀察社會和敘述生活的堅實的立場和依據(jù),通過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文學創(chuàng)作將已經(jīng)分化的社會重新整合在一起,在批判和整合中創(chuàng)造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學精品。
[1]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7.
[2]肖鷹.現(xiàn)實主義:從歐洲到中國[J].甘肅社會科學,2001(1):3-9.
[3]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2.
[4]陶東風,童慶炳.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缺失[J].文學評論1998(4):43-53.
[5]陳曉明.表意的焦慮——歷史祛魅與當代文學變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392;391.
[6]高爾基.高爾基文學書簡[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5.273.
[7]賀桂梅.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230;246.
[8]盛寧.現(xiàn)代主義.現(xiàn)代派.現(xiàn)代話語——對“現(xiàn)代主義”的再審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35.
I247
A
1002-3240(2017)03-0139-05
當代文學史新時期前期的改革文學適應著“文革”結束之后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啟動而獲得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歷史資源,代表了那一時期中國社會內在的歷史沖動和全體中國人的生活愿望,產(chǎn)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和效應,也因此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自己深刻的痕跡。改革文學的發(fā)軔以1979年蔣子龍發(fā)表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為標志,隨后改革文學的創(chuàng)作形成了一股洶涌的潮流,《開拓者》、《新星》、《沉重的翅膀》、《禍起蕭墻》、《家園街五號》等小說的出版掀起了改革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高潮。毫無疑問,改革文學所表征的是剛剛結束“文革”動蕩的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性歷史沖動,表達了中國人民對現(xiàn)代化理想的美好向往。這似乎再次驗證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往往是該時代歷史愿望和社會情緒的反映這一論斷。除此之外,改革文學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風格特征、改革家英雄形象的塑造也有助于改革文學的文學史地位的確立。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的改革已經(jīng)走過了三十多年歷程,當我們回首當代文學史的改革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可以發(fā)現(xiàn),改革題材小說創(chuàng)作應現(xiàn)代化運動而起,也隨著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的深入而變得復雜和多元。
一
當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學大潮成為歷史,隨著改革事業(yè)的深入以及新時期文學自身的發(fā)展,人們對改革的艱難性、曲折性、復雜性有了更深的認識和體會,改革文學也真正擺脫了當年的簡單化、模式化傾向。因此,人們對80年代前期的改革文學所表達的現(xiàn)代化想象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學觀念和模式又有了更多的反省和思考。在筆者看來,當年的改革文學尤其是城市和國企改革文學的問題主要在于在作品內容上改革的理念先行,缺乏對改革現(xiàn)實的真實生活內容更多的體驗,在形式上則有模式化的特點。因而從整體上來看,改革文學仍然是一種類同于新時期之前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其創(chuàng)新可以視為“舊瓶裝新酒”,而這新酒也不過是一種不同于革命年代的觀念化的社會生活。我們甚至可以假設一下,套用當年國企和城市改革文學的外在形式,將其內容置換為“文革”時期的階級斗爭,似乎也非常妥帖和合拍。因此,今天看來,改革文學的主要成就是表達了那一時期的歷史愿望,鼓舞了中國人投入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信心,但相對于80年代社會生活和文學自身創(chuàng)新的要求而言,改革文學從觀念到形式還顯得比較陳舊。
2016-12-11
本論文為湖南省教育廳項目:現(xiàn)代化語境中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潮流研究(12K119)階段性成果
張勇(1975-),湖南湘鄉(xiāng)人,文學博士,湖南理工學院中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
[責任編校:陽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