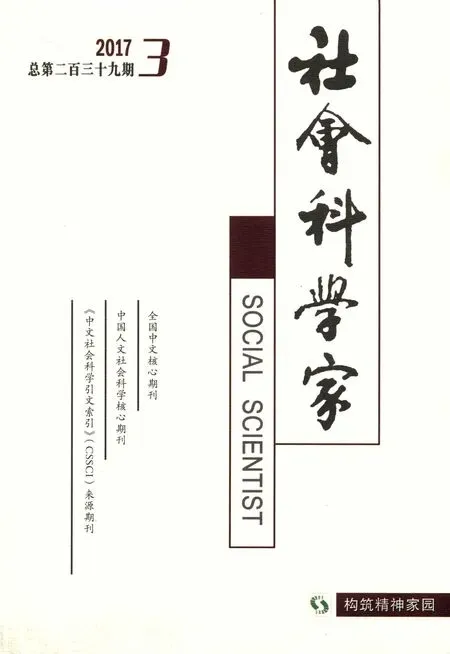論德國與法國的歷史敘述發展演進
徐璟瑋
(1.華東師范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歷史學系,上海 200241;2.上海理工大學,上海 200093)
論德國與法國的歷史敘述發展演進
徐璟瑋1,2
(1.華東師范大學 人文社科學院歷史學系,上海 200241;2.上海理工大學,上海 200093)
在整個歐洲,國別史的歷史書寫方式已經長達近2個世紀,這種書寫方式不僅帶來了各國間歷史研究的豐富及完善,也造成了歷史書寫中的競爭;尤其是在對民族國家的歷史進行書寫時,人們會不自然地將該國的人種、宗教、階層、性別作為特質進行描述。德國和法國就是之中非常典型的代表,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傳承的淵源,他們對民族意識的理解有著不少異同點,也一直是現代歷史學家熱衷于研究的對象。文章將對德國和法國的歷史敘述的最新發展進行梳理,以窺視到整個世界歷史敘述的發展動態與主流方向。
德法歷史敘述;民族和種族;宗教與性別
公元843年,《凡爾登條約》的簽訂讓歐洲歷史上著名的法蘭克王國從內部一分為三,形成了中法蘭克王國(843-855)、東法蘭克王國(843-911)和西法蘭克王國(843-987);這也是后來意大利王國、德意志第一帝國和法蘭西王國這三個國家的雛形。后兩者也漸漸形成了現代的德國與法國。而一直以來,德國與法國的史學都被深深地打上民族主義的烙印。兩個國家的發展過程和歷史演進一直是相輔相成而又獨具特色。歷史學家們的觀點是,兩國的民族主義在史學觀點上存在共同體特征,同時又質疑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儒勒·米什萊和利奧波德·馮·蘭克等著名的歷史學家都多次提及,他們的性格上受到跨國政治觀念的影響。他們還認為,種族與民族意識等方面的歷史敘述也呈現出兩國歷史觀的異同。對民族主義的史學研究并不能消除已有的或新出現的“國家”概念。德國和法國的歷史學家們,在他們的案例研究中考慮將其它概念融入本身的研究之中。
出于史學敘述的認真嚴謹態度,天主教知識分子、愛國主義歷史學家查爾斯·貝璣在他那段著名的評論中這樣寫道:“書寫一秒鐘的歷史將要花費我一個星期。書寫一分鐘的歷史將要花費我一年。書寫一小時的歷史將要花費我的一生。我需要一個永恒來書寫一天的歷史。”[1]他對于史學研究的態度讓我們敬佩,同時也是對后人很好地激勵。德法兩國的歷史敘述也是在這樣的史學大家的不懈的努力下得以傳承與發展。這些歷史敘述發展的演進也正是本文想要深入探討的主要內容。
一、德國與法國歷史中的種族與起源
現代德國的民族概念是在過去的200年中才逐漸形成了體系。不管是知識分子、政治家,還是歷史學家都在反復思考著有關“民族”的定義。一開始,民族國家的解釋是由知識分子對1789年事件的態度的積極或消極的來認定的。然而,這種模糊性很快被一種原始的概念所取代。1815年時,巴托爾德·格奧爾格·尼布爾曾斷言:“民族格局遠高于政治格局,某一個共同民族格局中的人們在政治格局中不會被分開和結合。”因此,到了19世紀20年代,浪漫主義學派的知識分子又提出,“日耳曼性”(Germanness)是自然所賦予的;這種“日耳曼式”的民族身份認同概念也同樣依賴于文化、語言和民俗學。從“1848年革命”失敗直至在1871年德意志統一后,知識分子一直在主張對普魯士做進一步的定義,并與普魯士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這也與德國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基督新教教義相接近。到了19世紀末,知識分子對民族身份概念定義時,又塑造了另一種解釋——“德國人民”。人民的概念賦予了這個民族一個重要的核心:一種結合了文化、生物學與民俗學的本質。著名歷史學家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在他的作品中闡述了這個概念:“民族的概念是歷史進程中自己形成與發展的結果;人們在歷史中建立了民族的軀干,這些只是這種概念中的一個部分。沒有民族的概念就沒有一個基本方向。民族的概念是恒定、統一和存在具體形式的力量,但它并非原始力量,它是在歷史的發展中建立的。它不會恒久保持不變,而是在歷史中演進。”[2]
德國的民族主義理論被記者和考古學家所推廣,這些研究民族的群體創建了他們自己的領域——“民族共同體”,并很快出現了和種族主義學說的聯系。正是這個“日耳曼性”的修改版本,最終不幸成為了納粹主義的特征。1945年之后的一長段時間內,研究者們都有些刻意避諱這個概念,有關于民族主義及其模式的任何討論都很容易被定義為“新納粹主義”。然而,尋找一個新的民族意識卻無法擺脫之前存在的意識形態,因為意識形態的延續性客觀上是人們在研究中無法繞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歷史學家、作家以及知識分子都做了嘗試,希望將德國超脫出前納粹意識形態,然而他們許多人本身卻早已被納粹意識形態的思維所定型。當然,在戰后一段時期,主要出現的新型思維方式是對西德民族身份的認定,除了主要的政治現象之外,基于公民、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印記還是基本被認同的;西德的政治家們和知識分子也比較青睞歐洲聯邦制的政治概念。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知識分子們對民族身份的嚴肅辯論才再次真正展開了。
法國現代的民族概念的形成與德國不太一樣。至少是從15世紀法蘭西王朝時期開始,一種所謂的“民族感情”意識就已明顯出現了。不過,“1789年革命”發生的時間點,還是被多數學者看作對民族概念進行詳細闡述的重要時間。當然,民族這個詞在語言上可能在人們還沒有形成概念意識之前就已經存在。但是直到經歷了18世紀80和90年代的社會動蕩之后,現代共和主義的民族概念才得以真正形成雛形。米歇爾·維諾克解釋說,“法國制造”的民族概念建立于革命、人民民主和法律意志之上;成為一名法蘭西共和國公民就是成為法國人,反之亦然。但是與這個斷言相對的是,保守的反革命分子、傳統歷史學家卻在構想著另一種差異很大的國家與種族概念。他們拒絕共和主義,認為這是一種不利于法國發展的模式。他們設想將人種作為民族文化的根本,而不是法國公民這一定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和主義及保皇主義者視角下的民族觀念卻共同分享了某些灰暗的種族主義思潮。一旦出現任何與精英文化相關的討論時,共和黨人就會要求整個范圍內的公民團體對上層的忠誠;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法國還建立了現代海外殖民統治規則。保皇黨的民族主義,對法國在文化和種族方面的觀點有著負面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顯赫的“法國行動”(Action Francaise)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實例,當時的保皇派支持者們出現了趨向于法西斯主義的思潮,甚至還鼓吹對納粹團體的支持。法國的共和黨與反革命部門的穩定性也逐漸消失。我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者觀念的改變,這種改變體現在各種民族身份認同的標記之上:語言、文化、王朝、民族共同體和公民生活。
對法國人而言,民族概念是幾乎不變的雙向主題,左右兩派在200年間持續對峙,而其中法國大革命對其的解釋則對文化和政治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史學界對1789年革命的合法性與否的爭論一直存在著,這也客觀上讓一直致力于法國定義的歷史作家形成了完善的核心團體。相比之下,德國的情形是由連續的民族建立片段所構成;換言之,一種“日耳曼性”思維模式代替了其他的觀點,并總是對歷史學界產生影響。例如,浪漫主義的德國歷史學家最初受到了一個瑞士作品的影響——約翰·馮·穆勒的《瑞士聯邦歷史》,并通過該作品來幫助構想“日耳曼性”的原始模型。卡爾·馮·羅泰克和海因里希·盧登的研究繼承了這種民族史學模式,他們的出版物也成為了早期民族主義運動的重要作品。當然,后世的歷史學家們通過補充,對“日耳曼性”本質的各方面進行了重新起草。
概括來講,法國相比德國對于共和黨和保皇黨之間的政治身份保持了長期的穩定性,并演化為一個單獨穩定的核心爭論。在德國不存在這樣一種持續了200多年的爭論。德國所需要面對的是,如何將納粹主義作為在1945年之后民族歷史中一個基本事件;而法國則要判別1789年的場景是否與法國的穩定與分裂間存在相關關系。民族意識的基本核心觀念的根本變化,對歷史學家在遇到其它不同點時如何進行論述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歷史學家與法國共和黨對過去的傳統解釋是從一種獨特的模式,是從反革命保皇黨或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批判中開始進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者對階級這一概念的處理非常有意思;共和黨的民間世俗主義甚至還接受了宗教方面的原始觀點。不過,大多數人認為,共和黨的愛國主義史學實際上從更廣泛的趨勢分裂了法國,而當開始將種族及種族主義融入民族史學時,這些法國與德國的專家就會自然而然被聯系起來。
二、德國與法國眼中的民族意識
1517年,歐洲大陸上刮起了一陣旋風,馬丁·路德提出了著名的《九十五條綱領》,宗教改革運動從德意志國家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這是一次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思想解放和政治運動,同時也奠定了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分庭抗禮的局面。而德國作為該運動的發起國,確定了“教隨邦定”的原則;德國的宗教觀念也形成了獨到的體系。
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標志著德法兩國在宗教歷史上呈現出聯系和區別。在結構上,兩者相似;可是在實際表現形式上卻大相徑庭。德國的歷史記載形成經歷和人們想象中是不同的。根據考證,第一代的現代德國歷史學家絕大多數是由新教牧師的孩子們所構成。因為以前文化學習不是那么普及,而牧師的孩子卻有著與眾不同的條件,可以追隨他們父親的腳步開始閱讀神學和學習文化。具有代表性像蘭克、德羅伊森,這些歷史學家將他們自己視為被上帝授權之人,他們有義務通過他們的編史實踐來證明上帝的行為,傳達上帝的指示。因此,早期歷史專業人員被稱作為“克萊奧的牧師”(Clio's priests)。同樣,鑒定歷史中的“主導概念”也是歷史學家們的任務,通過這些可以直接與上帝交流,并讓上帝與人類的歷史規劃緊密相連在一起。另外,歷史學家還要選出“上帝的代言人”,并有權利和責任對其進行考量。歷史學家是整個現實世界命運的敘述者,他們的任務是以帶有崇敬的態度和準確地方法論來講述這些故事。隨著新教神學愈發根深蒂固,其前景與民族主義的愿望也密切相關起來。1848年之后的所謂的“普魯士小型德國學派”(Prussian Small-German school)代表包括特奧多爾·蒙森、屈萊頓和海因里希·馮·西貝爾等人,他們確信:信仰新教的普魯士未來應當作為統一德國的主權國家。于是,歷史書寫、新教推動和普魯士的世俗權利三者齊頭并進。此外,普魯士的新教歷史學家將理論建立在一種知識遺產之上。因此,這個國家一定會考慮新教的潛在影響在德國史學所占的作用。理論上,利用這種跨越國界的宗教信仰,可能且可以打開了一條獲取自由民族認同的道路;這和“七月王朝”(1830-1948)期間,弗朗索瓦·基佐站在浪漫自由立場上贊美英國那樣。但是,普魯士新教終究沒有采取這條道路。相反,它的命運要和君主制信念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延續性相靠近。
到了19世紀80年代,堅持這種解釋的學派逐漸被邊緣化。尤其是在20世紀早期,德國技術的文化新潮使得許多老派的新教歷史學家困惑不解;到20世紀30年代時,力量核心也出現了根本的變化:“種族-民族”間的民族認同組合成為了主導力量,一直以來循序漸進的新教歷史傳統暫時變得沉默。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一個新教受影響的證據讓其重新顯現出來。吉哈德·里特爾的持續影響理論是戰后著名例子中的一種。他認為,希特勒的納粹其實是偏離了正常軌道。因此,在他1848年發表的作品《歐洲和德國問題》中,重新使用民族和新教的組合,并將其作為一種后納粹時期的自我防御。他的論點在于:盟軍的宣傳將同時代歷史過于簡化,并德國過去的歷史過于妖魔化;路德和俾斯麥也不應被視為希特勒主義的幻影。皮埃爾·阿克拜來這樣形容里特爾:他是“帶有原始過去的德國養育者,僅僅屈服于意外的誘惑”。[3]在20世紀60年代,歷史發展中的宗教問題,在歷史主義關注方面,變得不受歡迎。當然,在社會歷史被確立作為歷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論范式后,并且社會人民就被作為思考過去的一種新型指導方式,宗教則被忽略了。焦點在于經濟和社會進程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受韋伯和年鑒學派鼓舞啟發,取代了以前宗教所扮演的角色。典型的德國觀念主義被唯物主義“社會”的概念所取代。原本成員已經幾乎完全由新教徒組成的大學學院,從那時起開始涵蓋天主教或非宗教歷史學家。對左翼的專業歷史學家而言,“宗教和民族”可以作為一種合成體來敘述,而這對標榜推廣自己的右翼宣傳家來說卻成了不太真實的視角觀點。左派和右派史學之間顯現的反差,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漢斯·烏爾里希·韋勒和托馬斯·尼佩代從事的針對德國歷史的兩個主要項目之間的比較。韋勒的《德國社會歷史》至少在前三卷中都忽視了宗教、教會和信仰。相反,保守的尼佩代卻賦予了它重要的空間。近年來,左翼歷史學家在歸納文化和概念的新發現興趣點時,重新引入宗教和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左翼歷史學家這對兩種術語的使用都比之前的20年更為頻繁。通常情況下,這種使用是對這些概念的解構,或是散漫形式的探索,而并非單純意義上對原來論述的復制。
按照共和黨人的傳統,沒有一個宗教信仰體系能夠在法國主導民族主義史學。當然,天主教和保皇主義者間有著強烈聯系,但他們只是代表超越1789年革命意義的一種歷史線路劃分。就像德拉克洛瓦、多斯和加西亞解釋的那樣,在19世紀晚期時,從巴黎的古斯塔夫·莫諾參與的刊物《歷史雜志》(Revue historique)可以看出,科學方法的概念同共和黨與世俗國家進步的愿景之間是同步進行的。對莫諾而言,專業歷史學家的任務在于,鑒別歷史發展中連續性脫節的部分并將其拼湊起來。當然,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學家的責任是將其完善在一起。共和主義和科學方法完美協調在一起,因為兩者都處在理性和進步的一邊。對認同共和黨歷史的專業人士而言,比如莫諾或瑟諾博司,他們通過全面理性的方法去講述過去的故事,最終呈現出來的民族歷史便會出現更好、更全及更嚴謹的結果。“歷史科學”的概念在于,允許某種民族遺產完整化身為作品,并通過歷史學家的作品慢慢地將其揭示。這些革命的歷史,這些法國故事中對于“人民”構成的不同爭論,最終都被聚集在一種單個的科學敘述中,這可以對祖國的概念更加了解并整合在一起。這是一種拒絕宗教及含有非理性力量的歷史敘述,這種非理性還會讓任何對民族歷史的理性理解都簡單混淆在一起。
法國的共和黨科學理念和世俗史學的威脅,并沒有讓天主教歷史學家和知識分子迷失。諸如于斯曼那樣的思想家以及像馬西斯及塔爾德那樣的歷史學家,悲觀地將新經驗主義看作為一種不幸的變化趨勢。在巴黎大學的學院間流行的新歷史學派對方法論的要求非常嚴謹,他們認為事實收集、卡片索引這些行為非常可笑,認為這種方法完全忽視了法國歷史寫作的特點。天主教復興知識分子的史學(1871-1914)認為方法論并非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對他們而言,引入這種概念就是引入新教德國的愚蠢行為。對于這個團體而言,法國歷史是關于精神、意義和唯一的天主教之神上帝,簡言之就是智力、人才和靈性,這些才是進行宏大計劃時,可以了解法國角色和地位的明確指南;方法論是無法對此代替的。
在19世紀80年代,共和主義科學民族史學和天主教精神史學之間進行了一些小范圍的辯論,辯論中找出了“民族主義-史學-宗教”間的廣泛交叉性。在共和黨和反革命潮流的歷史解釋中,宗教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革命遺產在部門建立和多重解釋的趨勢中形成了不同的角度。籠統地講,對于那些通常受新教徒支持的共和黨人而言,民族歷史傾向于宗教身份的考慮,同時也映射了一個通過長期進展,并獲取共和黨理性主義勝利的故事。伏爾泰的生活和作品中,大量描述了啟蒙運動和早期革命時代。教會的罪惡,尤其是反宗教改革、宗教裁判所等,伏爾泰不停地提醒著讀者關于教權主義的危險。簡而言之,共和黨人的民族主義史觀傾向于強調自身的歷史發展,并把改革視作革命的前期準備;相反地,神職人員的歷史罪行應該被譴責,并在修辭上對反宗教恐怖進行了注解。沒有歷史學家可能會將其如此直觀,但是請允許我們說,那是史學趨勢的精神。就如羅伯特·吉爾提出的觀點,通過一種修補關系的努力以及一種尊重天主教信仰的觀點,把其變成一個更加團結民族共和黨的家庭。共和黨傾向于攻擊諸如耶穌會那樣的教派,并非在大體上僅僅只是外在的宗教本身。
對右翼的保皇派而言,天主教身份和反革命民族主義有關聯,并且直到今天在關于民族討論的前沿中依舊存在。法國的特殊性質在于其作為教會的長女角色。它的民族歷史是一種精神,而并非一種世俗之事;1789年革命對其而言是一場災難、一種神的懲罰行為,這也是共和黨時代對一種以前罪惡進行贖罪的短暫時期。就像吉爾解釋道:對天主教右翼的愛國者而言,所有民族發生的災難都可以模仿這種敘事模式,比如1940年在奠邊府①越南奠邊省省會,位于越南北部,緊臨上寮,南北長約18公里,東西寬約6公里,是四面環山的盆地平原地形。法屬期間(1884-1954)奠邊府成為法國最大軍事據點,駐守約二萬名法軍。和1962年在阿爾及利亞出現的情況。他們認為,民族的苦難屬于長期懲罰的歷史,這是神的旨意;在這種思想學派中,現代世界、宗教改革和革命均被視為基本錯誤或神的懲罰。
多年來,共和主義和天主教君主主義間的變化,引發了大量更加復雜的有神學根據的和民族史學的交集。浪漫主義史學的早期,作家被視作帶有一種唯心論觀念的群體。有時,這是一種令人困惑的探求,并且圍繞著民族世俗社會概念達成了特殊的統一,這些也是儒勒·米什萊在他一些著作中所作的貢獻;另一方面,更復雜的反神學概念被認為是著名的圣·西門思想的一種。在1918年之后的時間,作為神學教義人本主義組成部分的社會天主教,從天主教的反革命傳統中分裂出來,轉而去尋找牧師和工人之間的社會精神聯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那些集團的企業雜志、精神,已經發表了編史的文章,并促成了對歷史和集體記憶的集體民族辯論。然而,它并非是一個用于民族與宗教言辭的智囊團。今天的史學在辯論中多數是以世俗的、新科學的模式來進行書寫。
三、德國與法國的歷史敘述發展分析
德國和法國之間存在的民族差異是兩國歷史敘述演進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法國而言,1789年革命和共和黨傳統強化了民族身份中的公民概念,并且更開放地探索社會權利和社會歷史。德國本身沒有以這種風潮發展,在過去20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主流德國歷史學家不愿在他們的作品中融入階級概念。法國共和黨人的世俗主義意味著,宗教扮演的角色沒有像信仰新教的德國那樣專業。這些都是關系到重要分量的顯著差異。歷史學家對其他概念的解釋,結合了民族主義,表明了法國和德國間的分歧。簡而言之,歷史學家對階級概念、宗教和位于民族敘述之中種族的處理產生了潛在的民族敵對情緒。德法兩國的分歧也造成了相互間史學觀念差異:德國對階級概念感到恐懼并且排斥,法國共和黨人對此展現了敏感和革命的態度;德國對于法國歷史發展的浮夸和奢靡不屑一顧,而法國對種族理解源于對“高盧人”衰弱的同情,并且包含了對日耳曼法蘭克人或“野蠻人”的詆毀;在宗教方面,德國新教的科學方法研究和法國天主教的民族主義史學中的排外性也是格格不入的。盡管每種差異的程度大小不一,但是綜合所有的不同,這些都成為了民族張力長鏈條中的每一個鏈接點。
總而言之,德國的著作讓新教民族主義者見證了悠久的歷史,但是沒有涵蓋天主教民族主義者綜合的觀點。德國新教神學培訓是19世紀德國歷史研究誕生的代名詞。盡管有一些作家在他們的作品并未發揮出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種傳統沒有產生出任何一個有關“民族”的文本。法國的立場截然相反,有關的詮釋的確通過多重聯系發展了。在尖銳的矛盾中,法國天主教的思潮譴責這種做法為啟蒙運動,宗教失敗和受外國玷污的衍生物。具體來說,世俗和天主教歷史學家之間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民族敘事分歧,其中神的概念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天主教愛國史學沉迷于法國做為教會長女的身份,沉醉于中世紀的輝煌概念,敏感于現代世界的罪惡。毫無疑問,共和黨人是以不同方式來看待這些問題。他們把傳統的宗教視為王朝暴政和過時的保守主義。盡管如此,在1914年國家受到威脅時,法國宗教分支中任何一方的歷史學家們都支持神圣同盟對抗德國。法國共和黨對新教主義及對新教的同情心沒有擴展成像德國新教的跨國親和力。
當然,德國新教思想學派與法國天主教愛國史學在19世紀后期還是分享了簡單的結構特點。兩個團體的歷史學家都在宣稱,在上帝的宏偉設計中,自己的民族起著獨特的作用。兩個團體都通過知識分子、歷史學家等來解釋這些進程。民族意識、宗教信仰和歷史學家的任務終于合并在了一起。然而,至少在名義上,即使德國新教教義規定了運用經驗主義的歷史方法,可是還是沒有完全付諸實踐之中。盡管如此,我們可能現在還要強調一些潛在的相似之處。例如在語言修辭上,法國天主教和德國新教在言辭上仍有一定可比性。兩國在宗教解釋上,都認同將歷史學家的任務作為一個對上帝計劃。他們都認為各自的民族是被他們神所“選中”的。他們互相攻擊對方是有著異教習俗的外國人。種族思考和反猶主義的總體概念也是雙方國家民族主義作品的一部分。歷史學家將民族意識和種族概念相關聯,提供了關于“民族-文化-種族”起源問題的經驗主義敘述。作為一個主題,歷史學家還將種族和愛國主義敘述結合在一起。
我們還可以通過一種演繹來歸納兩國間的歷史敘述演進。傳統意義上,民族主義在遇到跨民族概念時,一般會出現四種經典的演繹方式:融合、恢復、利用、排斥。天主教的法國和新教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們將神學世界觀融入到世俗的愛國主義敘事之中;預先存在的宗教信仰體系融合到新的民族觀念中。融合一般是將潛在的矛盾概念融入一個相對和諧散漫的結果之中。恢復則是一種更為復雜的模式。當民族歷史學家使用跨民族概念來支撐他們的目標時,往往會缺乏完整的綜合對象。這種關系也被德法的歷史論證了,歷史學家利用種族思想和反猶太主義來強調他們對各自民族的贊頌。當一個歷史學家采納不同知識體系中的觀點后,可以在新環境中利用它作為知識儲備的優勢。德國和法國的共產主義史學表明了一種第三類的關系。階級的觀點明顯扮演了一種遠高于民族主義的塑造力。當然,共產主義歷史學家也希望獲取更多對本國的認可,并擁有以諸如抵抗外國侵略和解放這樣的經歷而自豪。排斥的概念是第四種常見過程,因為這些會干擾或者出現對某人意識形態批判性。民族歷史學家采用了這條線路:德國民族主義者忽視或反對階級的概念,法國公民共和黨人在捍衛自己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民族公民權利時,也擯棄了種族或文化認同的概念。總而言之,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許多以前被忽略或誤解的歷史敘述、歷史觀念等都會逐漸被凸顯及細化;尤其作為對歐洲甚至全球影響巨大的兩個國家,如何通過共同的努力和平發展并獲得共贏,我們拭目以待。
[1]CHARLES PEGUY.Reactionary Revolution[M].Griffiths,44.
[2]J.G.DROYSEN.Historik[M].Peter Leyh(Stuttgart,),1977.305.
[3]G.RITTER,EUROPA.die Deutsche Frage [A].Munich,1948.P.AYCOBERRY.The Nazi Question: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 Socialism[C].London,1981.119.
[4]吳友法,梁瑞平:德法和解是早期歐洲一體化的基石[J].武漢大學學報,2002,(5):599-606.
[5]華少庠.18世紀德、法作家—讀者二元體系與兩國歷史環境比較[J].南華大學學報,2007,(5):108-111.
[6]華少庠.18世紀德法兩國作家—讀者二元體系的比較[J].廣西社會科學,2007,(8):135-138.
[7]戴婷.試析二戰后德法和解中的歐洲一體化因素[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4):58-60.
[8]李伯杰.德國文化史[M].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36-37.
[9]丁建弘.戰后德國的分裂與統一[M].人民出版社,1996.15-17.
K091
A
1002-3240(2017)03-0144-05
2017-01-11
徐璟瑋(1981-),華東師大學歷史學博士,上海理工大學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德國歷史。
[責任編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