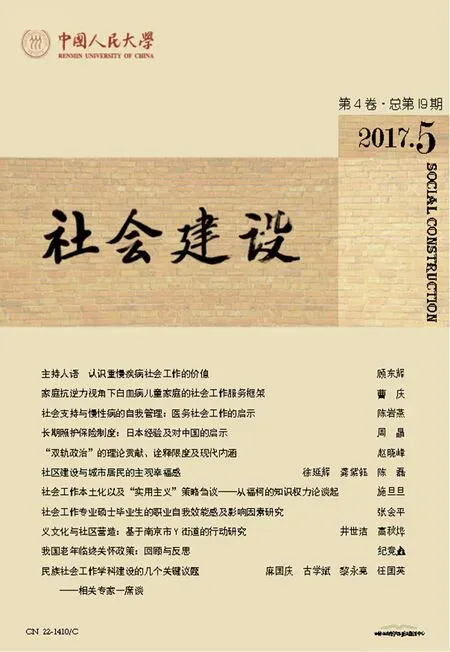“雙軌政治”的理論貢獻、詮釋限度及現代內涵
趙曉峰
□ 社會治理
“雙軌政治”的理論貢獻、詮釋限度及現代內涵
趙曉峰
雙軌政治是費孝通在解讀基層行政體制僵化時提出的重要概念,既有縣政與村治上下分層的治理領域劃分意涵,也有政務傳遞與壓力反饋上下通達的信息溝通意涵。雙軌政治這一概念的理論貢獻在于對中華帝制時代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給予了深刻解讀,蘊含著對中國傳統文化治理價值的理解和對理想社會政治模式的思考。費先生高度重視地方自治單位的重要性,卻沒能對家族與族權性質進行深入分析,難以詮釋國家政權建設與地方自治單位的辯證統一關系。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持續推進和現代性的不斷浸潤,地方自治單位的性質發生根本變化,村莊民主自治模式不斷完善,社區社會組織蓬勃發展,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加速重構,促使雙軌政治在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中顯示出積極的現代治理價值。
雙軌政治;基層行政;國家與社會關系;地方自治單位;社區社會組織
“雙軌政治”是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形象地刻畫了傳統中國官僚體制與地方自治的政治生態結構,對國家—社會關系以及基層社會治理的研判具有時代的穿透力,而學界對這一概念尚缺乏深入的跟進研究,更少有將這一概念與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結構變遷關聯起來的理論研究。
一
關于“雙軌政治”的理論貢獻,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其對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的解讀。張東蓀認為,雙軌可以用來描述傳統中國的政治軌道,本質上是甲橛和乙橛的關系,其中,“甲橛是皇帝的政權和官僚的政治,乙橛是鄉民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實行的互助”。①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5頁。甲橛和乙橛的劃分將皇權官僚體制下縣域政治社會治理結構的典型特征做了生動形象的簡單描述,這意味著在中華帝國時期,存在兩種秩序和力量:一是“官治秩序”和國家力量;二是“鄉土秩序”和民間力量。②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8.由此延伸出的問題是皇權的邊界向下延伸到哪里?按照費先生在《基層行政的僵化》中的描述:“中央所派遣的官員到知縣為止,不再下去了”①⑤⑦⑨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5頁;第151頁;第7頁;第151頁。,無疑代表皇權的行政機構止于縣級政權。雖然費先生并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溫鐵軍第一次清晰提出“皇權不下縣”的理論觀點后②溫鐵軍:《半個世紀的農村制度變遷》,《戰略與管理》,1999(6)。,學界依然將其淵源追溯到費先生提出的“雙軌制”③④ 胡恒:《皇權不下縣?——清代縣轄政區與基層社會治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第15頁;第15~16頁。。
這種認為皇權設置的行政機構止于縣,縣以下由鄉紳等民間勢力控制而并行統治的“雙軌制”思想,在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學科中比較流行,同時也飽受爭議;尤其是一些史學研究者,試圖推翻“皇權不下縣”的理論判斷。④將“皇權不下縣”的理論觀點追溯到費先生的“雙軌制”顯得有些偏頗。費先生提到,中央派遣的官員到知縣,而知縣掌權的衙門里還有皂隸、公人、班頭和差人之類的胥吏,他們要直接代表統治者向下傳遞縣政府的命令。如果縣政府的命令通過胥吏“直接發到各家人家去的,那才真是以縣為基層的行政體系了。事實上并不然,縣政府的命令是發到地方的自治單位的,在鄉村里被稱為‘公家’那一類的組織”。⑤因此,皇權向下延伸的邊界應是止于地方自治單位。
那么,何為地方自治單位呢?費先生在批評保甲制時指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政治單位必須依據生活單位”,但保甲制在推行中以數目來規定,力求一律化,破壞了地方自治單位的完整性,造成生活單位和政治單位的混亂。由此可以看出,地方自治單位應是人們的生活單位。在1938年出版的《江村經濟》中,費先生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人們的生活單位即是村莊。村莊是一個農戶聚集的社區,具有特定的名稱,是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保甲制直到1935年才進入開弦弓村,并且在實施過程中流于形式,未能產生實際的治理效果。⑥費孝通:《江村經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8頁。在《鄉土中國》中,費先生更是明確指出,“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⑦村落在農民生產生活中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使農民對其產生了高度認同和依賴,并在學界衍生出村落共同體的討論。村落共同體以土地的私人占有為基礎,以村落共有的水利設施為補充,內部形成了關于耕地和耕作的規則、用水的規則等共同體規則,并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生活規范。⑧樊 平:《村落公共權力: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韓明謨等著:《社會學家的視野:中國社會與現代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年。正因皇權未能進入自然村落,基層社會才會在聯合解決生存安全、水利供給等超越單個家庭之力才能化解的公共品難題中,形成歷史感和歸屬感,醞釀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地方文化和傳統。村落不僅是承載農民日常生活主體實踐的場域,還是孕育農民個體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的重要載體。因此,皇權才不應隨意進入村莊,以人為的政治單位去分割或合并人們的生活單位。⑨故“皇權不進村”應被視作理解“雙軌政治”概念內涵的重要維度之一,表達了費先生對國家行政權力與地方自治權利銜接邊界的認識和判斷。
二
村莊作為地方自治單位,其治理主體是被稱為管事和董事的地方領袖,即紳士。他們既擁有處理地方公務的權利,又擁有出入衙門直接與掌握實權的官員協商的權力。因此,紳士既是皇權在地方社會的代理人,又是村莊內部民眾利益的保護人,在鄉村政治社會生態結構中扮演著至為重要的角色。
首先,紳士是村莊經濟結構中的地主。費先生對紳士存續的經濟基礎有著清晰的認識,他認為,“經濟結構中的地主階級是這個社會結構中的紳士。”①③ 費孝通:《中國紳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14頁;第31~32頁。在資源匱乏的傳統社會,對普通農民來講,生存安全遠重于經濟發展的考量。因此,紳士能憑借其擁有的相對豐富的經濟資源去幫助地方自治單位中的普通農民,構建一種不平等卻又溫情脈脈的階層階級關系。這種關系類似斯科特在東南亞地區小農經濟中發現的在地主與佃戶之間的庇護關系,地主即保護人要在災荒之年保護其佃戶(被保護人或委托人),助其渡過難關,并在正常年份給予弱勢小農多方面的道義照顧。作為回報,被保護人則會提供全面的協助,成為富人的追隨者。②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程立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第52~53頁。庇護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地主對佃農的剝削色彩,讓租佃關系具有了道義倫理的特征。不僅如此,紳士往往還掌握著村莊里的“公田”或“族田”,而這些帶有鮮明“公家”特征的田地,大多以較低的地租出租給本村本族的貧寒人家,收益分配在滿足“公家”必要開支外,在災荒之年優先用于照顧貧寒人家。
其次,紳士是皇權在村莊政治結構中的代理人。在小農經濟剩余有限的情況下,皇權奉行的是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傾向于推行輕徭薄賦的利民政策,并將基層治理的重任交由紳士承擔,使其扮演皇權在村莊政治結構中的代理人角色。費先生在分析“學者當官”時指出,學者在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下,逐漸從實際政治中分離出來,放棄奪取政權的企圖,在朝廷的寬容下求得安全,成為倫理路線的維護者,并不對政治發生積極的影響。因此,作為學者的紳士,在傳統中國的權力結構中是一種非斗爭性因素,構不成對皇權的挑戰。③同時,紳士的成長軌跡顯示,紳士是一個家族理性選擇、集體培養的成果;其被自身所屬的家族選中,作為家族代表,由眾人出資供養并接受教育,通過官方考試入仕做官。紳士為官是為了獲取相應等級的豁免權和物質財富,為所屬家族提供政治庇護。然而,紳士接受教育的過程,就是接受皇權提倡的儒家意識形態的過程。受此影響,紳士會成為儒家倫理的接受者和維護者,因而與皇帝及整個官僚體系中的官員共享一套意識形態,成為皇權在地方自治單位中自覺的捍衛者。
再次,紳士是村莊社會結構中的道德權威。紳士憑借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和較為豐富的儒家倫理知識,很自然地成為鄉村領袖的主要人選。雖然為官的經歷為他們衣錦還鄉受到擁戴、享有社會權威創造了條件,但他們依然需要贏得地方自治單位中民眾的認可,在文化網絡中鞏固、夯實其權威的合法性,繼而才能長久維系這種特權。這意味著,一方面紳士在處理地方自治單位中的“公務”時要力求公平公正,必須按地方規則辦事,不徇私情;另一方面紳士在處理外來的“公務”時,需站在地方自治單位整體利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竭力保護受其庇護的民眾的權益免受官方權力的肆意侵犯。因此,紳士在民眾心中成為村莊社會結構中的道德權威,成為地方利益的保護人。如果皇權過于強大,或官方權力肆意向村莊社會滲透,使紳士失去為地方利益代言的機會而不能很好地保護民眾利益,他們就會逃避,從而使村莊社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保護型經濟被營利型經濟所替代,鄉村社會成為劣紳橫行的場所。④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最后,紳士是村莊文化規范的意義詮釋者。鄉土社會的基本秩序特征是禮治,維護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教化則要依靠受過教育具有識字能力、以學者身份出現的紳士。通常情況下,在人員流動性小、邊界清晰的村莊社會里,有一套經由歷史經驗沉淀而成的文化規范。在理想狀態下,人們通過社會化的過程,不斷習得村莊文化規范,并將之內化為自身的習慣,用以克己修身,提升修養。由此,人們幾乎不會向傳統規則發出挑戰,只需安分守己、恪守規范,就能獲得規則限度內隨心所欲的自由。但是,瑣碎、復雜的日常生活難免使人們磨牙生氣、產生糾紛,打破平靜的禮治秩序,產生“評理”的需求。主持評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個很會說話的鄉紳開口”,“他依著他認為的‘應當’告訴他們”,把當事人雙方都罵一頓,就把糾紛化解了。此時,保長雖然在場,卻從不發言。①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6頁。因此,紳士作為擁有特權的社會權威,掌握著話語權,是村莊文化規范的意義詮釋者,是維護禮治秩序的主導力量。在傳統鄉土社會中,紳士是一個有閑階級,“他們的主要任務是使傳統規則永久化”,從中鞏固他們的特權。②費孝通:《中國紳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43頁。
顯然,在費先生的視野中,紳士是理解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重要切入點。然而,這里的紳士概念并沒有嚴格界定的內涵和外延,缺乏明確的目標指向。在費先生的論述中,紳士與知識分子、學者、退休官員、官員的親屬、受過簡單教育的地主等或相提并論或有交叉,具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像是一個連續譜系。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費先生的紳士明顯不同于后續研究者提出的“地方精英”。地方精英是“在地方上行使支配權力的個人或家庭”③Joseph W. Esherick, & Mary B.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0.,其主要考察的是能否在地方發揮實際的支配作用,而不管其是商人、紳士、資本家,還是土匪首領④郭金華、林海、孫立平:《中國傳統生活中的皇權》,李培林、孫立平、王銘銘等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社會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第88頁。。其中,地方精英不再是道德的化身,地方精英研究具有明顯的去道德化傾向。⑤狄金華、鐘漲寶:《從主體到規則的轉向——中國傳統農村的基層治理研究》,《社會學研究》,2014(5)。相比地方精英,紳士這個概念雖有指代不清等不足,但更切合地方自治單位和農民生活單位的實際;而所謂的土匪首領等地方精英則往往構成地方自治單位防范的對象,也是村落共同體凝聚力來源的重要外因。因此,將紳士視作地方自治單位的基本治理主體應被作為理解“雙軌政治”的另一重要維度。
三
費先生認為,傳統集權與分權(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一個“協調關鍵”,基層行政僵化的原因在于中央職能的加強破壞了這個“協調關鍵”,使政治雙軌制變成政治單軌制。⑥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2頁。這里的“協調關鍵”實際上存在于知縣和紳士、國家與村莊社區之間,囊括知縣下派的皂隸、公人、班頭和差人等胥吏以及鄉約等兩類行動主體的活動空間。一方是代表帝國利益專享行政權的知縣,一方是代表村莊社區整體利益享有自治權的紳士,兩強之間“協調關鍵”的本質是構建了一個官方權力與地方自治權利的“協調地帶”。通過“協調地帶”的創設,知縣委派的胥吏和村落社區的代表鄉約達成“公務”上的溝通,避免行政權和自治權的直接碰撞,維護知縣和紳士各自的面子。由此,在“雙軌政治”模型中,中央集權的國家將稅賦和兵役等政務指令經由層層的官僚體制下達給知縣,知縣經由衙役、胥吏傳遞給鄉約,再由鄉約轉達、請示紳士。如果紳士認為這些政務指令超過了地方自治單位的實際承受能力,就會將之退回去。在這個過程中,知縣和紳士并沒有直接、明面上的公務往來;利益受損的可能是鄉約,因為他們會被衙役胥吏送到衙門以辦事不力的罪名接受處罰。但是,自下而上的溝通往來很快就會在私下里啟動,紳士會利用其地位與知縣接洽協商,甚或利用他自己或是親戚朋友、同鄉同年等私人關系到知縣的上司那里去交涉,直到舊的政務指令被修訂。從中可以發現,“協調關鍵”可被看作是理解“雙軌政治”概念內涵的第三個重要維度。
知縣與紳士之間的“協調地帶”,形式上類似黃宗智提出的“第三領域”。在“第三領域”中,司法規范比較復雜,“帶有成文法典和官家法庭的正式司法體制”與“通過宗族/社區調解解決爭端的根深蒂固的習慣法構成的非正式司法體系”都能參與其中。①黃宗智:《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間的第三領域》,載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260~285頁。并且,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即原則上由社區推薦和政府認可產生的“準官員”,包括鄉保、鄉約和牌長、村長等。在黃先生看來,準官員是第三領域中的治理主體,而正式司法體制和非正式司法體系中的制度規范則構成準官員行使治理權時可以綜合利用的規則資源。由此,國家得以避免將正式機構下沉到地方,只需依賴半正式的準官員就能維系鄉村社會的治理秩序。②黃宗智:《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半正式基層行政》,《開放時代》,2007(2)。但是,費先生提出的“協調關鍵”和黃先生所講的“第三領域”卻有根本的不同。費先生認為,無論是胥吏,還是鄉約,都是沒有實權且社會地位低下的人,他們并沒有自主活動的空間,發揮的基本上只是上令下傳和下情上達的信息溝通功能。村莊社區里真正享有治理權力的是紳士,他們要處理水利、自衛、調解等地方“公務”。而在黃先生的“第三領域”中,準官員擁有相應的治理權力。由于在黃先生的研究中,很少能看到準官員發揮作用的實踐機制,難以判斷準官員享有何種樣態的治理實權,“第三領域”概念遭受質疑。③趙曉峰:《公域、私域與公私秩序:中國農村基層半正式治理實踐的闡釋性研究》,載周曉虹、謝曙光主編《中國研究》,2013年秋季卷,總第18期。
第三領域和協調地帶認識的不同,源自于黃先生和費先生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不同認識。黃先生從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中尋找理論資源,提出在中國存在著一個國家與社會都參與其中的第三領域。黃先生的學術旨趣在于超越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關系,但同樣也預設了一個互相排斥的二元領域,未能辨識出國家法與民間法是一個“連續體”的客觀事實。④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第9~20頁。相反,在費先生看來,集權的國家與自治的村莊社區之間是并行不悖的關系,雙方并無實質性矛盾。從形式上看,村莊社區的自治在皇權認可的限度內,沒有哪個村莊會去尋求皇權默認或授權之外的權利;從實體上看,行使自治權的是紳士,而紳士是在皇權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的教化中成長起來的,是皇權官僚體制的捍衛力量。紳士及其功能說明,國家與社會之間并不是截然分明的關系,通過紳士階層的培育,皇權能夠依靠意識形態實現對看似自治的村落社區的治理。紳士不接受知縣下達的“公務”,并非是對皇權不滿,而是為了更好地協調國家與地方自治單位之間的關系,避免知縣及以上的官僚層層加碼和加重人們的負擔,從而危及皇權合法性的民意根基。紳士積極地通過私人關系的聯結紐帶向上直至皇帝傳遞信息,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在費先生的視野中,中華帝國時期,國家與社會之間是一體而非二元的關系,協調地帶是追求無為而治的皇權為維護紳士的地位,避免國家權力與地方自治權利發生明顯的沖突而生發出的彈性機制。
由此,從雙軌政治的三個理解維度可以發現,雖然費先生并沒有刻意提出自己的理論旨趣,但這一概念對中華帝制時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給予了深刻解讀,使后輩學人能夠以社會學的想象力予以見仁見智的闡釋。由于紳士所處的上下通達的位置,國家之法治與村莊之禮治并非二元對立的關系,紳士在上升的過程中受到國家法制精神的教化,并得以掌握村莊文化規范的意義詮釋權,從而使國家之法與村莊之禮得以融合,能夠以異形同構的形式劃疆而治。所以,國家之法與村莊之禮皆為儒家文化之折射,而“雙軌政治”則蘊藏著費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治理價值和理想政治社會模式的理解,這是該概念的重大理論貢獻。
四
費先生認為,雙軌政治的破壞和政治單軌制的推行,造成了基層行政的僵化。從中可見,費先生對傳統的雙軌政治保有理想的情愫,雖然他認為自己并沒有否定加強中央權力的需要和趨勢,也沒想重提皇權無為論,甚至還提出要從民間的自治機構入手改革社會①②③④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4頁;第58頁;第34頁;第24頁。,但對地方自治單位的性質和改革必要性缺乏深入分析,對國家政權建設與地方自治單位的關系關注不夠。村莊社區是一個地緣單元,但“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②。因此,地方自治單位的背后隱藏著的是血緣關系,是“擴大了的家庭”,本質上講即是家族。費先生將家族視作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社群,認為家和家族的大小由事業的大小決定,彼此差異很大,但在“結構原則上卻是一貫的、單系的差序格局”③。然而,費先生更多關注的是個體、家庭和家族之間的差序關系,對其中的群己關系缺乏詳細論述,雖然他也意識到家族對個體具有一定約束懲罰的權力,但依然覺得鄉土社會存在這樣一個事實上的公式:“為自己可以犧牲家,為家可以犧牲族……”④在將差序格局從社會關系的認識推向社會結構的分析時,費先生遭遇到后輩學人的質疑。
翟學偉認為,中國社會的最小單位是擴大的家庭,而家庭又是費先生眼中的事業社群,在家庭之內個體是無法以自我為中心的,不可能“為了己,犧牲家”,而是“為了家,犧牲己”。其中,翟先生用的是“擴大的家庭”,尚未明確區分家庭和家族的異同。⑤翟學偉:《再論“差序格局”的貢獻、局限與理論遺產》,《中國社會科學》,2009(3)。賀雪峰認為,一方面家庭是中國社會的細胞,是中國農民基本的認同和行動單位;另一方面家族和以家族關系為基礎的村落是超越單個家庭之上的認同和行動單位,其壓抑了介于家與家族之間的亞級房支和聚落房支等其他各級單位的認同水平和行動能力。⑥賀雪峰:《農民行動邏輯與鄉村治理的區域差異》,《開放時代》,2007(1)。因此,有學者認為差序格局這個概念本身存在“名實分離”的內在矛盾,費先生希望用這個概念去把握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但他在具體分析中又側重從微觀層面展開分析,以己為中心,在差序的圈層中去理解個體的行動邏輯。⑦廉如鑒:《“差序格局”概念中三個有待澄清的疑問》,《開放時代》,2010(7)。所以,從社會結構而非社會關系的角度認識“差序格局”,發現家和家族的存在影響了“雙軌政治”的現實解釋力。進一步而言,費先生對家和家族的認識,也影響了其對地方自治單位性質的判斷。
宋朝的統治者接受張載的主張,通過宗法制來重建鄉村組織,借助民間組織力量治理鄉村社會。⑧曹錦清:《歷史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探索與爭鳴》,2006(10)。宗法制度的推行要求在分散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構建家族共同體的組織框架,以比三代家庭更大的家族組織來重構社會,一方面為家族中各家庭生產生活必需基本公共品提供基本保障,另一方面為維系鄉村社會秩序穩定、無為皇權的政治統治和社會控制提供組織基礎。正是在皇權開始重視鄉村組織建設、推行宗法制的新形勢下,紳士作為族權和紳權的統一體逐漸崛起,日益成為鄉村社會的治理主體。①林文勛、谷更有:《唐宋鄉村社會力量與基層控制》,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5,第180頁。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家族組織日益成為完善的基層社會組織,家族族長甚至還得到默許的部分司法權,有的家族擁有對族人的生殺大權。②常建華:《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43~51頁。家族權力不僅愈趨強大,而且遍及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如費先生所說,“在云南呈貢化城的人民如果娶了親不生孩子每年都要受公家的罰,甚至于打屁股。”③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0頁。
始自宋初的社會建設,在中國歷史上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文治復興”運動。這場運動的兩個關鍵:一是通過推行“祠堂之制”實現國家禮儀的士庶化,二是通過推行“祖先之禮”實現民間禮儀的國家化。“祠堂之制”指士大夫將祠堂作為思想生產和傳播的空間,作為行道的工具和場所進行文化再造活動。推動祠堂相對自由設立,促進國家禮儀滲入基層,進而引發了大規模的造宗族運動。“祖先之禮”則以“祖先”界定社會禮儀秩序的方式,將庶民之禮納入國家禮儀當中。這里的“祖先”即是一個宗族追溯的始祖,其幾乎全是皇室成員或官宦士大夫,自然利于“在無形之中將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到民間,同時也將民間禮儀納入國家”秩序。④張小軍:《“文治復興”與禮制變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禮的個案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通過這場運動,國家與社會得以融合,使得國家之法與村莊之禮以內在精神契合的方式共存,并且使宗族/家族走上了地方歷史舞臺。⑤本文側重從鄉土秩序和民間力量的視角分析傳統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解讀“皇權不進村”的原因。學界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還有一種官治秩序和國家力量的視角,認為行政權力無力向下延伸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財力不夠。但這種觀點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李懷印指出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帝國,有數量巨大的納稅人口,統治者只需采取輕徭薄賦的政策就能滿足財政的需要;同時,儒家意識形態中“聽民自便”、反對官府“多事”“擾民”的行政理念,也促使官方限制自己的觸角(李懷印:《華北村治》,北京:中華書局,2008)。從中可見,傳統中國國家權力滲透能力有限是學界的共識,不同的是解讀視角和闡釋路徑不同。
宋以來的農村社會建設強化了家族在基層治理中的主體地位,使家族成為形塑村莊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力量,使“國家與農民”的關系變成了“國家—家族(紳士)—農民”的關系。“血緣是穩定的力量”,家族是鄉土中國禮制社會秩序形成的重要促進力量。家族世代聚集,使村莊社區成為具有較強集體行動能力的共同體。同時,在安土重遷的思想影響下,鄉土社會的流動性較低,單個個體與家庭往往難以脫離家族獲取生存資源,造成個體與家庭嚴重依賴家族,使中國人形成了家族集體主義的行為取向。⑥楊國樞:《華人社會取向的理論分析》,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社會心理學》(上冊),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年。因此,在中國人的行為取向中,家族是重于個人和單個家庭的,為了維護家族的利益,在必要的時候不得不犧牲個體的私利。正是如此,傳統中國農民形成了有家族認同而無國族認同的政治社會信任格局,導致進入近代以后的國家面臨政權建設動力不足的困境。⑦趙曉峰:《公私定律:村莊視域中的國家政權建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在近代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出現過“一個困惑,兩種解法”。一個困惑來自民主革命運動的先驅孫中山,他認為:“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是一盤散沙,這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于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至于說到對國家,從沒有一次極大犧牲精神去做的。”⑧孫中山:《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617頁。從中可見,孫中山說中國人“一盤散沙”不僅從個體層面,更是從家族層面討論的,因為家族的存在割裂了國家與個體的有效對接,導致中國革命的動力不足。基于此認識,孫中山認為要以宗族為基礎,一級一級地改造、聯合,直到成就一個國族:“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族以抵抗外國……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的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①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239頁。與之相反,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將族權看作“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之一,提出要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以解放農民。②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毛澤東看來,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就是要打翻這一封建勢力,打倒紳權和族權,以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
因此,傳統的家族構成近代中國革命與改革的主要對象,構成國家政權建設的重要障礙。如果不能將農民從家族控制中拯救出來,建立農民對現代國家的政治認同,就難以將傳統農民改造成現代公民,也就無法為政權建設提供依靠力量和動力支撐。費先生看到中央集權的加強、保甲制的推行,破壞了農民生活單位的完整性,加重了基層行政的負荷,致使地方治理陷入困境,從而認為提高行政效率的關鍵在地方。其中的關鍵在于,現代國家建設的步伐遠遠快于地方自治單位的變遷,如果家族在地方自治單位中的影響力不能及時消散,農民個體及其家庭仍要受制于家族,現代國家建設與地方自治單位之間的矛盾就無法化解。為了立,必須破,國家政權建設需要家族順應時代的發展進行必要的變革,這將引發村莊社區中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發生質的變遷。費先生雖然充分重視了地方的重要性,卻沒能對家族與族權性質進行深入分析,沒能對地方自治單位內部變革的必要性給予高度重視,難以真正詮釋國家政權建設與地方自治單位的辯證統一關系,致使重構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構建新的雙軌政治模式缺乏有力舉措。
五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家政權建設加快推進,逐步在鄉村社會確立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國家權力進入村莊社區,將農民從家族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編入生產隊中,以政治單位重組了農民的生活單位,通過機構下鄉實現了國家對鄉村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全面管理。1979年開放改革以來,國家改變了政權建設的推進方式,越來越重視公共規則的治理價值,推行行政科層化改革,強調通過正式的法律法規和技術治理,使群眾分享現代化的成果。③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6)。取消農業稅費以后,村黨組織和村委會的正式化和制度化傾向明顯,基層權威趨于官僚化,規則下鄉初顯成效。但是,法律法規和政策法令等正式制度可以在朝夕之間發生改變,從村莊社會文化中衍生出來的非正式制度卻不會對正式制度做出即時反應④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杭行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3頁。,正式制度通過規約村官行為壓縮了非正式制度的運作空間,卻依然難以完全替代非正式制度,多元規則相互交織、彼此作用于村莊社區,使正式規則的統一性、權威性受到損傷,基層治理中的糾紛難以得到及時化解,原本能夠在村莊內部得到有效解決的矛盾向上轉移,無理上訪、牟利信訪等現象時有發生⑤陳柏峰:《農民上訪的分類治理研究》,《政治學研究》,2012(1)。,加重了農村基層行政的負荷,降低了基層行政的效率。
為此,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探索創建新型農村社會治理模式,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鄉村社會的現代化。在這些創新模式中,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將村民自治的范圍從行政村下移到自然村或村民小組,賦予自治主體更大的自主空間。這樣的創新實踐并非全新的事物,而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其模式創新充分體現了“雙軌政治”的現代內涵,說明在新中國成立60多年后的農村,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成功,政府開始越來越多地推行惠及民生的社會政策,中央與地方自治單位之間的利益共識日益增加,這些促使“雙軌政治”在新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中顯示出積極的現代治理價值。
第一,費先生認為,提高行政效率重在地方,“真心要改革社會,只有從民間的自治機構入手”。①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9頁。其中的地方,按照前文所述,即為自然村莊,并且村莊的背后是家族。因此,“雙軌政治”的現代內涵之一,即是要重視村莊,順應形勢發展新型民間自治機構,并為之配置適當的資源,使之享有合法的自治權限,激活社會組織的活力。農村改革以來,隨著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離鄉進城,家族發展失去后繼力量,家族與農民的血緣關系逐漸被國家與公民的社會契約關系取代,家族對農民生產生活的影響能力日漸式微。②王朔柏、陳意新:《從血緣群到公民化:共和國時代安徽農村宗族變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4(1)。隨著合村并組、撤銷村民小組長等鄉村體制改革的推進,自然村莊重新獲得了自治的空間。這就為以自然村為單位重建地方推行社區自治、發展新型社區社會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2004年,江西省贛州市政府推行鄉村體制改革,在行政村與村民小組之間設立以自然村莊為單位的新社區,鼓勵農民自建社區理事會,由大家共同推選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成為理事會成員,由社區理事會負責籌措資金組織開展包括道路修建、空心房拆除、改水改廁等新農村建設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社區理事會成為當地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載體。通過改造和利用傳統資源,提高了農村基層行政的效率,促進了當地農村社區的良性發展。雖然目前從全國范圍看,以自然村為單位,以社會組織為中介的社區自治模式尚未普及,但隨著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允許“在有實際需要的地方開展以村民小組或自然村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等相關文件和配套政策的實施,這種模式會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發展民間自治機構,不僅要培育不同類型的社區社會組織,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還要創新基層民主實踐機制,以費先生所說的同意權力為核心構建社區權力結構,并積極發揮村規民約的現代治理價值,賦予社會組織適當的自治權限。同意權力建立的基礎是社會契約,源自村民的共同授權。社會分工與社會分化越復雜,同意權力的重要性越凸顯。③④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50頁;第157頁。當前中國社會中的村莊正在加速轉型,農民的個體化進程也在不斷加快,這就要求社會組織的發展須建立在同意權力的基礎上,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匯聚民意,整合分散的家庭力量,以配置社區自治需要的各種資源。
第二,費先生提出,“如果能把附著在紳士這個名詞上的惡感和成見除去,我想地方上的領袖人才在恢復政治雙軌中實是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的。”④結合前文所述,雙軌政治的現代內涵之二是重視地方領袖人才的培育。紳士成為地方領袖,一是由于他們是鄉村培育出來的,對鄉土有著親密的感情;二是因為他們受過教育,接受了儒家意識形態,是學者或知識分子。這些使得他們愿意回歸鄉土,通過向同族同村的人們提供庇護,贏得民眾認可,成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等多元鄉土資源的共同載體,以此獲取影響民眾態度和行為的能力,成為真正的社會權威。受教育使得他們習得了儒家倫理,成為皇權在地方自治單位中的代理人,從而使皇權倡導的意識形態與地方自治的基本理念相融合,并使他們掌握了地方自治規則的意義闡釋權,成為地方上“公家”的管理者。近些年來,退休官員、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在外創業的企業家等出身鄉村的一批能人開始越來越多的回歸鄉土,參與社區發展與農村建設。他們比普通村民更熟悉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理解并認同國家的治理理念和民主原則,具備成為不同類型社會組織領辦者的素質和能力。隨著他們扎根鄉土,并在服務社區發展中贏得民眾信任進而成為社會權威,如此就能發揮類似紳士的中介功能,使國家治理理念融入村莊自治規范,化為村規民約或章程制度之有機構成要素。一旦他們成為地方領袖,就能夠實現治理主體、治理規則與組織依托的有機統一,為重建地方找回依靠力量,使村落社區逐漸形成落葉歸根的社會有機循環系統。①返鄉能人類似于費先生所說的“紳士”,他們從鄉村走出去,獲得成功后,又走回鄉村。他們是中國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和留守村莊的能人一起推動著中國農村的發展。但是,能人并不等同于權威,尤其是經濟能人并不能天然地成為鄉村治理的主導力量。其中的關鍵,是要推動返鄉能人融入村莊,利用自身的資源稟賦逐漸成為村莊里的公共權威,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返鄉能人和村莊里成長起來的農民精英能夠成為社區社會組織的主導力量,能夠洞悉、領會和踐行國家治理理念,能夠維護村民的共同利益,在政府和自然村之間扮演好新時代的“準紳士”角色,就能重建有機的鄉土秩序。這在轉型期的中國鄉村依然非常重要。
第三,雙軌政治的現代內涵之三是重建“協調關鍵”,在國家與社會組織間構建一個權力與權利相互制衡、協調共處的關鍵地帶,暢通農民合法權益的制度化表達渠道,重構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在江西省贛州市等地,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為村莊社區自治提供了組織依托,重建了雙軌政治中的乙橛。相比作為甲橛的政府權力,農村社會組織的治理權限尚小,社區自治的空間有待拓展。綜上,國家一方面可以通過意識形態建設,加強對地方領袖人才的思想引領,將社會組織的發展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范疇中,另一方面可以適時退出一些行政效率不高的領域,讓渡必要的自治空間給社會組織,保障社區自治權利的穩定增長。為此,在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需要重建“協調關鍵”,建立國家權力與村莊社區自治權利此消彼長、相互制衡、和諧共處的協調地帶,促使社會組織的治理權力能夠在現行法律許可的框架內,以政府授權或默認的方式不斷增長,增強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和權限。同時,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利于將分散的個體農民及其家庭匯聚、整合成一個整體,為重建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創設條件。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能夠幫助個體農民及其家庭化解日常糾紛、生產難題,又能匯集民意,形成意見和建議,降低個體直面國家反饋意見的概率,避免信息反饋渠道的淤塞。而政府若能夠建立制度化的渠道收集社會組織反饋的民意,并以正式的方式及時回應,就能實現信息的暢通。
從中可以發現,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應堅持以下原則:自治單位的選擇應根據具體情況,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自治主體的發展應重視傳統資源的現代價值,培育社區社會組織;自治權力的來源應是以村民共同參與、民主協商為基礎,以現行法律法規為依據,制訂實施的村規民約和章程制度;自治人才的遴選應注重從返鄉人才中選取,能夠將現代國家治理理念融入社區治理實踐的地方領袖;自治組織的成長應重視與地方政府溝通協商,探索構建雙方協同治理的合作機制等。同時,在創新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的過程中,國家應避免政府行政權對社會自治權的非必要干涉,盡可能地保護社區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的平等協商權,促進不同類型農村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由此,中國政府就可以真正地從甲橛與乙橛上下分層、雙向信息渠道并行不悖兩個角度,重建雙軌政治,以此提高農村基層行政效率,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Abstract: Double-track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FeiXiao-to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gid system of grass-root administration. This concept not only covers the implication of governance dicision about county and village, but also includs goverment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sure feedbac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understanding dimension of double-track politics in FeiXiao-tong’s sociology thought system. This concept contributes to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era. It contai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anc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thinking of a ideal social and political model. Mr.Fe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units, but he did not make a deap analysis of clan and family nature,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to explain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 units.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state power construction and the modernity infiltration, the natur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has changed radically,the mode of village democratic autonomy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been growing vigorousl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has been reconstructed. These make it possible for doubletrack politics to present positive modern governance value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s:Double-track Politics;Grass-root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 and Society;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Local Self-government Units
(責任編輯:黃家亮)
T eoretic Contribution, Interpretation Limit, and Modern Connotation of Double-track Politics
Zhao Xiao-feng
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農村社會組織發展與‘和諧陜西’建設協同創新機制構建研究”(2015G002)、陜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青年英才支持計劃資助項目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軟科學研究項目“農村社區建設與基層治理體制創新研究”(2016RKX10)。
趙曉峰,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副院長,陜西省鄉村治理與社會建設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楊凌,71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