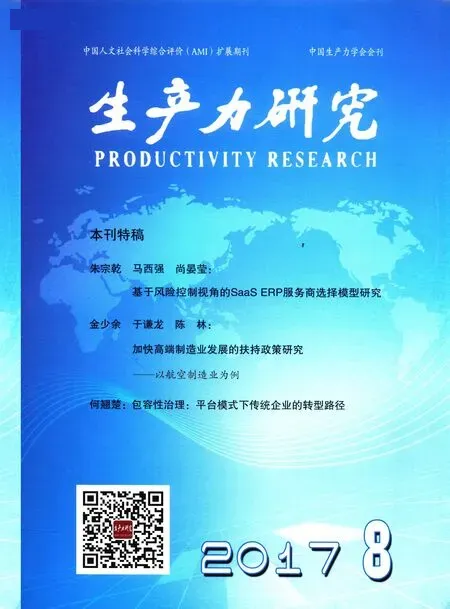包容性治理:平臺模式下傳統企業的轉型路徑
何翹楚
(中國人民大學 勞動人事學院,北京 100872)
包容性治理:平臺模式下傳統企業的轉型路徑
何翹楚
(中國人民大學 勞動人事學院,北京 100872)
當下,平臺模式正重塑著我國經濟格局,以互聯網和高科技為代表的新經濟在憑借平臺模式獲得發展先機后,正在向傳統產業跨界發展。使得傳統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為此,傳統企業應進行平臺化轉型。包容性治理契合平臺模式的特性,有利于規避轉型風險。它通過對科層組織的全面解構,形成一種平面化、直線型、網格狀的新型組織結構。進而致力于營造多邊互補、可持續的大平臺生態圈。并且,打破人事制度的樊籬,激勵內部員工創新,吸引市場和用戶參與。同時,強調協同創新和品牌責任,為無邊界的組織塑造有凝聚力的核心價值。由此,實現平臺效應最大化。
平臺模式;小微公司;包容性治理
2002年,Gawer A.和 Cusumano M.A.在《平臺領導者》(Platform leadership)一書中提出“平臺”(Platform)[1]概念,開啟了市場經濟學的平臺理論研究。2004年,由法國產業經濟研究所(IDEI)和政策研究中心(CEFR)共同舉辦的學術會議專門研討了“雙邊市場平臺”(Two-Sided Market Platforms)這一主題。認為,平臺是買賣雙方進行交易的場所或機制。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平臺的經濟學意義已不僅限于市場交易的媒介,而日益成為一種先進的運營模式。當下,平臺模式正在重塑我國經濟格局,以互聯網和高科技為代表的新經濟在憑借平臺模式獲得發展先機后,正在謀求向傳統產業的跨界發展。傳統產業主導的經濟格局正在被顛覆,使得傳統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主動接納平臺模式,分享平臺模式的集群效應和遞增收益,是傳統企業的理性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海爾、聯想等傳統大型企業開始實行平臺化改造,由此必將經歷轉型陣痛期。規避轉型風險,要求企業治理方式的變革,而包容性治理為其提供了可行性路徑。
包容性治理是“包容性增長”從發展經濟學領域向現代管理學領域延伸的新概念。2007年8月9日,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在其舉辦的題為“Key Indicators 2007”研討會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概念,使得包容性問題成為發展經濟學的時代課題。Ifzal Ali提出,包容性增長主張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及合理的利益分配。認為,可持續增長應建立在廣泛的社會基礎之上,能夠包容大部分社會成員及弱勢群體[2]。傳統企業平臺化改造同樣面臨包容性問題。包容性治理將企業治理與包容性增長的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結合起來,以包容性作為治理的價值取向,倡導建立一種各種利益相關者平等參與、共享資源和收益的治理模式。其精髓是多元合作、機會公平、收益共享,這與平臺模式的特質高度契合,為企業的平臺化變革開拓了路徑。
一、構建包容性的組織結構
在現代企業制度下,清晰的職級、職能、職責劃分創造的高效組織,使得一些關鍵環節的科層組織具有保留的必要。因而企業的組織變革盡管以扁平化為方向,但限于效益最大化目標,扁平化的實質僅是有限減少治理層級,而并未能徹底打破科層架構。與此不同,包容性組織結構是在傳統企業平臺化轉型中,通過對科層組織的全面解構,逐漸形成的平面化、直線型、網格狀的新型組織機構。它對內突破了企業固有的科層邊界,對外與大市場平臺溝通起來,打通了企業的上下通道和周邊通道,這就將企業上下、內外的人才、資源全方位包容進來,面向一切市場機會,實現與互聯網平臺的高度融合。
具體而言,包容性組織結構是由“小前端+大平臺+智慧型總部”構成的自組織系統。“小前端”是眾多的小微公司,它們位于組織最前端,與用戶和市場直接相連;“大平臺”是各職能平臺,位于小微公司之后,處于組織中端;“智慧型總部”位于組織末端。在前端←中端←末端方向上,所有組織后端皆為其前端提供服務,最終指向用戶和市場。
(一)解構中間經理層,建立小微公司
在與互聯網融合之前,企業大多采用的是金字塔型組織結構。董事會、監事會位于金字塔之側,掌握企業的領導權與監督權,制定企業戰略,監督管理層。高層經理人位于金字塔頂端,掌握整個企業的經營決策權,負責企業戰略的執行。而金字塔中部,則是中層經理人。
首先,解構中間經理層。企業按照職能部門明確分工,各中層經理人對本部門負責,也對上級負責,這就使得科層組織層級清晰,邊界明確,有效保證了標準化生產的效率。可見,中層職業經理人是科層組織管理的中間力量。然而,在平臺運營模式下,這一中間經理層日益低效和僵化,難以應對網絡市場的瞬息變化,成為一線團隊與總部之間溝通的障礙。企業平臺化變革就是要解構中間經理層。
其次,組建小微公司。就是要打破職能部門壁壘,將企業目標向內市場化,即向所有員工開放。在全公司進行公開征選,讓員工組建小微公司進行項目開發和目標實現。小微公司是一種全流程、自驅動、自優化的自主經營體。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具有自主的人事權。小微公司由員工自由組合,可以從二三人到十幾人不等,組織規模精煉,具有高度協同性;不設職位層級,只有作為專業技術權威的團隊負責人,由成員共同推舉;而且,根據項目完成情況自主擴員或解散,以便更好地匹配市場需求和創新需求。這樣,成員按單聚合,團隊負責人按單變換,企業變成項目團隊“組建-運行-解散-重組”的整合平臺。
二是具有自主的經營權。原先屬于中高層經理人的決策權下放到小微公司,它根據市場變化自主進行產品設計、生產,組織營銷活動,對產品質量負責,這種決策自主權大大提高了決策效率。
三是具有自主的財務權。小微公司責、權、利對等,利益分配與其利潤直接掛鉤。在企業總部與小微公司之間,根據企業內部分利機制進行獨立核算,小微公司自負盈虧,超利分成。在小微公司內部,成員的薪酬標準按照其各自的價值貢獻率進行彈性分配,多勞多得。
小微公司是包容性組織結構的最小單元,其兼具靈活性和高度自主性的組織特性,是企業包容性治理的組織保證。
(二)解構職能部門,搭建服務型功能平臺
功能平臺是平臺化企業的基礎架構,是專注于為前端小微公司提供服務的后臺。它是傳統職能部門平臺化的結果。
首先,傳統職能部門的平臺化轉型。職能部門平臺化,就是依托互聯網,企業通過將各項傳統職能部分或全部、向內或向外市場化,實現去中介化的轉型過程。企業的研發與設計部門,可以通過向內市場化的方式,征選有能力的員工組建小微公司進行創新或創業,分解職能任務;同時,再通過向外市場化的方式,在線上與用戶和市場對接,搭建用戶信息與社交平臺,形成包容內部員工、外部用戶、市場不確定人群等各方主體共同參與的研發與設計平臺。進而,通過入駐B2B垂直細分平臺,將企業的采購、生產制造、銷售等環節與上下游企業連接起來,聚集行業內資源,相應地形成原材料交易平臺、生產制造平臺、分銷平臺等系列平臺,由此將線下的產業價值鏈升級為線上的功能平臺。
其次,建立指向小微公司的平臺服務系統。這些功能平臺依自身職能為小微公司提供不同服務,滿足小微公司對原材料、生產、倉儲、物流等方面的需求,保證小微公司的順利運營。同時,也促進小微之間的協作,讓他們擁有更強的創新能力。而且,前端小微將客戶需求反推給后臺團隊,帶動起各個功能模塊的快速互動和高效運轉,從而激活全企業的創新活動。
最后,形成互動聯合的大平臺。功能平臺打破了企業職能部門間的壁壘,溝通了各業務板塊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溝通了行業內外的資源。它連接每一個小微公司,將指令鏈條轉型為基于網絡的自主反應鏈條,形成一個功能多樣、兼容互通的聯動系統。未來,在大數據、云計算和工業4.0的驅動下,功能平臺不斷升級,將提升成為功能更為強大的云平臺。
(三)更新頂層設計,建立智慧型總部
企業平臺化轉型過程中,原本處于金字塔頂端的高層管理角色虛化;而獲得自主經營權的眾多小微公司在獨立運營后,必將面臨總體規劃、制度安排、虛體與實體的統籌協調等治理空白領域,因而智慧型總部應運而生。智慧型總部是平臺化企業的總后臺,是在企業所有者主導下、通過競聘重組而成的智囊團隊。它秉持包容性治理理念,輸出企業價值,為平臺化運營提供資源與服務,與員工保持平等的伙伴關系。
首先,掌握戰略方向。在組織運營中,總部只負責把握公司發展的大方向,而不再干預企業治理的具體事務。總部依托前端的創新小微,積累數據、沉淀知識,進而將其匯聚為智慧型總部的智力資源,作為其調整戰略決策的依據。
其次,制定指導性規則。在平臺組織中,智慧型總部處于末端,是前端小微公司和中端功能平臺的總后方。其功能定位是服務,解決前端創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在以契約承諾、伙伴聯盟組成小微公司的過程中,負責剩余散、小、差、弱員工的妥善安置,實現減員增效;在職能部門市場化重組過程中,在外部人才吸納、項目招標各環節中建立科學評判規則,保證全面分解企業目標的小微公司的市場競爭力,避免弱弱聯合。
最后,建立共享型分配機制。總部本身的角色在于提供技術、資源、資金、品牌優勢及孵化期的避風港,進行風險評估和風險投資。總部定期對所有小前端按銷售額、毛利率等相關財務指標進行考核,據此引入外部風險資本,對效益好的團隊進行資金傾斜。在風險投資到位之后,鼓勵創業員工參與小微公司的投資,享有小微公司的部分股權。這既是對創業員工實行的股權激勵,也是公司與員工風險共擔的一種方式。員工跟投之后,再次引入的風險資本投資,可分享總部設置的期權。小微跟投、期權對賭機制使每個員工成為企業的股東,形成有效引力。
二、營造包容性的大平臺生態圈
傳統企業治理以企業自身效益為中心,重在競爭。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成為其經營成功的可靠保證。這就使企業處于競爭性的市場生態中。而包容性治理則重在聯合,變競爭對手為合作伙伴。它致力于營造多邊互補的平臺生態圈,形成一種資源開放、互利共贏、良好有序的平臺環境。大平臺、富生態、共治理能更好地實現優勢互補,使企業獲得可持續的發展后勁。
(一)依托高效的智能互聯機制搭建大平臺
平臺化企業的發展與壯大,取決于其所依托的平臺規模與平臺環境,因而擴大企業平臺就成為其發展的前提條件。擴大企業平臺,就是在企業實現平臺化轉型后,依托高效的智能互聯機制突破企業邊界、向更大的產業平臺延展的擴容過程。由此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大平臺系統。
首先,高效的智能互聯機制,為產業互聯創造了條件。網絡時代,互聯技術不斷進化,從初期的PC桌面互聯、移動互聯,發展到萬物萬能互聯,將所有生產要素、市場要素和社會要素關聯起來,由此推動著消費互聯、工業互聯向產業互聯發展的進程。隨著產業互聯程度不斷提高,系統的互聯互通及基于其上的社會協作創造更大增殖空間,使平臺潛能發揮到最大。
其次,擴大企業平臺,就是要接入更大的產業互聯平臺。即以本企業的核心、優勢項目為基礎,搭建水平擴展平臺。將企業的相對競爭優勢對等為平臺價值,與行業內外企業交換資源,實現產產結合,優勢相長,發展范圍經濟。平臺化企業與產業互聯平臺對接后,能夠聯合更多的企業,匯聚更多的共享資源,由此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大平臺生態圈。Vargo和 Lusch認為,平臺生態圈實際上是一個服務生態系統(service ecosystem),遵循以服務為導向的邏輯(service dominant logic)。大平臺生態圈的形成,有利于維持資源的可持續交換,使系統中的成員處于合作互利的良性互動中,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平臺化企業還可在產業平臺的基礎上,探索入駐金融平臺,實現產融結合之路,借助資本力量,撬動更大的市場。
(二)依托完善的市場機制創造富生態
Rochet&Tirole從價格結構的角度提出“雙邊市場”[3]的概念。“互聯網+”時代,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雙邊或多邊市場,它連接雙邊或多邊平臺化企業,為它們提供交易平臺,使各平臺化企業的邊際收益遞增。這一收益源自于市場機制激發的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使平臺化企業接入后交易規模持續擴大,不斷吸引更多平臺化企業的接入,因而促使平臺化企業的接入數量與平臺用戶規模同增共長。可見,完善的市場機制是為平臺化企業創造豐富平臺生態的關鍵因素。
互聯網平臺的市場機制包含價格總水平、價格結構、網絡外部性等一系列平臺杠桿。向買賣雙方收取交易費用是維持市場平滑運行的前提,平臺可以通過提高或降低定價來吸引用戶。Rochet&Tirole研究發現,平臺在向買賣雙方收取的價格總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調整價格結構(即對雙邊用戶的不對稱定價)來吸引用戶[4]。
在價格杠桿的基礎上,Amstrong提出了交叉網絡外部性(Cross-group Externalities)問題。他認為,通過平臺實現互動的兩組用戶,其中一組用戶數量的增加會引起另一組用戶獲得的網絡外部性收益的增加[5]。如果發生持續影響的用戶在平臺的同一邊,即為同邊網絡效應;反之,則是跨邊網絡效應。Rysman研究了雙邊市場的跨邊網絡效應,認為,一邊用戶可以利用網絡型平臺與另一邊用戶實現互動并且從中獲得收益,是雙邊市場存在的必要前提[6]。Rochet&Tirole研究發現,用戶接入平臺帶來的外部性存在差異,用戶對平臺的需求彈性也不同。對此平臺應采用逐個擊破的定價策略。對外部性較強、需求彈性較大的用戶,應通過降低其交易費用的方式培養其接入的興趣;反之,則提高交易費用。以增加用戶規模,實現平臺整體利潤的最大化[7]。平臺通過調整價格結構和評估網絡外部性促使多邊平臺化企業相互吸引、接入平臺,使各方共同從規模經濟中獲益。同時,也帶來平臺自身規模與價值的增加,形成更加豐富的平臺生態環境。
三、推行包容性的人才策略
傳統治理模式下,企業的人才開發往往集中于經理人和技術精英群體,人才激勵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普通員工和企業外用戶。“互聯網+”時代,企業本身即是平臺,它一端連接員工,另一端連接用戶、資源和市場。企業成功的關鍵在于讓員工與市場對接、用戶與企業對接后而產生的持續創新優勢。由此,員工和用戶就成為影響平臺化企業發展的核心人才,他們的創新力成為企業競爭力的增長點。因而,平臺化企業的包容性治理,就是要打破狹隘的人才觀念,包容員工和用戶兩大群體,為全員創新、多元共治提供人才支持。
(一)面向金字塔底層的人才賦能策略
企業平臺化后,將原本處于金字塔底層的員工被推到平臺化企業的最前端,賦予了全新職責,即發現市場潛在需求,進行項目研發與設計。這就使一線員工從執行者轉變為創新者,成為具有創造價值的人才資源。面向一線員工的人才開發,應重點抓好三個方面。
首先,權力下放。平臺化企業的員工有相當一部分是以85后、90后乃至00后為主力的“網生代”,當其創新沖動無法在公司中實現時,在自我效能感的驅動下,他們可能選擇獨立創業。為此,企業應轉變管控型思維定式,通過組建小微公司及創新團隊,向員工下放決策權,以主人翁角色留住人才。
其次,能力培養。西奧多·W·舒爾茨研究了人力資本的形成方式與途徑,并對教育投資的收益率以及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做了定量研究[8]。企業應通過培訓、“干中學”[9]等方式,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開發員工創新能力;通過資金、技術投資對員工創新活動進行孵化,使其實現自我驅動,培養創客型員工。
最后,薪酬激勵。傳統治理模式下,平衡企業剩余價值在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分配比例,一直是企業制定薪酬制度的根本原則。而包容性治理則承認員工對企業剩余價值的分享權,實行公司與員工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分配機制,激發員工的創新動能。由此,平臺化企業實現了員工創客化、人人專家化,成為創新服務基地。
(二)面向用戶群體的用戶至上策略
數字經濟學認為,在互聯網上,注意力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企業與互聯網融合后,其用戶群數以億計,注意力成為維持用戶規模、促成企業邊際成本驟減的關鍵因素。然而,傳統治理模式把產品與服務質量作為維系用戶忠誠度的關鍵因素,故而將用戶置于企業生產之外,處于“研發-生產-銷售-使用”價值鏈的末端,忽視了注意力的資本價值。包容性治理則肯定用戶注意力對維系用戶忠誠度的直接作用,將用戶納入企業生產過程之中,推行用戶至上策略。
首先,滿足用戶的個性化偏好。互聯網條件下,用戶需求高度個性化、動態化,平臺化企業應借助平臺與用戶進行同步溝通,分析用戶的曾經偏好與當前偏好,研判未來偏好。進而包容用戶偏好,將用戶置于企業價值鏈的前端,作為企業資源配置的導向,變大規模生產為大規模定制,才能有效提升產品與服務對目標用戶的粘性。
其次,將企業的部分功能向外市場化。企業在平臺化轉型過程中,可以將研發、設計等功能單元直接向市場開放,以互聯網為平臺連接用戶與設計、市場與生產,讓用戶直接參與創新,并且重視用戶體驗和產品的閉環設計。通過與用戶的全程交互持續引爆創新活動,這既降低了研發成本,又關照了用戶需求;同時還突破了內部創意的局限,保持了創新活力。
最后,實行平臺會員制。企業可以憑借平臺的分享與服務優勢,利用會員制引導用戶消費。精心設計用戶入口,規劃線下的門店體系,引導線上的社區體系,吸引用戶加入。并且,可以利用虛擬貨幣促進用戶消費,將用戶消費需求鎖定于平臺化企業的產品,在提高銷量、增加平臺化企業利潤的同時,通過虛擬貨幣報銷抵現的形式對會員進行利益再分配,使用戶得到返利。這種是平臺、企業、會員三方共同受益的分配制度,有效地維系用戶規模,推動平臺化企業的發展。
人才的創新力是平臺化企業的發展的根本驅動力,無邊界的平臺化企業需要無邊界的人才。未來平臺化企業的發展,在開發企業內員工和用戶群體的基礎上,還應進一步打破傳統人事制度的樊籬,變雇傭關系為契約關系,打破用人邊界。一方面,實時監測行業人才動態,建設人才數據庫;另一方面,經營人才社區,形成與跨行業人才的持續互動,吸引外部人力資源加入組織。從而擴大創業、創新、創利隊伍,以人才的成長促進企業的發展。
四、塑造包容性的組織文化
平臺化組織的無邊界發展,其基本方式之一就是吸引全社會的優質資源、人才不斷加入。然而,組織的邊界越模糊,越是需要核心價值的引領,這就要求塑造富有凝聚力的組織文化。
(一)以協同創新為組織的核心價值
互聯網時代,平臺化企業成長的驅動力是基于大平臺協作基礎上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Hausman從企業層面上對研究投入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二者存在很強的相關性[10]。Hausman強調了創新投入的重要性。然而,在新技術背景下,對于平臺化企業的發展而言,提升創新等級,可能比加大創新投入更為關鍵。而協同創新正是推動創新升級的有效途徑。
Ansoff于1965年提出協同的概念,初期的協同是指兩個組織在資源共享的基礎上相互依存、同生共長的關系[11]。協同創新是由多元創新主體互動合作、產生系統疊加效用的一種創新方式。而在平臺化企業中,協同創新面臨著挑戰。這是因為,企業平臺化激活了其組織結構,但也導致了創新單位的小型化,使得平臺化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變成了基于商業利益連接起來的松散聯盟。而組織松散則可能導致創新供給不足,創新思維不活躍,難以實現創新植入增長。這就需要組織文化的凝聚力。樹立協同創新理念,將組織創新目標與個人愿景充分融合,有助于促進創業團隊內部、創業團隊之間的合作,培育創新主體的組織認同。同時,也有助于打破自我積累、小團體研發的狹隘模式,構建知識互補、集思廣益、暢所欲言的協同創新機制,進行高強度的智力激勵,形成更大的頭腦風暴(Brainstorming),實現高于創新個體平均水平的創新效益。
(二)以品牌責任為組織的核心價值
平臺化轉型使企業面臨品牌挑戰。一方面是公司的微型化、小型化在客觀上淡化了品牌意識。平臺化企業充分放權,員工被賦予全面的自主權,實現了其市場價值的最大化。但同時,由于大集團管控的退位,員工的集體觀念被長期擱置,進而導致公共責任感下降。另一方面,互聯網大平臺的海量用戶為小微公司創造了無限的試錯機會。對于用戶的投訴,它可能不作出及時回應,也可能將返回的問題產品重新出售給另一個用戶。交易平臺不斷出現的問題產品、服務差評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企業平臺化之后面臨的品牌危機。
由于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和快捷性,品牌對平臺化企業的重要性甚至要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品牌是平臺化企業的無形資本,能夠創造不可計量的無形收益。而小微公司任何拒絕承擔質量責任與服務責任的行為,都可能對品牌價值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正如Kiran和Sharma所言,企業也應承擔社會責任。“隨著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引入,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概念正逐漸受到關注。企業不僅僅是為賺取利潤,更重要的是與員工和社會分享利潤。”[12]平臺化企業與小微企業在業務運營中,是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在利益分配中,是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而在品牌維護上,則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同體關系。因而,只有將品牌責任升華為組織的核心價值,才能使小微公司嚴格自律,才能為用戶提供長期的服務和質量承諾。
包容性治理與平臺模式具有天然的聯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平臺模式的優勢。而在實踐層面上,平臺化企業的成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企業需要應對轉型各個階段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為此而對平臺化戰略進行層層推演,從而推進企業有次序的、系統的組織變革。隨著平臺化企業匯聚的資源越來越多,釋放的能量越來越大,它的功能就越來越強,進而向更高層次演進。未來,平臺化企業不斷優化升級,其治理路徑也必將更為開放、包容。
[1]Gawer A.,Cusumano M A.Platform leadership[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2:15.
[2]Ifzal Ali.Inequality and the Imperative for Inclusive Growth in Asia[J].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7,24(2):1-16.
[3]ROCHET,J C,TIROLE J.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Journal of European conomic Association,2003(1):990-1029.
[4]Rochet,J.C,Tirole.J.Two-sided markets:an overview[R].Working paper,Mimeo,IDEI,Universite de Toulouse,2004:1-44.
[5]Armstrong,Mark.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7(3):668-691.
[6]M.Rysman.The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9,23(3):125-143.
[7]Rochet J C,Tirole J.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markets[J].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1):990-1029.
[8]西奧多·W·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6-81.
[9]Arrow Kenneth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155-173.
[10]J.A.Hausman,B.H.Hall,Z.Griliches.Econometric Models for Count Data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ents R and D Relationship[J].Econometrica,1984,52(4):909-938.
[11]Ansoff H.C.orporate strategy.Revised edition[M].New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7:35-83.
[12]Kiran R,Sharma A.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Corporate Strategy for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2011,4(1):10-17.
(責任編輯:D 校對:L)
F271
A
1004-2768(2017)08-0012-05
2017-06-08
河北省科技計劃項目“基于技術進步理論的我省健康產業科技創新對策研究”(16456229)
何翹楚,女(滿族),河北秦皇島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研究方向: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