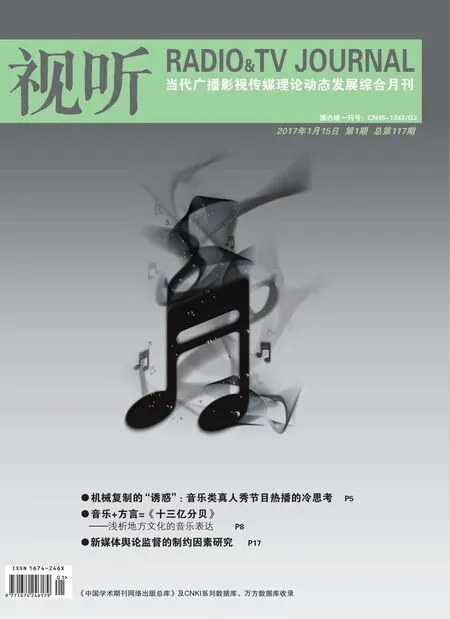試析《紀實72小時》對國內平民化電視紀錄片的啟示
□田靜
試析《紀實72小時》對國內平民化電視紀錄片的啟示
□田靜
平民化電視紀錄片自90年代以來在國內一直受到歡迎,但隨著這類紀錄片的升溫,“流水賬”“片段組合”等流弊也日漸凸顯。本文以日本NHK的《紀實72小時》為研究對象,從拍攝創意、敘事技巧、人情味三個方面入手,試分析《紀實72小時》對傳統平民化紀錄片的突破,以期對國內平民化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一些借鑒與啟示。
《紀實72小時》;平民化;拍攝創意;敘事技巧;人情味
所謂“平民化”,其實質是在節目素材的遴選上以老百姓的視角和審美趣味出發,記錄生活、貼近生活、貼近百姓、拍攝老百姓關注的題材。①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平民化”理念指導下創作出了一批經典紀錄片作品,如《沙與海》《毛毛告狀》《最后的山神》《舌尖上的中國》等。但隨著創作實踐的深入,一部分創作者對于“平民化”理念在認識與操作上出現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主要表現在將“平民化”等同于簡單地模仿和再現生活。具體到紀錄片創作中,表現為對原生態材料不加篩選地使用,如簡單粗暴地運用大量長鏡頭、同期聲、跟蹤采訪,忽視創作過程中表現手法與編導意識的引領,使得成片蒼白空洞、缺乏深度,最終呈現為一些簡單的、雜亂的、放任的片段組合。
紀實主義強調尊重生活的原始形態,強調紀錄片保持一種符合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的逼真性,這就決定了普通人及其生活成為紀錄片的主要角色。②那么,如何更好地操作這類題材以展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態,甚至更深一步刻畫世俗生活背后所隱藏的深刻真實,挖掘世俗生活背后蘊含的普遍人性?《紀實72小時》或許可以為以上問題提供一些思考。該片拍攝于2006年,是日本NHK綜合頻道推出的人文紀實類紀錄片,共23集,每集針對一個地點或人群進行連續72小時的跟拍,然后將拍攝素材剪輯成時長30分鐘的紀錄片。自其播出以來廣受好評,無論是其創意、敘事技巧,還是其呈現出的人情味都值得仔細研究。
一、新穎的拍攝創意
紀錄片要紀錄真實生活,而生活的一大特點就是其散漫性與平淡性。但紀錄片一定存在著敘事與節奏的要求,這就要求拍攝者們要在散漫而平淡的生活中找出其固有的戲劇性與矛盾沖突,這也是為什么國內很多紀錄片一跟就是幾個月、一兩年(當然不是連續拍攝)的原因。《紀實72小時》卻反其道而行,只對某地某人群進行連續72小時的跟拍,72小時之后不管結果如何都必須停止拍攝。這樣,散漫的物理時間與緊張的拍攝時間形成角力,成為吸引觀眾的一大看點。
二、完善的敘事技巧
《紀實72小時》的表現手法可說純粹原生態呈現,無搬演、扮演,無情景再現,也無后期特效,只通過采訪和跟拍來編輯、架構片子,但又沒有傳統紀實類紀錄片那種重點不明、敘事平淡和節奏紊亂的弊病,這主要歸功于它在選題、攝影、節奏方面的匠心獨運。
(一)選題
要在72小時的時間里拍攝到足量的可用素材絕非易事,這需要創作者謹慎地選擇創作題材。《紀實72小時》往往會選擇城市中一個不起眼卻有意思的地點作為拍攝駐扎地,比如24小時營業的理發店、大型舊貨店、大排檔街、專供外籍人士購物的超市等等,蹲守72小時,用鏡頭記錄來往人群,并用采訪、跟拍的方式挖掘普通人背后的故事及他們的內心情感。這些地點人流量大,而來到同一場所的大抵是同一類人,這就使得主題突出,避免了泛泛而談。通過對這一人群不同個體的記錄,又避免了單一,做到有輕有重,內容翔實。
(二)攝影
《紀實72小時》全部采用手持拍攝。這部片子每一集都是人物眾多,如《福岡·人情排檔街》,拍攝對象是大排檔街上的攤主們和客人,重要人物就達20多位,人數龐雜、密集且處于不斷運動中。手持拍攝使攝影機擺脫了三腳架的束縛,解放了拍攝角度、拍攝距離、構圖、運動方向等,使得創作者可以靈活地呈現畫面。創作者還大量運用近景、特寫鏡頭,使被訪者的表情在鏡頭前被細致地呈現,無論是喜是怒是哀是樂,都非常有感染力。
同時,手持攝影獨有的特點——輕微晃動,也帶給觀眾一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而“輕微晃動”則很貼近“記錄生活”的理念。
(三)節奏
馬塞爾·馬爾丹曾說:“所謂影片的節奏,并不是指各個鏡頭放映時間的比例,而是指每個鏡頭的延續時間適應于該鏡頭所能引起并使觀眾感到滿意的那種注意力的緊張程度。”《紀實72小時》很好地把握了這一點,如在《上野阿美橫·漫話吃茶》一集中,茶館店主切茶點的干脆利落與茶葉花朵般在熱水中展開的徐緩形成節奏的變化,觀眾觀影時的心理也由緊張變為喜悅,這就是節奏的拿捏。而外部結構上的節奏則巧妙地通過計時器的呈現來實現,如不時插進類似電子時鐘的字幕,將已經過去的時間展現出來。
三、人情味
除了這些,真正使這部片子擁有魅力的是它所傳達出來的濃厚的人情味。
《紀實72小時》始終將目光對準平凡的普通人,他們是為圣誕節購買蛋糕而忙碌的超市老板,是在福岡排檔街擺了一輩子小吃攤的老夫婦,是在舊貨店淘寶的年輕人,是工作到凌晨來買宵夜的工薪一族……創作者們難能可貴地用平視的視角來記錄每個擁有獨特生命體驗的個體,用“他們的”語言去跟受訪者交流,在《東京·高速巴士車站》中,面對一個凌晨才下班來買夜宵的受訪者,創作者這樣開始他們之間的交流:“每天都這個點下班嗎?”“你老婆的工作沒這么辛苦吧?”語氣親切,充滿關懷,這是來自于創作者們發自內心的對于受訪者的尊重、親近與關心。
該片將對個體的關注又聚焦在心理層面,雖然影片有很多外部生活場景的攝入,但重點在于通過對人物的采訪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通過創作人員不斷的提問,受訪者最終多少都吐露了一些真實的感觸。如《化妝間》這一集中,名叫由美的辦公室女郎下班后來化妝間補妝,通過采訪者與她的交流,我們得知她竟然每天下班后都會來補妝,然后美美地回家。為什么下班了還要來補妝呢?家里有誰呢?由美一開始并不愿意多說,記者繼續與她交談、追問,我們終于知道她家里并沒有別人,她自己一個人在東京租著一個小房間,她補妝再回家是想自己能一直保持一個好心情。“一個人在家會不會比工作時多出很多情緒?負面的。”記者繼續追問,由美說:“是的,一個人的時候我情緒會低落,因為……所以我回去前來這里補個妝,就是想提醒自己要保持樂觀的心態,開開心心的。”這樣就將一個單身女青年漂泊在都市的孤獨、彷徨與樂觀、堅強完整地展現在了觀眾面前。
四、結語
如貝拉·阿拉茲在《電影美學》中所說:“紀錄片必須在經驗世界的廣闊天地中發掘最有特征意義的、最有趣的、最可塑造和最有表現力的東西。”從《紀實72小時》取得的成功可以看出,要突破電視紀錄片平民化表達的瓶頸需要創作者們革新拍攝創意,一定要有新的東西出現,才能吸引受眾的眼球。同時,要在敘事技巧上下功夫。平民化不等于普通化,不等于流水賬,要尋找合適的題材,根據題材調整攝像方式,同時把握好影片的節奏。最后,應該體現人文關懷,只有這樣,才能使電視紀錄片有更好的藝術表現力。
注釋:
①趙金龍.關于電視紀錄片平民化的思考[J].新聞傳播,2014(01):52.
②溫立紅.平民化紀錄片的價值與缺失[J].大眾文藝, 2010(07):58.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