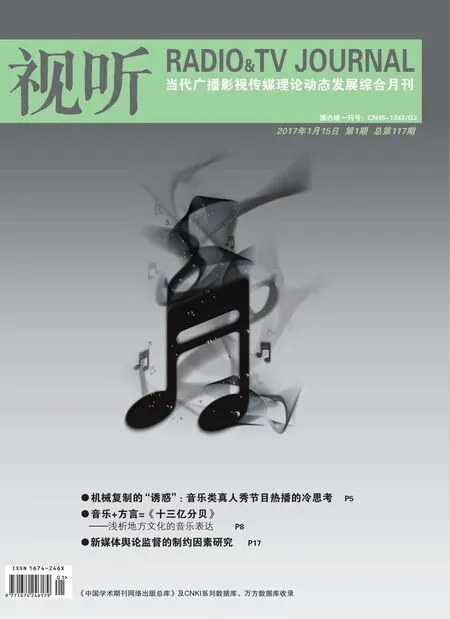新媒體視閾下的農(nóng)民交往方式研究
——以阜陽(yáng)市阜南縣柴集鎮(zhèn)為例
□丁家佳 詹婷 任曉利
新媒體視閾下的農(nóng)民交往方式研究
——以阜陽(yáng)市阜南縣柴集鎮(zhèn)為例
□丁家佳 詹婷 任曉利
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社交空間狹窄、單一,“熟人”關(guān)系主導(dǎo)著人際關(guān)系,這種局面因新媒體在農(nóng)村地區(qū)的普及而發(fā)生著變化。本文旨在研究農(nóng)村地區(qū)對(duì)大眾傳播的使用現(xiàn)狀,同時(shí)將視角置于新媒體之下,將眼光投入廣袤的農(nóng)村大地,研究新媒體對(duì)農(nóng)村地區(qū)的影響。筆者在調(diào)查走訪安徽省阜南縣柴集鎮(zhèn)之后發(fā)現(xiàn),不同于傳統(tǒng)的農(nóng)村,新的社交形態(tài)在農(nóng)民的社交過(guò)程中呈現(xiàn)出來(lái),具體表現(xiàn)為意見(jiàn)領(lǐng)袖的身份更為多元、“熟人”社會(huì)關(guān)系被打破、新的社交空間逐步建立等特點(diǎn)。
農(nóng)民交往;新媒體;社會(huì)關(guān)系
隨著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新媒體成為大眾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技術(shù)進(jìn)一步拓展了人類的交往范圍,所謂的“遠(yuǎn)親不如近鄰”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發(fā)生了變化,時(shí)空不再是人們信息交往的阻礙,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大眾可以在更廣闊的時(shí)空完成人際交往和信息交換。由于數(shù)字鴻溝的影響,部分大眾占有獲得信息的先機(jī),他們率先掌握了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設(shè)備的能力,從而拓展了信息獲取和人際交往的渠道。技術(shù)賦權(quán)不僅僅惠及城市,作為媒介接觸滯后區(qū)的農(nóng)村地區(qū)也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浪潮中發(fā)生著變化,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人際交往方式的變化。
在廣大的農(nóng)村地區(qū),新媒體惠及大眾,同時(shí)也對(duì)農(nóng)民提出了更高的媒介接觸要求,在原有的知識(shí)鴻溝基礎(chǔ)上又增添了新的數(shù)字鴻溝。農(nóng)村地區(qū)的傳統(tǒng)人際交往方式多為面對(duì)面的人際傳播或是借助傳統(tǒng)的固定電話和移動(dòng)電話溝通,信息溝通的范圍較窄。然而,在新媒體普及的今天,農(nóng)民的交往方式發(fā)生了潛移默化的改變,從單一的人際傳播向多種方式傳播轉(zhuǎn)變;從較窄的信息傳播區(qū)域向千山萬(wàn)里以外延伸;傳統(tǒng)的人際交往模式和交往對(duì)象也隨之而變。新媒體普及以及人際交往方式的嬗變,使農(nóng)民的生活方式較之以往發(fā)生了轉(zhuǎn)變,而農(nóng)民自身也在交往方式中完成對(duì)自身的認(rèn)知構(gòu)建。
一、研究背景
據(jù)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中心發(fā)布的第38次《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路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jì)報(bào)告》顯示,截至2016年6月,農(nóng)村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為31.7%,農(nóng)村網(wǎng)民達(dá)2.25億。雖然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不及城市地區(qū),但是農(nóng)村地區(qū)已擁有數(shù)量龐大的互聯(lián)網(wǎng)用戶。作為擁有龐大農(nóng)村人口的安徽省阜陽(yáng)市,全市常住人口為771.6萬(wàn),城鎮(zhèn)人口比例僅為36.2%,外出務(wù)工半年以上的人口比例為36.97%。“留守”“外出”“返鄉(xiāng)”,這三類人群成為阜陽(yáng)農(nóng)村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網(wǎng)絡(luò)和手機(jī)等新媒體散落在這三類人群中。“變”成為農(nóng)民交往方式轉(zhuǎn)變的主題,信息傳播者、信息傳播渠道、信息接收者、信息量、信息的表達(dá)方式等都在發(fā)生變化,作為重要因素的農(nóng)民自身在這種變化之中的交往模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觀念也處在深層次的變化中。農(nóng)村地區(qū)的變化對(duì)于社會(huì)形態(tài)的重塑、社會(huì)文化的構(gòu)建、社會(huì)關(guān)系等的建造都產(chǎn)生著重要的影響。
二、調(diào)查現(xiàn)狀
(一)調(diào)查對(duì)象——安徽省阜南縣柴集鎮(zhèn)
安徽省阜陽(yáng)市地處于安徽省西北部,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城市,富余農(nóng)村勞動(dòng)力約200多萬(wàn),為全國(guó)勞動(dòng)力輸出重要基地。作為阜南縣中心鎮(zhèn)之一的柴集輻射后湖村、羅莊、孫崗村、賈茶棚村等多個(gè)村莊,交通較為便利,擁有龐大的網(wǎng)絡(luò)受眾。
本研究選取了柴集鎮(zhèn)所轄的孫崗村、后湖村、羅莊三個(gè)人口較多的村莊作為主要調(diào)查地點(diǎn)。
(二)調(diào)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質(zhì)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結(jié)合的方法對(duì)調(diào)查對(duì)象進(jìn)行研究。具體方式為走訪、深度訪談、觀察采集信息。本次調(diào)查主要是對(duì)于孫崗村、后湖村、羅莊三個(gè)村莊進(jìn)行走訪,在村莊負(fù)責(zé)人的帶領(lǐng)下,走訪村莊的主要街道,并選取有代表性的人群進(jìn)行訪問(wèn)調(diào)查。
(三)調(diào)查結(jié)果
1.柴集鎮(zhèn)孫崗村
孫崗村的戶籍人口有4482人,1113戶,其中外出務(wù)工人數(shù)約占70%,剩余常住人口大多是老年人和留守兒童,老年人約占60%。全村接通網(wǎng)絡(luò)的住戶僅有幾十戶,村委員會(huì)以及少數(shù)農(nóng)戶家中接通網(wǎng)絡(luò),農(nóng)民通過(guò)電腦接觸網(wǎng)絡(luò)的渠道比較少,擁有操作計(jì)算機(jī)技能的農(nóng)民數(shù)量不多,多數(shù)是村干部(因工作需要)以及年輕人。由于月租貴、不便攜帶等原因,農(nóng)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基本不通過(guò)固話,多通過(guò)手機(jī)進(jìn)行信息傳達(dá)。在當(dāng)?shù)兀謾C(jī)的普及率相當(dāng)高,很多農(nóng)民均掌握了智能手機(jī)的使用,通過(guò)智能手機(jī)上網(wǎng)為農(nóng)民接觸網(wǎng)絡(luò)提供了一個(gè)更為便捷易得的渠道。
通過(guò)對(duì)村委會(huì)主任的訪問(wèn)得知,他和部分朋友、同事都有朋友圈和QQ,但主要是瀏覽信息,很少通過(guò)這些社交軟件聊天,村中多數(shù)是年輕人(30歲以下)玩微信。值得注意的是,他會(huì)通過(guò)微信來(lái)了解子女的生活近況,但不會(huì)與子女進(jìn)行交流,原因是因?yàn)楦舸涣?xí)慣使用微信與子女進(jìn)行溝通。
一名張姓青年受訪者接受了我們的訪問(wèn),筆者通過(guò)他了解到村中20歲—30歲的青年接觸網(wǎng)絡(luò)的頻率比較多,他們使用聊天軟件進(jìn)行交流的頻度較少,多是瀏覽并獲取信息,接觸網(wǎng)絡(luò)主要是為滿足娛樂(lè)和獲取信息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他們對(duì)微信使用的次數(shù)不多,但是他們已經(jīng)通過(guò)這些聊天軟件建立了朋友圈。當(dāng)沒(méi)有手機(jī)的時(shí)候他們僅通過(guò)電腦進(jìn)行網(wǎng)絡(luò)交流,手機(jī)上網(wǎng)功能給了他們更多的選擇和可能。
2.柴集鎮(zhèn)羅莊
羅莊大部分青壯年村民都外出務(wù)工,留守的大多是兒童和老人,電腦的普及率很高,多是由外出務(wù)工或讀書的子女?dāng)y帶,家中都未聯(lián)網(wǎng),在家中常住的村民基本不使用電腦也未掌握計(jì)算機(jī)的使用技能。在與老人和兒童的對(duì)話中發(fā)現(xiàn),他們基本上都未接觸過(guò)網(wǎng)絡(luò),很多老人甚至不了解、也沒(méi)有接觸網(wǎng)絡(luò)的意愿。與此不同的是,很多稍微年輕的村民知道網(wǎng)絡(luò),并了解微信、微博的使用方式,有些年輕村民頻繁使用微信。在對(duì)某些村民的走訪中,筆者了解到他們有微信群,經(jīng)常使用微信與遠(yuǎn)距離的親朋好友交流。這些村民認(rèn)為雖然面對(duì)面的交流少了,但是微信以及網(wǎng)絡(luò)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在閑暇時(shí)會(huì)他們也會(huì)使用手機(jī)的上網(wǎng)功能瀏覽新聞、玩游戲以及聊天軟件;有些村民接觸微信已有兩年之久,認(rèn)為掌握新媒體使用功能并不難,基本是自學(xué)掌握各種手機(jī)軟件的使用。
3.柴集鎮(zhèn)后湖村
調(diào)查了解到后湖家庭農(nóng)場(chǎng)有限公司是當(dāng)?shù)鼐哂械湫托缘谋就疗髽I(yè),因此,將此處選為本次調(diào)查的對(duì)象之一。經(jīng)過(guò)訪談了解到后湖農(nóng)場(chǎng)具體經(jīng)營(yíng)水蜜桃生產(chǎn)和銷售,現(xiàn)有基層工人34名,其中女性居多,約占75%,年齡大多40歲左右。農(nóng)場(chǎng)共配備4臺(tái)聯(lián)網(wǎng)計(jì)算機(jī),辦公人員約六七名,都已掌握計(jì)算機(jī)技術(shù),但是都未經(jīng)過(guò)系統(tǒng)培訓(xùn),高層辦公人員之間有微信群,主要用于業(yè)務(wù)交流。
另外,在對(duì)農(nóng)場(chǎng)負(fù)責(zé)人的個(gè)人訪問(wèn)中了解到她與父親交流主要通過(guò)微信,部分取代了以往的電話溝通,在業(yè)務(wù)交流中也大量使用微信等聊天軟件。此外,她與遠(yuǎn)方的好友親朋的溝通主要通過(guò)微信。她本人獲取信息的渠道主要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娛樂(lè)活動(dòng)中接觸網(wǎng)絡(luò)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如玩游戲、觀看視頻、網(wǎng)購(gòu)、瀏覽新聞等。上網(wǎng)已經(jīng)成為她的一種生活方式,通過(guò)她我們了解到農(nóng)場(chǎng)員工基本不接觸網(wǎng)絡(luò),她們的業(yè)余生活比較單調(diào),主要是觀看電視。值得注意的是,農(nóng)場(chǎng)負(fù)責(zé)人有多次替員工網(wǎng)購(gòu)的經(jīng)歷,她表示員工們都很認(rèn)可網(wǎng)購(gòu),認(rèn)為網(wǎng)購(gòu)方便、便宜、物品精美。
三、調(diào)查結(jié)果分析
(一)農(nóng)村農(nóng)民交往方式特點(diǎn)
通過(guò)對(duì)柴集鎮(zhèn)各個(gè)村莊的調(diào)查結(jié)果進(jìn)行分析之后,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農(nóng)民交往方式呈現(xiàn)出以下特點(diǎn):
1.交往方式多樣性
較之以往單一的交往方式,柴集鎮(zhèn)農(nóng)民的交往方式得到了豐富,人們不再拘泥于面對(duì)面的人際交往,借助于新媒體平臺(tái),農(nóng)民主要通過(guò)QQ和微信建立新的交流圈,通過(guò)這些渠道,村民們進(jìn)行信息交流。但由于身份的差別,利用媒介平臺(tái)進(jìn)行的信息交流具有特殊性,如村干部建立的信息圈主要是進(jìn)行業(yè)務(wù)交流、政策宣傳等,而普通農(nóng)民多是進(jìn)行社交和娛樂(l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農(nóng)民群體的特殊性,新媒體平臺(tái)對(duì)于農(nóng)業(yè)發(fā)展也起到了推動(dòng)的作用,農(nóng)民群體利用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交流農(nóng)業(yè)技術(shù)。雖然交往的信息內(nèi)容有別,但是新媒體已然為農(nóng)民提供了更多的人際交往渠道。
2.交往范圍擴(kuò)大化
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超越時(shí)空的信息交往方式得以實(shí)現(xiàn),農(nóng)民通過(guò)微信等方式與遠(yuǎn)在千里之外的家人維系著親情,千里外的親朋好友們?cè)诟鞣N符號(hào)的流動(dòng)中不斷拓寬著交往的邊界。隨著智能手機(jī)以及移動(dòng)互聯(lián)設(shè)備的普及,農(nóng)民接觸網(wǎng)絡(luò)的基礎(chǔ)設(shè)施得到了保證,中國(guó)移動(dòng)、電信、聯(lián)通等運(yùn)營(yíng)商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的大力推廣也給農(nóng)民們接觸網(wǎng)絡(luò)提供了可能。在調(diào)查走訪中得知,農(nóng)民們使用的手機(jī)基本具有上網(wǎng)功能,且話費(fèi)套餐中多帶有免費(fèi)的網(wǎng)絡(luò)流量,由于網(wǎng)絡(luò)接觸渠道多、接觸成本低等優(yōu)勢(shì),新媒體成為農(nóng)民交往面對(duì)面人際交往之外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時(shí),脫離了時(shí)空的限制,信息流通的范圍也在迅速延伸。
3.交往符號(hào)豐富化
傳統(tǒng)的交流符號(hào)多是文字和語(yǔ)音,單一的符號(hào)承載著信息。不同于平日里的簡(jiǎn)短電話溝通,新媒體交往支持更多的交流符號(hào),交流變得更加簡(jiǎn)單豐富,圖像、文字、語(yǔ)音、視屏,各種信息載體單一或是復(fù)合地傳遞著信息,農(nóng)民的交往變得更為多元。
4.交往群體年輕化
信息鴻溝的藩籬在信息時(shí)代更甚,舊的知識(shí)鴻溝還未填滿,新的信息鴻溝又產(chǎn)生。農(nóng)村地區(qū)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不完善,教育水平較為落后,這些使得新媒體的使用對(duì)于年齡較大的農(nóng)民群體更為困難,青壯年群體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的熟悉程度更高,新媒體使用頻度更高,這導(dǎo)致了農(nóng)村地區(qū)的新媒體使用群體年輕化。這些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技術(shù)賦權(quán)的受益者用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臺(tái)進(jìn)行交往,建立著新的交流圈。
(二)農(nóng)村農(nóng)民交往分析
1.意見(jiàn)領(lǐng)袖的存在和變化
1940年,傳播學(xué)者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id))及其同事為調(diào)查大眾媒介對(duì)政治生活的影響,對(duì)美國(guó)伊利斯的選民進(jìn)行了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選民受到更多的是身邊人的影響,而非大眾傳媒。在《人民的選擇》一書中,拉扎斯菲爾德等人將這群影響他人的人群稱為“意見(jiàn)領(lǐng)袖”,并將其定義為:“代表著社會(huì)中活躍的那部分人,他們?cè)噲D影響社區(qū)中的另一部分人。”①這些人身份地位多元,存在于社交群體的各個(gè)位置,他們通過(guò)大眾媒介掌握信息,信息從媒介流向意見(jiàn)領(lǐng)袖,再?gòu)囊庖?jiàn)領(lǐng)袖流向不太活躍的人群。
在農(nóng)村地區(qū),受到地緣和信息交流手段的局限,人際交往多為面對(duì)面的交流,關(guān)系圈固定,在這些交往圈子中,意見(jiàn)領(lǐng)袖的地位也較為固定,這些人多由鄉(xiāng)村行政人員擔(dān)任。如在走訪的孫崗村,以村書記為中心即建立了一個(gè)關(guān)系網(wǎng),村書記接受信息并且將其傳達(dá)給其他村民,這種上傳下達(dá)的過(guò)程中村書記成為了該圈子的意見(jiàn)領(lǐng)袖。在新媒體于農(nóng)村地區(qū)的應(yīng)用過(guò)程中,除了傳統(tǒng)的人際關(guān)系和意見(jiàn)領(lǐng)袖依然存在,也誕生了一些新的意見(jiàn)領(lǐng)袖,他們的誕生與網(wǎng)絡(luò)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系。
如后湖村的家庭農(nóng)場(chǎng)中有34名基層員工,他們有多次要單位負(fù)責(zé)人為其網(wǎng)絡(luò)代購(gòu)的要求,該單位負(fù)責(zé)人就是網(wǎng)購(gòu)關(guān)系網(wǎng)的意見(jiàn)領(lǐng)袖。在柴集鎮(zhèn)的部分物流集散地,物流網(wǎng)點(diǎn)的負(fù)責(zé)人不僅負(fù)責(zé)快件代理收發(fā),還提供代購(gòu)的服務(wù)。除此以外,部分年輕農(nóng)民在建立的微信朋友圈中,也存在著新的活躍分子。總而言之,這些新誕生的意見(jiàn)領(lǐng)袖呈現(xiàn)著這樣的特點(diǎn),年齡較輕、新事物接受度高、媒介接觸能力高、受教育程度高,在媒介的篩選下,意見(jiàn)領(lǐng)袖的地位和身份在發(fā)生著變化。
2.強(qiáng)弱關(guān)系的對(duì)立
費(fèi)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guó)》中寫到:“鄉(xiāng)土社會(huì)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huì)。常態(tài)的生活是終老是鄉(xiāng)。假如在一個(gè)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guān)系也就發(fā)生了一種特色,每個(gè)孩子都是在人家眼里看著長(zhǎng)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就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gè)‘熟悉’的社會(huì),沒(méi)有陌生人的社會(huì),在這個(gè)社會(huì)中,血緣關(guān)系強(qiáng)于契約關(guān)系,人們重視輩份、地位、身份而不是法律上的平等關(guān)系。”②
在鄉(xiāng)村社會(huì),強(qiáng)關(guān)系依然是主導(dǎo)關(guān)系,格蘭諾維特(MGramovetter)從關(guān)系強(qiáng)度程度劃分,“將‘關(guān)系’劃分為強(qiáng)關(guān)系和弱關(guān)系,是從相識(shí)時(shí)間的長(zhǎng)短、互動(dòng)頻率、親密程度、互惠支持四個(gè)維度加以劃分的。”③傳統(tǒng)的人際網(wǎng)絡(luò)由強(qiáng)關(guān)系支配,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密切,交往圈子小,在新媒介沒(méi)有介入之前,人們的信息交流依靠口耳相傳,關(guān)系網(wǎng)固定且密切。然而在交流方式多樣化之后,一些“陌生人”加入到人際圈子中,千里之外的朋友也成為“熟人”,潛入傳統(tǒng)的人際圈,網(wǎng)絡(luò)為人際圈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依靠網(wǎng)絡(luò)新的朋友圈子在被建立,新的意見(jiàn)領(lǐng)袖產(chǎn)生。網(wǎng)絡(luò)帶來(lái)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改變了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格局,不像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網(wǎng),這種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虛擬、脆弱、充滿著變化。傳統(tǒng)的強(qiáng)關(guān)系網(wǎng)和新媒體帶來(lái)的弱關(guān)系社交網(wǎng)形成了對(duì)立,這種對(duì)立同時(shí)推動(dòng)、重塑著社交關(guān)系網(wǎng)。
3.新的社交空間的建立
新媒體的介入改變著農(nóng)村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農(nóng)民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也順勢(shì)而變,發(fā)生著潛移默化的改變,雖然農(nóng)村地區(qū)網(wǎng)絡(luò)普及率低,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不完善,但是新的媒介平臺(tái)為農(nóng)村地區(qū)新的社會(huì)交往空間的建立提供了契機(jī)。
與以往的社交形態(tài)不同,農(nóng)民的人際圈子變得更為復(fù)雜,以單一個(gè)體為中心,發(fā)散出多個(gè)社交關(guān)系線,人際關(guān)系的圈子和節(jié)點(diǎn)復(fù)雜,充滿了變數(shù),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也加入到了交往圈子之中,“人情”社會(huì)、“熟人”關(guān)系不再絕對(duì)主導(dǎo)著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農(nóng)民交往的新社交空間逐步建立。而且這種改變會(huì)隨著新媒介技術(shù)的普及會(huì)逐步明顯和擴(kuò)大。新媒體改變的不僅僅是社交,也改變著著社會(huì)生活、文化、經(jīng)濟(jì)、教育等多個(gè)方面。
四、結(jié)語(yǔ)
媒介服務(wù)于大眾社會(huì),同時(shí)媒介也在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融入整體的大眾社會(huì)環(huán)境,改變并重塑社會(huì)形態(tài)。農(nóng)村地區(qū)作為媒介接觸落后地區(qū),知識(shí)鴻溝和信息鴻溝阻礙著農(nóng)民對(duì)于新技術(shù)、新事物的習(xí)得,但這不代表農(nóng)村地區(qū)對(duì)于新技術(shù)帶來(lái)的改變毫無(wú)感知。技術(shù)賦權(quán)同樣惠及農(nóng)村地區(qū),但是由于群體的特殊性和地區(qū)的特別性,媒介帶來(lái)的改變呈現(xiàn)出較多特性。新媒體下的農(nóng)村地區(qū)正在發(fā)生著改變,媒介推動(dòng)著新的農(nóng)民社交形態(tài)的構(gòu)建。
注釋:
①(美)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森,高德特等.人民的選擇[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2:43-44.
②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guó)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6-9.
③朱逸.關(guān)系嵌入: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中的消費(fèi)行為芻議[J].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5(1).
本研究受到安徽大學(xué)輿情與區(qū)域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資助。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