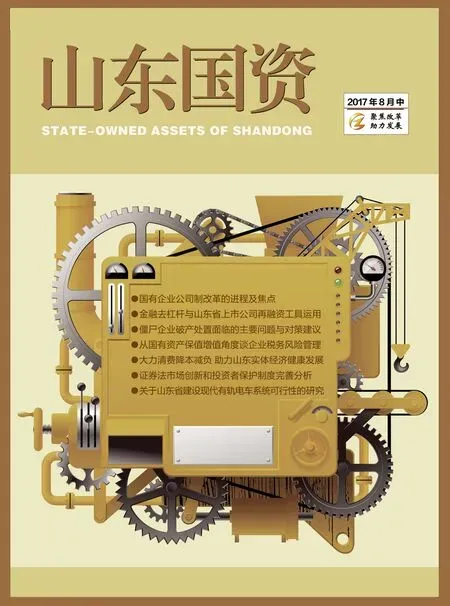論我國合同法中違約金過高的調整
李付慧
論我國合同法中違約金過高的調整
李付慧
《合同法》確立了過高違約金的調整制度,但在相關實體操作問題上仍存在較大爭議。對過高的懲罰性和賠償性違約金之調整,應區(qū)別對待,判定賠償性違約金過高應以實際損失為基準,懲罰性賠償金還應考量當事人惡意程度;對違約金的具體調整除應考量實際損失外,還包括合同履行狀況、主觀過錯程度、替代交易難度、違約金條款情況等因素,充分發(fā)揮自由裁量權,確定具體調整幅度,避免30%標準適用之僵化。
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賠償性違約金;實際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 114 條、2009年最高法在《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法釋二)在一定程度上為過高違約金的調整提供了方向路徑,但在具體操作規(guī)范上,如不同性質的違約金調整差異、30%標準之適用、具體調整幅度及影響因素等實體法問題,學界和實務界有著不盡一致的認識和理解。本文立足于這些問題的實際解決,從實體法方面對當前過高違約金調整規(guī)則作一梳理和分析。
一、違約金性質之厘清
違約金可分為懲罰性違約金與賠償性違約金,按照其功能,懲罰性違約金指合同或法律規(guī)定一方當事人違約時應支付的作為懲罰的金額,賠償性違約金指雙方預先估計的賠償損失總額。按照支付違約金之后的法律效果區(qū)別,賠償性違約金中,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不需繼續(xù)履行也不需進行損害賠償;懲罰性違約金中,支付違約金之后仍需繼續(xù)履行或進行損害賠償。我國《合同法》并未對違約金性質作出具體規(guī)定,但由于不同性質的違約金其功能以及支付后的法律效果不同,因而對其進行調整的依據是有區(qū)別的,不應籠統適用目前的調整規(guī)則,有必要明確兩個問題:一是《合同法》所規(guī)定的違約金之性質究竟為何?二是對兩種性質的違約金進行調整的具體規(guī)則是否有差別?
《合同法》所指的違約金性質,學者們主要有兩種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賠償性違約金為《合同法》中違約金性質,這主要基于《合同法》第114條規(guī)定的違約金確定標準與違約情況、損失賠償額間的必然關系得出的,同時違約金偏頗以實際損失作為參考以及增加后排斥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規(guī)定也印證了違約金的損害賠償性質。另一部分學者基于訂立合同意思自治原則之法理,認為如無法律之禁止,當事人可自由約定違約金性質,違約金兼具賠償性和懲罰性,如對過高違約金的調整程序依申請啟動,過高違約金的調整也不會完全地將違約金調整到與實際損失相一致,而是劃定了實際損失30%這樣一個標準,可見法律對于違約金過高之調整未否認懲罰性之性質,而是在認可前提下進行一定的限制。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的違約金性質兼具賠償性和懲罰性更趨合理,但應注意的是懲罰性是有限的,當事人不可任意約定其數額。
對于第二個問題,筆者認為,兩種性質的違約金應基于其功能和法律效果的不同進行差別化的類型調整。下文論述中將涉及二者調整規(guī)則的區(qū)別。
二、衡量違約金過高之標準
(一)違約金過高的基礎參照標準
1.存在實際損失下的基礎標準
法釋二將衡量違約金偏頗的基礎參照標準明確為“實際損失”,兼顧預期利益等因素,雖然較之《合同法》“造成的損失”作了進一步細化,但其僅將預期利益視為一個參考因素有待商榷。因此,有必要對“實際損失”作進一步明確,對法官來說尤為緊迫。
筆者認為,可得利益損失應包含在實際損失之中,理由有以下三點。首先,依據《合同法》第113條,違約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通過體系解釋,判斷違約金偏頗標準中的“實際損失”標準也應包含可得利益損失。當然,對于可得利益損失賠償,應當符合可預見性等可得利益損失規(guī)則的限制。其次,可得利益損失具有一定客觀性,基于《合同法》完全賠償原則,應對可得利益損失進行賠償,這是等價有償原則的應有之義。雖然可得利益損失具有不確定性,但是只要守約方能夠證明其存在及因果關系,就應當承認可得利益損失的客觀存在性。最后,賠償性違約金功能在于補足損失,懲罰性違約金在于懲戒,如排除可得利益損失,難以達到補損及懲戒之目的。
需指出的一點是,關于懲罰性違約金過高的判斷標準應否包括實際損失基準這一問題有不同認識。筆者認為,以實際損失作為基礎標準更有助于保障守約方從合同中獲得利益的狀態(tài),因為即便是懲罰性違約金的功能在于懲罰性,但當事人當初訂立合同的目的是為了履行合同獲得利益,而非為了懲罰違約方締結合同,“懲戒性”僅僅是給雙方施加完全履行合同的壓力。另外,采用以實際損失為基準的判斷標準,也方便法院在認定違約金是否過分高時的相關技術性操作。但是,考慮到懲罰性違約金功能及法律效果的特殊性,其基礎標準中應加入當事人主觀過錯程度,主要是違約方違約惡意的考量,所以,法官在判斷懲罰性違約金是否過高時,可以根據y=kx(k>o)正比例函數進行處理,其中,x表示違約一方惡意程度,y表示約定的違約金與實際損失之間的數額差。在這一函數關系下,如果x越大,則y為法律所容許的數額差就越大,反之越小。過錯因素在懲罰性與賠償性違約金調整中的影響能力上,將在下文調整過高違約金的考量因素中進行論述。
2.其他情形下的基礎標準
將“實際損失”作為判斷違約金過高的基礎標準,有時難以做出準確判斷甚至難以適用,如違約后并沒有發(fā)生實際損失的糾紛案件中,就沒有依據判斷違約金的高低問題。所以筆者認為,應明確不存在實際損失案件中,綜合考量合同標的額與合同履行程度,避免因標準單一無法衡量違約金偏頗的情況出現。
(二)“超過實際損失30%”標準之適用
法釋二規(guī)定認定違約金過高的比例標準為超過實際損失30%,但筆者認為,《合同法》沒有界定什么是“過分高”,那么法官對于相關比例的判斷具有自由裁量權,司法解釋應起著導向作用,而非強制性規(guī)定。因此,法院不應機械地把超過損失30%的數額一律認定為“過分高于”,而是應結合案件具體情況,在司法解釋指導下,對比例判斷進行自由裁量,避免出現判決結果的僵化。
三、違約金過高的調整規(guī)則
(一)調整過高違約金的考量因素
法釋二第29條確立了對違約金調整堅持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參考其他因素的標準。以實際損失為調整標準的規(guī)定,在賠償性違約金中的適用問題不大,而在懲罰性違約金中,對當事人過錯程度或違約惡意考察尤為重要。由此,違約金的調整規(guī)則應當因違約金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在賠償性違約金中,以實際損失為基準;而懲罰性違約金應采取過錯主義的調整原則。
對于實際損失前文已述,這里主要對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進行梳理。
1.合同履行情況
違約情形下的合同履行狀況包括部分履行和完全不履行。在合同部分履行的情形下,應分情況處理:如果合同處于履行不能的情況,法院應對違約金數額進行調減;如果合同能夠繼續(xù)履行,應當征求雙方意見,若當事人繼續(xù)履行的合意強烈則應駁回調整違約金的申請,判決繼續(xù)履行,如果當事人對于繼續(xù)履行合同沒有明確合意,當事人有權自由選擇繼續(xù)履行、支付違約金、請求損害賠償等任意一種方式,法院根據當事人訴求作出裁判。在合同完全不履行的情況下,如果非違約方已經提起支付違約金的訴求,違約方認為違約金過高的主張成立,法院應依程序調整違約金。
2.當事人過錯程度
《合同法》中的違約責任,原則上為嚴格責任原則,但法釋二將過錯作為過高違約金調整的參考因素,對此,筆者認為還是應按照性質對違約金調整進行不同的處理:過錯不妨礙賠償性違約金的過高認定,但會對懲罰性違約金過高認定產生影響,這在上文中已經進行了論述;此外,由于違約方主觀程度即惡意或過失決定著違約金懲罰性和補償性功能的此消彼長,因此在違約金過高的事實得到認定后,不同的過錯形式在兩種性質的違約金數額調整中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在賠償性違約金中,過錯一般不能成為調整違約金的影響因素,但在確定違約金過高的事實后,在以下兩種情形下,應當將當事人過錯程度作為調整違約金的影響因子,在合理幅度內降低違約金:一是當事人是惡意違約的情形;二是雙方均存有過錯,在違約情況發(fā)生后,積極采取補救措施且取得較好效果的一方可以適當地減輕其違約責任。
懲罰性違約金本身對于違約方就具有懲罰功能,因而在確定違約金過高后,應當根據過錯程度,在合理幅度內適當調整違約金:如果過錯程度較高甚至是惡意違約,則違約金數額降低幅度要小,保持較高的違約金;如果過錯較小,則在一定程度內降低違約金;如果違約方僅是輕微過失,則不應對其實施過重懲罰,而是在較大幅度上降低違約金數額。
3.替代交易難易程度
替代交易難易度會影響守約方的損失情況,因此在對過高違約金進行調整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中,應當納入尋求替代交易的難易情況以及相關成本。因此,需要考量守約方在對方違約后,能否通過與他人締結合同達到相同目的,如果能夠達到最初的目的,那他重新締結合同的“額外”花費應當在調整違約金數額時予以考慮;如果再次締結合同達不到最初目的甚至難以達成新合同,那么過高違約金的降低幅度盡量控制在較小范圍,即違約金數額相對較高。當然,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及《合同法》第119條之規(guī)定,守約方負有止損行為義務,其應積極采取措施尋求替代交易,這種情形下產生的“額外”成本代價才能作為調整過高違約金的考慮因素。如果守約方怠于尋求替代性交易,放任損失擴大,那么擴大的損失金額就不能作為支付高額違約金的依據。
4.違約金條款情況
對違約金條款的考量主要是看其是否存在強迫締約、顯失公平、格式條款等情況。如果當事人有證據證明違約金條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素,除了依照顯失公平進行撤銷外,還可以通過違約金調整制度進行救濟。值得注意的是,過高違約金條款若屬于格式合同或格式條款,應當考察違約方是否是提供格式合同或條款的一方。如果違約金條款屬于霸王條款,提供格式合同或條款的一方為非違約方,那么非格式合同或條款提供方違約且認為違約金過分高的,法院應綜合其他因素對過高違約金進行調整;如果提供格式合同或條款一方自己違約,又以違約金過高為由請求司法機關調整的,就不能降低違約金。
(二)過高違約金的調整幅度
對于不同性質的違約金,均適用“30%標準”的調整幅度,可能出現不同性質的違約金無法充分發(fā)揮各自功能的后果。具體來說,假設在兩個不同案件中,第一個案件中當事人約定了賠償性違約金,第二個案件當事人約定了懲罰性違約金(假設約定超過了造成損失的50%),經過法院認定兩個不同案件中的違約金均過分高于實際損失,那么在第一個案件中,將超過部分的賠償性違約金調整到實際損失的30%,本來旨在彌補損失的違約金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懲戒性功能,超出了當事人補損之意思表示;在第二個案件懲罰性違約金中,法院將超過部分降低到實際損失的30%以下,無法體現合同締結時當事人懲戒性之合意。按照此種方式的調整幅度,均是對當事人未來預期賠償數額的偏離,違約金調整的剛性規(guī)范極大地縮減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范圍。
因此,對不同性質的違約金進行調整的幅度應當區(qū)別對待。有一種觀點如下:賠償性違約金中,應將過高違約金調整到與實際損失相同或近似水平;懲罰性違約金中,在實際損失的100%至130%之間確定調整后的數額,違約方的過錯越大,這一比例就越大,但上限為實際損失的130%。但是超出部分占實際損失的30%標準是較早時期最高法針對商品房買賣合同確定的標準,若將此標準適用于一般的買賣合同、借款合同等標的額未必這么大的合同違約金調整中,可能造成調整比例過低。因此,為了充分尊重懲罰性違約金中當事人的“懲罰性”意思,建議在懲罰性違約金調整中,法院不應受限制于法釋二確立的30%標準。在違約金調整案件中,法院應綜合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等因素行使自由裁量權。在實務中,有以“合同標的額”或者“合同未履行部分總值”作為違約金調整上限的,或具一定比照意義。
以上是筆者對過高違約金調整制度的理解與看法。對于這一制度在運行中產生的新問題,還有待于相關部門和學者對司法實踐中的經驗和教訓作進一步的梳理和總結,從而彌補違約金調整制度在運行中的空白,糾正實踐中的偏頗做法。
①梁慧星主編:《民商法叢論(第8卷)》[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②梁慧星:《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M],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③王利明:《違約責任論》[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④沈德詠 奚曉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⑤崔建遠主編:《合同法(第五版)》[M],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⑥王闖:《當前人民法院審理商事合同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J],《法律適用》,2009年第9期
⑦陳懷峰、趙江風:《違約金數額司法調整的適用問題》[J],《政法論叢》,2011年第6期
⑧李東琦:《論懲罰性違約金的調整》[J],《當代法學》,2013年第6期
⑨歐達婧:《違約金數額調整研究——基于司法判決的實證分析》[J],《沈陽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⑩蘇亞拉:《過高違約金的調整問題研究》[D],內蒙古大學,2011年
李付慧,山東師范大學法學院2015級民商法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合同法、證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