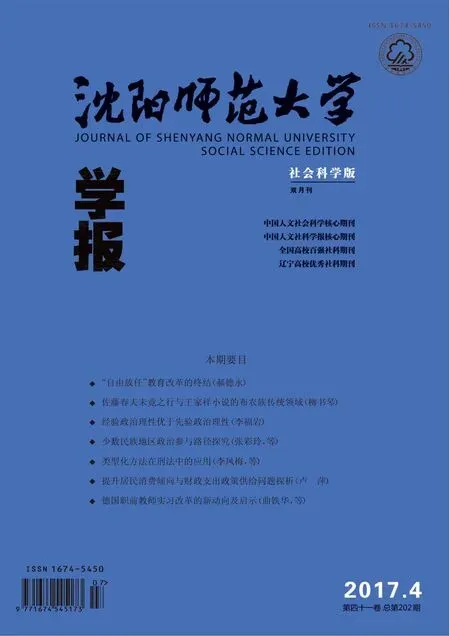經驗政治理性優于先驗政治理性
——試析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哲學批判
李福巖
(沈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哲學動態
經驗政治理性優于先驗政治理性
——試析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哲學批判
李福巖
(沈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法國大革命時期,從經驗政治理性出發的柏克猛烈攻擊大革命及其政治原則,認為經驗政治理性優于先驗政治理性,反對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等的抽象政治理論及其先驗政治設計。在批判法國革命者政治經驗缺乏及其對先驗政治理性的濫用之后,他從所謂真正理性的角度為世界樹立經驗政治理性的英國樣板。柏克審慎、妥協的保守政治理性中也含有一些現代公共理性的成分,從柏克、葛德文到羅爾斯、哈貝馬斯把理論付諸實踐之前年復一年的等待和商談中,我們可以看到由啟蒙理性運動始發,經大革命政治實踐對理性的洗禮,再到和平年代公共理性話語的運動軌跡——政治事實與政治價值的適度分離。
經驗政治理性;先驗政治理性;柏克;法國大革命;政治哲學
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即刻在海峽彼岸的英國引起了巨大反響,并與歐洲其他各國在政治、經濟與宗教等問題上逐步發生沖突。柏克(又譯伯克)從1765年至1790年一直是英國輝格黨主要的政策發言人,曾任下院議員近30年。在1790年法國大革命一周年紀念之際,柏克寫成了《法國革命論》一書,集中而猛烈地攻擊大革命及其政治原則,把大革命看成是人類罪惡的淵藪。后來,他又在《新輝格黨人向老輝格黨人的呼吁》《對法蘭西事物的思考》《關于弒君者的和約的信札》等著作中,進一步展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
這一系列批判,與以前柏克反對奴役貿易、支持北美獨立的較激進自由主義政治主張的輝格黨態度大有不同。他以英國百年妥協政治實踐為基準,以折中的政治哲學對大革命及其政治原則進行批判。因此,現代法國學者哈列維說:“代表著半經驗主義,半神秘哲學,以功利原理為基礎,伯克譴責法國大革命”[1]。但柏克也因此奠定了以拒斥抽象理性及其濫用、反對革命、堅持君主立憲與改良及貴族式的自由為主要內容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由此也引出了英國式自由觀念與法國式自由觀念的分歧,從而使他成為18世紀下半葉英國最富盛名的政治理論家,也因此成為近代西方思想界反對法國大革命保守派的首席代表。
一
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主流深信理性能帶來社會進步,要以自然權利、社會契約這些抽象的理性燭亮國家與社會等一切黑暗無知的地方,摧毀現存一切不合理性的事物。以伏爾泰、孟德斯鳩為代表的啟蒙主流歷史觀更是典型的理性支配歷史的唯心史觀。而柏克則堅持歷史傳統、習慣、道德與神等非物質的、經驗性的東西支配歷史的唯心史觀,反對抽象理性的唯心史觀。由此出發,柏克批判啟蒙運動的先驗政治理性,抨擊法國大革命為這種惡的理性濫用的結果,從而試圖建構一種保守的、神秘的經驗政治理性。
幾十年的從政經歷,柏克積累了大量的政治經驗,使他特別推崇政治經驗,認為經驗政治理性優于先驗政治理性,反對政治哲學家的抽象政治理論。古羅馬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羅曾區分了理論型政治學家與實踐型政治家,又從實踐型政治家的才能中發現了人類理性的卓越作用,認為實踐型政治家優于僅僅關注政治理論的人。柏克非常贊賞西塞羅的經驗政治理性觀念,在《法國革命論》中常引用西塞羅《國家篇》《法律篇》中的觀點、話語攻擊大革命及其先驗政治理性。
進而,柏克對法國啟蒙哲學家的先驗政治理性展開批判,并把大革命看成是一場“哲學式革命”帶來的惡果。而鼓動起大革命惡果的法國啟蒙政治哲學更是“放肆的哲學”“野蠻的哲學”“墮落而卑鄙的哲學”;那些啟蒙思想家們則是“哲學家的陰謀集團”“偽劣的形而上學的販子們”、剝奪所有權、教會產業的“哲學的掠奪者”。在柏克看來,啟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學是一種先驗的政治理性,啟蒙政治哲學這種野蠻的哲學乃是冷酷的心靈和理解混亂的產兒;啟蒙哲學家的先驗政治理性不是建立在對極其復雜的人性和社會目標的權衡思考之上,并非真正的政治理性,而是缺乏經驗的虛幻思辨的結果,“這種人對自己的人權理論是如此之感興趣,以至于他們已經全然忘記了人性。”[2]
客觀地說,啟蒙政治理性的抽象先驗人性論基礎,確實給了柏克攻擊的口實。正如施米特所說:“這些反革命派從大革命的權利意識——它是建立在自然權利的學說上——中只看到了混雜著激情與形而上學抽象觀念的判斷。”[3]但柏克對人性的解說也并不比抽象人性論高明,而是回到了它之前的神性論,他說:“人在本質上是一種宗教動物”[2]122。宗教動物這個神秘人的第一天性,借用了休謨習慣是人的第二天性的理論,并把二者混合起來而形成的所謂經驗政治理性。對此,德國現代哲學家曼海姆比較公允地評價說:“歷史保守主義幾乎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為國家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真正基礎的那些憑沖動行事的、非理性的因素。它認為這些力量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并且暗示人的理性本身沒有能力理解或控制它們。”“這一態度已由伯克在18世紀末表達出來”[4]。
相比較而言,柏克不相信政治理論家的理性,更相信政治實踐家的理性;不相信個體理性,更相信人類理性;不相信人類理性,更相信人類本性。他認為,“政策不應該由人類的理性調節,而應該由人類的本性調節;理性不過是人類本性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本稱不上是最偉大的那部分。”[5]面對復雜的人、社會、國家,柏克看到,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唯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堅信政治經驗,尤其堅信英國百年君主立憲的政治經驗,推崇實踐政治家為“行動中的哲學家”,不反對理性本身。
柏克堅決反對先驗政治理性的僭越與瀆神行為,反對抽象的政治理性設計,反對直接建筑在一種先驗政治理性上的政治。在此,他又從經驗論者休謨那里獲得了力量,因為休謨說:“一切假定人類生活方式要進行巨大變革的政府設計方案,顯然都是幻想性的。柏拉圖的《理想國》、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都屬于這種性質。”[6]
二
柏克還批判盧梭這個“形而上學家和哲學家”,認為以理性主義的公理為基礎的個人活動創造不出任何持久的東西,只能拖延、破壞和消滅事務的自然進程。柏克尖銳地批判盧梭,而且是在反對誤用理性的名義下進行的。而我們知道,盧梭卻是否定、懷疑理性能帶來社會進步的,也反對濫用人類理性。和盧梭一樣,柏克也靠內心感覺到政治國家應與宗教并存,他說:“我們在內心中感覺到宗教乃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在一開始我們必須說服我們的公民相信,神是我們的主人和萬物的尺度。”[2]120-121
柏克對盧梭最大的不滿,在于盧梭學說中的革命性主張。盧梭曾宣稱應該首先掃清地面并拋棄一切陳舊的材料,以便重新建立起一座美好的大廈,這樣才能把理想的國家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上。柏克無法容忍這種“自負而又抽象的理性政治設計”,認為正是盧梭這種摧毀與重建的政治哲學引發了法國大革命。柏克說從休謨那里“得知盧梭寫作的秘密”,要打動和吸引聽眾,“就必須創造政治上和道德上沖突的奇跡。我相信,如果盧梭還活在人世,在他某個清醒的片刻,他是會對他的學生們的實踐的狂熱感到震驚的——他們在他們的悖論中乃是奴性十足的效顰者;并且即使是在他們的毫無信心之中也會發現有一種隱然的信仰。”[2]223盧梭這樣的“醫國的醫生”,不滿足于治療病癥,而是妄圖在承擔重建國家體制中表現出做作的、非常的能力來,而實際上不具備這樣的理性和智慧,“他有很嚴重的智力障礙。”[2]115
對盧梭從理論到人身的攻擊中,可以發現柏克堅決反對先驗政治理性設計與政治實踐的結合。他認為,正是以盧梭為代表的先驗理性政治導致了大革命這個災難性的惡果;盧梭等啟蒙思想家不具備真正的治國政治智慧。這樣看來,盧梭就不是理性主義政治的設計師,而是情感主義或浪漫主義政治的設計師了。而盧梭早已聲明,他只是探討理論、權利,不是一個政治實踐家;他自己若是政治實踐家,就不會浪費時間來談《社會契約論》。可見,柏克有些邏輯矛盾地批判了盧梭。
以經驗政治理性批判先驗政治理性,柏克試圖論證英國君主立憲制的“現實合理性”,設計法國舊制度的英式改革。正如當代英國學者肯尼所說,柏克所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健全的政治判斷所需要的知識,不是純粹理性的——甚至不是以理性為主導的。”[7]雖然他對盧梭先驗政治理性設計的批判自身也存在著矛盾,但他對先驗政治理性的批判中也含有一些閃光之處。這就是,任何政治理論、原則都不應該從先驗概念出發,而應該從現實社會政治生活出發;政治理論有理論的價值,事實有事實的價值,政治理論與實踐之間應該保持適當的張力、平衡,而不是一邊倒。
進而,柏克批判了法國大革命對先驗政治理性的濫用以及革命者政治經驗的缺乏。他把法國革命者視為馬基雅維里式的政客,以先驗的理性觀念為基礎進行革命,政治經驗貧乏。他猛烈抨擊了文人、哲學家對革命的鼓噪所帶來的血腥暴力,在他看來,這些法國政治文人、陰謀家煽動起了血腥暴力的革命,只能帶來理性的暴力,只能造成理性自由與秩序全部喪失的災難性后果。大革命之前的這種“墮落而卑鄙的哲學”“在打動人們的想象時,那時候那種體系的經營者們對人的自由還懷有著敬意。在他們的騙局中沒有滲進暴力。這就被保留給我們的時代來撲滅理性的這點,可以打破這個啟蒙時代的深重黑暗的微弱的閃光。”[2]311
柏克認為,法國三級會議的代表雖然人數驚人的多,“但是在國家的任何實際經驗方面,卻找不出一個人來。最優秀的人也不過是談理論的人。”[2]53三級會議中的下等人、無知無識的代表只有一些雄辯的才能,卻沒有相應的政治智慧,不會照顧財產的穩定,不會考慮任何制度的穩定性;法國暴民們最淺薄的理智、最粗笨的雙手、暴怒與瘋狂只能完成摧毀一切的偷懶工作,不具備審慎的、深思熟慮的智慧來從事改革與重建的事業。而這種補償、調和、平衡的深沉政治智慧,絕非指導法國革命的“江湖郎中”“煉金術士”與“諷刺作家”所能相比。法國建設者們的立法基礎是幾何學,“當這些國家的總監們前來考察他們的測量工作時,他們很快就發現,在政治上的一切事物之中,最謬誤的莫過于幾何學的證明了。”“法律、風俗、習慣、政策、理性都要服從的這種形而上學的原則,卻還得使自己服從于他們的意愿。”[2]226-227柏克還說在法國國民會議已形成的大量司法規劃中,也沒有看出具有任何聰明才智的地方。
在批判了導致法國大革命的先驗政治理性、革命者政治經驗缺乏及其對先驗政治理性的濫用之后,他就要從所謂真正理性的角度為世界樹立經驗政治理性的樣板,即英國經驗政治理性的樣板。
柏克認為,真正的政治理性應充分考慮“虛飾的人性”、歷史傳統、秩序、習慣、道德、宗教等因素。而這些因素歸結到最后,只不過是在歐洲世界里,多少世代以來都一直依賴的兩項傳統原則:紳士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貴族和教士。真正的政治理性是深思熟慮的、審慎的,他說:“審慎在所有的事物中都堪稱美德,在政治領域中則是首要的美德。”[5]304他認為,建立英國那樣的自由政府需要深思熟慮和一顆睿智、堅強而兼容并包的心靈。政治的“審慎”與“深思熟慮”這兩個詞,僅在《法國革命論》中就分別被柏克強調了至少13次與12次之多,與這兩個詞匯相近的、相反的詞匯更是在其著作中隨處可見。他以此向國內政敵、向法國革命者、向世界顯示他“審慎”而“精明”的政治智慧。
柏克認為,真正的政治理性是妥協、平衡與折中。他說:“人權是一種中間的、不可能界定的東西,但并不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人在政府中的權利乃是它們的優勢所在;而這些往往是各種不同的善之間的平衡;有時候則是善與惡之間,有時候又是惡與惡之間的妥協。”[2]81這種妥協政治理性的典型是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第一部憲法,在當今美英兩國政治實踐中也頻繁再現。所以,他希望政治家應以虛飾的寬仁和理性教導人民順從、忍耐,也希望政治家具有真正的政治理性,一種高智慧的政治理性——妥協。
可見,柏克并沒有否定政治理性設計本身,最后還是要確立他自以為高智慧的政治理性。這種政治智慧要充分考慮虛飾的人性及需要,最為重要的是這種實用政治智慧需要長期、大量的政治經驗積累。他說:“政府這門科學既然其本身是如此之實際,并且是著意于如此之實用的目的,所以就是一個需要有豐富經驗的問題,甚至于比任何一個人在整個一生中所能獲得的都要更多的經驗”[2]80。他還把政治智慧、政治理性視為一種道德上的計算原則,而非形而上學、數學的計算原則。和休謨一樣,這種政治智慧帶有不可知論與神秘色彩,既認為政治可以解析為科學,也認為人類政治事務偶然事件甚多而不可確定。
三
從柏克到歐克肖特,保守主義者一貫表現在對先驗政治理性的不信任與批判上,伯里、勒龐、傅勒、福柯延續著柏克對先驗政治理性批判的思路和某些話語。在歐克肖特看來,近代理性主義是“權威的敵人,偏見的敵人,傳統、習俗和習慣的敵人。”[8]“它主張沒有知識不是技術知識。”[8]11“理性主義的政治是政治上沒有經驗的人的政治”[8]23,新的政治上沒有經驗的階級“每一個都需要一種抄本,一種政治教義,以取代政治行為習慣。”[8]25從歐克肖特的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柏克反啟蒙先驗政治理性的影子,只不過少了些柏克那種即時性的、尖銳的、帶有情感偏見和神秘色彩的批判味道。
稍遜于柏克的革命批判,伯里也認為,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借理性的名義而行動”“這班使徒自以為替理性開了新紀元,實則理性的名字被冤枉地誤用,這是空前絕后的一幕。”[9]而勒龐則把柏克與邁斯特的批判結合起來,外加了一種心理學的解釋,在現代更加激烈地批判法國大革命。他認為,英國經歷了兩次革命,把一位國王送上了斷頭臺,但仍是一個穩定的國家,“英國人從來沒有像我們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樣,夢想以理性的名義徹底打破古代的傳統,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10]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神秘主義邏輯常常嫁接在感情和激情的沖動之上,它是大型群眾運動的力量源泉。”[10]63“極為微弱的理性力量、強烈的激情和濃厚的神秘主義,正是構成雅各賓精神的三種心理要素。”[10]71我們可以從勒龐對大革命的批判中,看到柏克與邁斯特大革命批判的理論因子:尊崇古代傳統,反對抽象理性誤用。傅勒也冷靜地觀察到,那時的政治家“觀念超前”,在政治行動上更多的是“臨場發揮”,法蘭西精英階層、知識分子“本質上也是對政治經驗一竅不通的一個社會集團”[11]。從傅勒的觀察中,我們也可看到柏克對大革命先驗政治理性批判的路數:抽象的理論觀念指導下的革命,缺乏政治經驗。后現代法國哲學家福柯等延續思考啟蒙哲學、法國大革命、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中的理性問題,也反對理性的總體性,反對理性的暴力、理性的集權主義。后馬克思主義者墨菲很好地總結了保守思想對啟蒙理性的批判,他說:“保守思想主要著力點之一確實在于它對啟蒙的理性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批評,這是它與后現代思想的相同之處。”[12]
在柏克看來,理性主義原則和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便成為一種集權和暴力。誠然,法國大革命高潮時期有血腥恐怖與暴力,但不能簡單地說這就是理性主義和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的結果,而應該從當時法國的社會政治矛盾、民族性、文化傳統與革命情勢中去找原因。抨擊法國大革命的人,一般都會突出英、美的政治經驗,強調英、美的自由主義政治,批判法國大革命對自由的“傷害”,把英、美兩國與法國看作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典范,進而看作兩種完全不同的現代性。在他們的視野中,英、美的現代性是比法國的現代性更好、更合理的現代性選擇。
不過,柏克審慎、妥協的保守政治理性中也含有一些現代公共理性的成分,而推崇理性的葛德文在反對暴力革命的時候,對現代公共理性更是有較大貢獻。葛德文強調,應該反對憤懣、怨恨和狂怒,應該要求的只是清醒的思維、清楚的辨識和大膽的討論,在把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以前愿意年復一年地等待,而革命及其暴力有害于理性的和諧進程、獨立精神與自由研究。所以,從理論認識層面上講,葛德文看好一種文人的理性商談機制,“動嘴動筆乃是促進人類社會改變的正當而合宜的方式,而暴亂則是不正當和可疑的方式。”[13]
把這種妥協的、商談的理性真正轉換為現代公共理性的,是羅爾斯的公共理性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或話語理論。羅爾斯所談的公共理性是在一個政治民主的國家里,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為公共善進行商談的理性,“公共理性之理想的關鍵是,公民將在每個人都視之為政治正義觀念的框架內展開他們的基本討論”[14]。哈貝馬斯則論述了“理性的公用”。他認為,自主的公民們通過公開運用理性探討現實政治的合法性等問題,但他們無法把實踐理性付諸實現,因此他們“應當把握和認真對待否定他們自身的自主性后果,把握和認真對待把實踐理性付諸實現的意義”,而羅爾斯的“‘重疊共識’就只是實用性的一個癥候,而不再是理論正確性的一種證明。”[15]“重疊共識”所關注的是如何“確保社會穩定的問題”[15]74。
從柏克、葛德文到羅爾斯、哈貝馬斯把理論付諸實踐之前年復一年的等待和商談中,我們可以看到由啟蒙理性運動始發,經大革命實踐對理性的洗禮,再到和平年代的公共理性話語的運動軌跡:政治事實與政治價值的適度分離。
[1]哈列維.哲學激進主義的興起[M].曹海軍,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99.
[2]柏克.法國革命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85.
[3]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M].馮克利,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1.
[4]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M].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21.
[5]柏克.自由與傳統[M].蔣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12.
[6]休謨.休謨政治論文選[M].張若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93.
[7]肯尼.牛津西方哲學史[M].韓東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312.
[8]歐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義[M].張汝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2.
[9]伯里.思想自由史[M].宋桂煌,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61.
[10]勒龐.革命心理學[M].佟德志,劉訓練,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8.
[11]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M].孟明,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255-256.
[12]墨菲.政治的回歸[M].王恒,臧佩洪,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19.
[13]葛德文.政治正義論:第2卷[M].何慕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488.
[14]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240.
[15]哈貝馬斯.包容他者[M].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3.
Priority of Experienced Political Rationality over Transcendental Political Rationality——Analysis on Burke’s Political Philosophy Critique on French Revolution
Li Fuyan
(College ofMarxism,Shenyang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110034)
During the period of French Revolution,Burke attacked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of French Revolution violently by experienced political rationality,for he thought that experienced political rationality was superior to transcendental political rationality.He also opposed to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thinker Jean Jacques Rousseau and other abstract political theory designs.Later he had built a model of experienced political rationality for the world from the so-called true rationality.The prudent,conservative political rationality of Burke also contained some elements of modern public reason,from the waiting and negotiations year after year.Before Burke,GedeWen,Rawls and Habermas put theory into practice.From the rational practice of the baptism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o the peaceful era trajectory of public rational discourse,it can be seen that the orbit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movement:the appropriate separation offact and value.
experienced political rationality;transcendental political rationality;Burke;French Revolu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B504
A
1674-5450(2017)04-0029-05
【責任編輯:趙 偉 責任校對:趙 踐】
2017-04-17
遼寧省社會規劃重大研究方向課題(L15ZDA008)
李福巖,男,遼寧遼陽人,沈陽師范大學教授,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與社會政治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