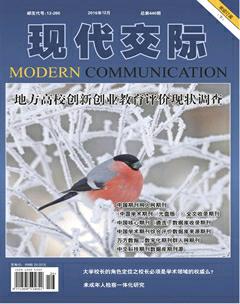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罪數與形態認定
許永++程琳
[摘要]近年來,隨著民間借貸的盛起,人們的投資風險意識不足,實踐中經常發生各種債權債務糾紛且執行的難度較大,頻頻發生行為人以拘禁他人的方法索取債務的案件。文章從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罪數與形態認定方面入手,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及實踐情況,多角度、多維度詳細分析了該罪的罪數問題、犯罪形態問題以及共犯問題,以期使司法工作者在面臨困難時能夠豁然開朗,從而進一步提高法治水平,加快法制建設。
[關鍵詞]非法拘禁 綁架 債務
[中圖分類號]D9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11-03
一、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一罪與數罪
對于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罪數認定應當分不同情況分別判斷:一,非法拘禁行為單獨構成犯罪,其他行為尚不足以構成犯罪時,僅成立非法拘禁罪一罪;二,當非法拘禁只是其他犯罪的手段行為,兩者之間存在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的牽連關系時,不再認定為非法拘禁罪;三,當非法拘禁與其他相聯系的行為均構成犯罪,兩者之間無牽連、想象競合吸收關系時,應數罪并罰。①
(一)結果加重犯
非法拘禁罪的結果加重犯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行為人對于被害人的重傷或者死亡結果主觀上是出于過失;二是被害人的重傷或者死亡結果與行為人的拘禁行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我們在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時應當看其拘禁的整個過程中,對被害人所遭受的人身危險的預見上,結合犯罪手段、暴力程度以及行為人的主觀判斷能力進行綜合評價。例如:行為人在非法拘禁的過程中雖然使用輕微暴力,但是被害人是因為自身的體質或者難以預料的情況而死亡的,我們在判斷其主觀心態時應當綜合考慮行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的特殊體質以及其是否具有可預見性。
被害人的重傷或者死亡結果與拘禁行為之間應該具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關系,即必須是非法拘禁行為本身所導致的。例如:因為拘禁中進行長期的捆綁、挨餓等因素導致的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或者被害人不堪忍受長期的折磨而自傷或者自殘的。此時,我們應當認定為被害人的重傷或者死亡結果與拘禁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是如果是因為行為人自身的原因不慎死亡的,我們能否認定兩者之間有因果關系呢?
案例:2014年10月,行為人甲在被害人乙(已死亡)經營的位于某小區六樓的麻將室打牌。同年12月1日,甲從他人處得知,乙在麻將機中安裝了作弊程序致自己輸掉大量現金,便找丙幫忙要回輸掉的錢。兩日后,甲電話聯系丙約其到麻將室幫自己向乙索要輸掉的錢款,丙糾集丁一同前往。到場后,三人要求乙在10分鐘內給出退賠的錢款,在未得到滿意答案后,三人威脅要毆打乙。當日23時許,三人逼迫乙給甲寫下一張自己在麻將機中安裝作弊程序的證明以及5萬元人民幣(甲在乙處輸掉5萬元)的借條后,逼乙還錢未果,后于次日凌晨1時許將乙押回麻將室,繼續看押乙。約一小時后,乙趁甲、丙外出買酒,丁上廁所時,襲擊丁并將房門反鎖后翻窗逃跑,不慎墜樓身亡。
本案例事實比較清楚,但在對幾名被告人定罪時產生了巨大的爭議:
一種意見認為幾名行為人構成非法拘禁罪,且具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行為。理由:幾名行為人主觀上對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具有過失。在非法拘禁期間,行為人非法限制、剝奪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致使被告人實際上負有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的特定義務,該義務是由行為人先前的非法拘禁行為引起的。所以在實施非法拘禁的過程中,行為人應當考慮到被害人具有發生人身危險的可能性,而本案中幾名行為人均沒有預見到,其主觀上具有疏忽大意的過失。
(二)行為人的非法拘禁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本案中,行為人對被害人進行看押,并要求被害人償還大量的錢款,被害人為了擺脫非法拘禁行為想獲得人身自由選擇爬窗逃離而不慎墜樓身亡,故行為人的非法拘禁行為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非法拘禁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另一種意見認為行為人僅構成非法拘禁罪,并不存在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行為。理由:1.行為人甲由于被害人在麻將機中安裝程序致使自己輸掉大量的錢款,主觀上只是為了要回自己輸掉的錢款,并不希望對被害人有任何傷害的意圖,從非法拘禁較短的時間及拘禁過程中幾名行為人僅是口頭威脅被害人從未有過毆打的行為均能體現。所打欠條的數字也與甲輸掉錢款的數目相當,只要被害人主動將自己的非法所得還給被告人甲,本案未必構成刑事案件。2.本案行為人的非法拘禁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已經中斷。行為人非法拘禁被害人,與被害人翻窗逃跑之間雖然存在因果關系,但被害人翻窗逃跑過程中不慎墜樓的行為中斷了拘禁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行為人的角度而言首先是不希望被害人逃跑的,其次更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因為行為人只是想追回自己應得的錢款。從被害人的角度講,被人非法拘禁后希望逃跑是人之常情,但逃跑過程中應當注意對自己人身的保護,在寒冷的冬夜從被看押的六樓民居翻窗逃跑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危險性,被害人置此危險于不顧仍然選擇翻窗逃跑,最終失足墜樓身亡,中斷了其非法拘禁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結合案件本身來看,筆者認為,行為人對被害人的拘禁行為相較于一般的非法拘禁罪是十分輕微的,且看押被害人的地點是被害人自己經營的位于小區六樓的麻將室,看押的時間也是寒冬臘月的深夜。換做一般人都會認為只要被害人把自己非法獲得的錢款如數還給行為人就可以了,但被害人的做法顯然與常人思維不一致,寧可冒著從六樓翻窗逃跑的風險也不愿意歸還錢款。按照正常的思維,在這種環境下除了部分特定的人員,如特種部隊、消防官兵等人之外,從六樓逃亡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一般人從六樓翻窗逃跑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被害人仍然冒著這種風險選擇逃跑。這對行為人要求的注意義務實在太高,甚至到達了苛刻的地步。被害人在逃跑過程中墜樓死亡純屬意外事件,如果仍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對幾名甚至不在現場的行為人定罪量刑,有失公正。
(三)轉化犯
轉化犯的實質是在某一具體犯罪的實施過程中,由于其他情形的加入,使得犯罪構成發生了變化,超出了原罪而滿足另一罪的情形。
在非法拘禁過程中,使用暴力致人重傷、死亡的,分別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要使非法拘禁罪轉化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暴力行為,并且造成了被害人重傷、死亡的危害結果;二是行為人實施暴力的主觀方面必須是故意。正如張明楷的觀點:非法拘禁他人,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是指超出非法拘禁行為本身以外的暴力致人傷殘或者死亡(因為非法拘禁行為本身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暴力),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是故意,此時才能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②例如:行為人在拘禁過程中使用捆綁、拳打腳踢等一般人認為不足以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輕微暴力,導致了上述危害結果。此時,行為人并沒有傷害、殺害被害人的故意,主觀上是過失。若行為人實施的是刀砍棒擊等嚴重剝奪他人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暴力手段,并且憑借一般人的認識也能預料到可能造成重傷或者死亡的危害結果,此時,我們可以推斷出行為人主觀上是基于故意的心態實施的暴力行為,其行為已經由非法拘禁轉化為故意傷害、故意殺人。因此,導致被害人重傷或死亡結果的,究竟是結果加重犯還是轉化犯,應當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方面以及因果關系進行判斷。
非法拘禁中,行為人索要債務數額發生變化可能轉化為綁架罪。例如:甲欠乙30萬元,乙多次向甲提出償還債務,甲均以各種理由拒絕,未果。乙糾集多人將甲予以扣押,本想要求甲歸還人民幣30萬元,后乙覺得只要回本金太虧,不足以彌補自己的損失,最終決定要求甲歸還50萬元債務。甲的家人報警,乙被抓獲。乙聲稱多要的20萬元是其因為甲未按時歸還債務所受的損失。這個案例屬于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即名為索債,實為勒索。從表面上看,甲與乙之間確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乙對甲進行非法拘禁也是為了實現債權,看似符合索債型非法拘禁的犯罪構成,但是從數額上來看,已經明顯超出其本身債務的數額,其犯罪意圖已經由索取債務轉變為勒索財物,認定為綁架罪更為適宜。
(四)數罪并罰
如果行為人在非法拘禁之前或者之后,傷害或者殺害被害人的,應當分別定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與非法拘禁罪進行數罪并罰。因為此時行為人實行的是兩個行為,既不存在結果加重的情形,也不存在轉化的情形。
如果行為人在非法拘禁的過程中又搶劫被害人財物,搶劫的目的不是為了沖抵債務而是為了占為已有,那么其主觀目的已經發生改變,構成搶劫罪,與非法拘禁罪實行數罪并罰。③因為非法拘禁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綁架罪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又侵犯了財產權利,綁架罪中又實施搶劫的,可以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從重處理;行為人在非法拘禁中又實施搶劫的,因其侵害的是不同客體,不存在吸收的問題,所以不能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處理。
二、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既遂與未遂
理論界對于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既遂與未遂認定標準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一)“結果犯”說
該說認為本罪既遂的標準是行為人通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為實現自己的債權。如果行為人已經實行了非法拘禁行為,但是還未實行向債務人或者第三人索要債務的行為就被抓獲了,或者雖然實行了向債務人、第三人索要了債務的行為,但是其債權還未實現就被抓獲了的,構成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未遂犯。
(二)“復合行為犯”說
主張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僅僅實行了拘禁行為并不能實現行為人的犯罪目的,行為人只有實行了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之后才能成立本罪的既遂,即非法拘禁行為加索債行為。如行為人只實行了其中的一個行為則不能認定為本罪的既遂。同時,達到本罪既遂的標準并不要求行為人實現其犯罪目的。④
(三)“單一行為犯”說
該說認為,成立本罪的既遂只需要行為人基于索債的目的實行完成非法拘禁他人的行為并實際控制被害人即可。至于行為人是否向他人提出了索取債務的要求,以及是否實現了自己的債權并不影響本罪的成立與既遂。⑤
筆者贊成單一行為說,因為判斷犯罪是否既遂,應當看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是否完全具備了某種罪名的全部構成要件,不能以犯罪目的是否實現作為劃分犯罪形態的標準。例如:甲欠乙10萬元,乙多次索要未果,遂糾集丙、丁將甲扣押起來,并向甲的家人索要債款,后甲的家人報警,甲得以解救。本案中,乙雖然是以索債為目的扣押甲,但是其將甲控制起來之時就已經既遂了,不管后面是否向甲的家人索要債款、債權是否實現,都成立既遂。因為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作為普通非法拘禁罪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行為人只要實際控制了被害人,滿足了普通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構成,即可成立本罪的既遂。“索取債務”只是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目的,并非基本構成要件。并且非法拘禁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身體自由權,并不侵犯他人的財產權,所以,不能將行為人主觀目的是否實現作為認定既遂的標準之一。
三、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問題
我國對于共同犯罪范圍的界定采取“犯罪共同說”,即認定共犯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是犯罪主體必須為二人以上;二是雙方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三是雙方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超出共同犯罪故意以外的犯罪,行為人之間不構成共同犯罪,應由實際行為人承擔自己超出共同故意以外的責任。
(一)債權人與他人共同實施非法拘禁行為的認定
(1)當債權人為了索取債務糾集他人一起實施非法拘禁行為時,雙方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實施拘禁行為時,雙方構成非法拘禁罪的共犯。例如:甲欠乙10萬元,乙糾集與甲無任何債權債務關系的丙共同扣押了甲,丙雖然與甲并無債權債務關系,但是丙與乙是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實施非法拘禁他人的行為,因此,構成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
(2)如果債權人與被害人之間本無債權債務關系,但是欺騙第三人稱其有債權債務關系,請求第三人非法拘禁被害人幫其索債,那么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則不成立非法拘禁的共犯。例如:甲為了斂財產生了綁架乙的歹念,并糾集丙謊稱乙欠其錢,請求丙幫其索債,二人將乙關押起來。在此期間,甲打電話向乙的家屬索要錢財20萬元,丙負責看押乙。直至乙的家屬交出財物,乙才得以釋放。案例中的甲和丙共同實施了拘禁乙的行為,表面上看構成非法拘禁罪的共犯,實則兩人之間有著不同的主觀故意:甲明知自己與乙之間并無經濟往來,基于勒索財物的目的伙同他人對乙實施拘禁行為,主觀目的為非法占有;丙由于存在認識上的錯誤,誤以為甲與乙之間有債權債務關系而幫助甲拘禁被害人乙,其主觀上是為了實現甲的債權,并無其他非法目的。因此,二人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不能認定為共同犯罪,應分別對甲、丙以綁架罪、非法拘禁罪論處。該案例屬于典型的共同實行犯之間的意思聯絡不一致,其中部分行為人對另一部分實行犯主觀犯意及事實情況缺乏認識,所以對現實發生的結果原則上阻卻共同犯罪的成立。⑥
(二)債權人委托他人實施非法拘禁行為的認定
債權人自己不參與討債而是委托他人進行討債的時候,債權人是否與受托人構成共同犯罪?
(1)債權人委托他人幫助自己實現債權時,明確提出必須采取合法手段,而受托人為了盡快實現債權而采用非法拘禁的手段索取債務。此時,債權人與受托人之間不夠成共犯,受托人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由自己承擔。債權人與受托人之間沒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明確表明了采取合法手段,因此,債權人不應對受托人的行為負責。例如:甲委托乙以合法手段向丙索要債務,并答應事成之后給乙一定的分成,乙為了盡快拿到分成采用非法手段將丙扣押起來,并采用暴力手段致丙重傷。這種情況下,應當由乙獨立承擔拘禁他人的責任。
(2)債權人要求受托人采取拘禁的手段并且不得傷害被害人索取債務,而受托人未經債權人同意違背其意志私自采用暴力手段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結果或者是超出雙方的“合意”索要明顯超出原債務數額的財物。這種行為已經明顯超出債權人的授權范圍,屬于“實行過限”,債權人只與受托人在共同故意的范圍內承擔刑事責任,超出的過限行為由受托人自己承擔。如果債權人明知受托人實施了過限行為而不加以阻止的話,債權人應當對“過限行為”承擔同樣的刑事責任。⑦例如:甲委托乙以合法手段向丙索要債務,并答應事成之后給乙一定的分成,乙為了盡快實現債權,采用暴力手段扣押了丙,致丙重傷,并在甲不知情的情況下索要了遠超過原債務數額的財物。此時,甲與乙只在共同的犯罪故意范圍內承擔責任,對于丙的重傷結果以及超出原債務數額的財物由乙單獨承擔責任。
(3)債權人委托他人幫忙索債,但是對受托人采取的手段持放任態度。受托人不管是采取何種手段索取債務,債權人都應對受托人的行為負責,因為債權人明知受托人可能會采取非法手段甚至會造成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結果,沒有采取任何的風險告知以及警示行為,而是放任其違法行為,主觀上存在概括的故意,根據“概括故意以結果論”的原則,債權人應當與受托人共同承擔刑事責任。例如:甲委托乙向丙索要債務,并聲稱不管采用什么手段都要把錢要回來,乙于是采用拘禁手段控制了丙,在非法拘禁的過程中又使用暴力致丙重傷。這種情況下,由于甲并沒有履行風險告知以及警示義務,主觀上存在一個概括的故意,因此,甲應當與乙共同承擔致丙重傷的責任。
(三)事中參與人行為的認定
事中參與人即“事中共犯”,其并未參加非法拘禁行為的組織策劃,而是被害人在被拘禁期間參與進來,例如:甲被乙拘禁期間,丙幫助乙看押甲,給乙送飯送水,應當認定為非法拘禁的共犯。因為事中參與人對整個的拘禁行為起到了幫助、輔助的作用,給拘禁行為提供了便利,間接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因此,以非法拘禁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責任沒有問題。
(四)單位為索取債務指使單位工作人員實施非法拘禁行為的認定
由于法律沒有規定單位可以成為非法拘禁罪的主體,但是現實生活中經常會發生由單位決策機構決定,單位工作人員實施索債行為的情形,此時,我們可以認定單位決策人員與單位工作人員構成共同犯罪。例如:甲、乙分別為丙公司的經理和員工,甲指使乙向丁索要債務,乙采用非法手段扣押了丁,并致丁重傷,雖然乙是代表單位的意思實施的拘禁行為,但是由于單位不是非法拘禁罪的主體,所以應當由甲和乙共同承擔責任,成立索債型非法拘禁罪的共犯。
注釋:
①趙秉志.非法拘禁罪、綁架罪專題整理[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26.
②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03.
③夏自衛.索債型非法拘禁行為的刑法問題[D].湘潭大學,2003:27.
④張明楷.刑法學(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
⑤劉憲權,錢曉峰.關于綁架、拘禁索債型犯罪定性若干問題研究[J].法學,2001(09):31.
⑥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603.
⑦傅陽.論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中的若干問題[D].華東政法大學,2012:31.
【參考文獻】
[1]魏昌東,錢小平著.非法拘禁罪、綁架罪專題整理[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
[2]陳山著.非法拘禁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3]張明楷著.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5]祝銘山主編.非法拘禁罪、綁架罪[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6]趙秉志主編.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分則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徐松林主編.刑法學[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2011.
[8]楊興培.索取非法“債務”拘押他人的刑法定性[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02).
[9]張雯瓊.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區別之探討[J].法制與經濟,2012(02).
[10]黃麗勤.索債型非法拘禁案件的定性分析[J].法學,
2012(04).
責任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