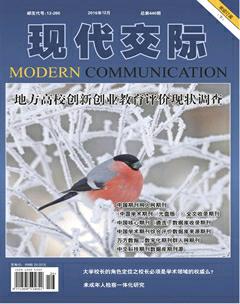略談音樂的社會教化作用
金鎮國++金順愛
[摘要]音樂對社會風氣的形成、社會文化的建立,起著潛移默化、舉足輕重的作用。建設有秩序、和諧的社會需要有能夠啟迪思想、滋潤心田、陶冶人情懷的音樂,防止頹廢萎靡的風氣。
[關鍵詞]音樂教化 正能量 傳承 弘揚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4-0078-02
一、音樂的多種功能
(一)教育功能
利用美的旋律等音樂特征,來影響人的情感世界和心靈,從而對思想情操、道德觀念發生滲透式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開發人的潛能、發展創造性思維、培養音樂能力等。
(二)社會功能
音樂能使我們在生產、生活、交際中,調節人和人、團體和團體、國家和國家之間關系,能夠相互和諧地相處和交流。
(三)審美功能
音樂具有凈化心靈、啟迪智慧、陶冶情操、調節身心和諧等功能。
(四)認識功能
人們通過音樂的象征、模擬、暗示、抽象等表達方法,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認識現實和歷史,同時也可以從中認識藝術創造者的立場、觀點、情感和精神狀態。
(五)娛樂功能
愉悅養性、怡情健身、參與自娛等作用。
二、音樂對社會的教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音樂的諸多功能中教育功能應該是最重要的,古今中外的有智慧人士,很重視音樂教化作用,良好的音樂對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現代社會在商業大潮的影響下,音樂的娛樂功能被放大了。人們過分追求音樂的感官刺激,音樂的思想內容被淡化了。而且代表前沿音樂的流行音樂,其創作魚龍混雜,不乏低俗的作品,影響著社會風氣。
(一)“善樂”使人心善,使社會形成良好的風氣、秩序井然
中國古代的舜帝具有高度的智慧,懂得運用音樂來教化人心。
“帝曰:‘夔[kuí]!命汝典樂,教冑[zhòu]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意思是舜帝說:“夔,任命你去主持樂官,教育后代子孫,使他們正直而且溫和,寬厚而且謹慎,剛毅而不粗暴,能諫諍而又不傲慢。詩可說出心中志向,歌唱可詠出表達思想感情的語言,聲調依據歌聲詠唱,六律和諧五聲,八種樂聲能夠和諧,不搞亂相互順序,那么神與人將會和睦。”
可見古代圣賢都很重視用音樂的手段來教化人,使其具有良好的修養,乃至讓社會有秩序。
周代的禮樂制度是樂從屬禮的思想制度。它所培養的對象是王和諸侯的長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從民間選拔的優秀青年。主要教授學員們學習六代樂舞與小舞。大司樂通過音樂教育,使貴族子弟懂得“禮樂”是一種有效的治國方式。
周代的禮樂制度以“禮”來區別等級秩序,同時又以“樂”來共融和同“禮”的等級秩序,兩者相輔相承。按周禮,天子的舞隊用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士二佾。
不同階層使用不同人數的舞隊,形成了等級秩序,使人通過“禮樂”制度來懂得禮節和秩序,使國家長治久安。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共傳31代38王,朝代歷史綿延791年,“禮樂”制度在治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孔子的音樂造詣很高,精通音律,曾說:“韶,盡美也,又盡善也。”“武,盡美也,未盡善也。”意思是說,孔子評價《韶》樂時說:“藝術形式很美,思想內容也很好。”評論《武》樂時說:“藝術形式很美,但思想內容稍差一些。”
孔子主張好的音樂不但要做到藝術形式“美”,還要做到思想內容“善”。
(二)“惡樂”使人心惡,使社會形成不良風氣、秩序混亂
唐朝的詩人杜牧通過詩《泊秦淮》,譏諷群臣們沉湎于酒色的晚唐政治,詩中所描述的歌女唱“玉樹后庭花”,綺艷輕蕩,歌聲哀傷,是亡國之音。當年陳后主長期沉迷于這種萎靡的音樂,最后陳朝亡國,但靡靡的音樂卻留傳下來,還在秦淮歌女中傳唱。杜牧借題發揮譏諷群臣們沉湎于酒色的晚唐政治。
紂王因寵愛妲己,命令他的樂師師延匯集民間萎靡、頹廢的音調寫成作了《北鄙之音》和集中中原和東夷等少數民族中柔弱、淫蕩的舞姿寫成《北里之舞》。紂王和妲己非常喜歡這些靡靡之樂,常常通宵達旦歌舞游樂。后來,殷紂王被周武王消滅。
三、音樂要重視內容,提倡正氣、正能量
“文藝不能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優秀作品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堅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一)流行音樂的負面作用
現今社會流行音樂大行其道、魚龍混雜,很多流行音樂內容淺白甚至低俗,對社會的風氣的形成起到負面的效應。
有一首流新歌曲叫《別讓我的心為你流淚》。歌詞中說道:“別讓我的心為你流一滴淚,別讓我的夢為了你癡癡的醉,不在乎什么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過。”
究其內容表現了只想索取而不愿意為對方付出、把責任推卸給別人、不在相信有忠貞不渝的愛情等不負責任的態度和行為。
前一段時間社會上流行一首叫“老鼠愛大米”的歌曲,歌詞中有這樣一段話:“我愛你,愛著你,就象老鼠愛大米。不管有多少風雨,我都會依然陪著你。我想你,想著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讓你開心,我什么都愿意,這樣愛你”。“我愛你,愛著你,就像老鼠愛大米”這句歌詞給人的感覺是,對待愛情的態度像動物對食物的本能生理需求一樣,赤裸裸地表現了人的生理欲望,“只要能讓你開心,我什么都愿意,這樣愛你”,這句話表現了被愛情沖昏頭腦,神志不清、沒有理智的狀態。
流行音樂應該是先進的、進步的,在汲取傳統音樂營養的基礎上又有創新的音樂,而如今的很多流行音樂成了快餐式文化,發泄空虛的人的情欲工具。
流行音樂在異化的發展中,媒體的影響很大。
電視節目、網絡上流行音樂影響面很大,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極大地滿足大眾的感官刺激,滿足大眾的獵奇心理,只要是新奇甚至怪異的都可以登臺。
網絡上的音樂更是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地表達著個人的欲望。
(二)傳統音樂具有豐富的營養,要傳承和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也是我們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堅實根基。新的時代更需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中國文藝要更好發展繁榮起來,就要做到中西合璧、融會貫通,借鑒其他先進文化來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不斷地開拓創新。
京劇為什么能成為我國的國粹?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京劇的藝術理念、表演形式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觀,如端方中正,溫和典雅,善惡分明,空靈寫意,靈動婉轉。京劇的很多作品宣揚中華傳統文化的“真善美”和儒家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內容一致,對社會大眾具有很好的教化作用。
如京劇“赤桑鎮”描寫了包拯年幼失去父母,由嫂吳妙貞撫養成人。侄子包勉任蕭山縣令,貪贓枉法,包拯秉公將其鍘死。吳妙貞趕到赤桑鎮,哭鬧不休,責包拯忘恩負義,包拯婉言相勸,曉以大義,吳妙貞感悟,叔嫂和睦如初。
中國京劇藝術的表現手法具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中國京劇是寫意為主,追求內容與形式的高度和諧。外國歌劇是寫實為主,追求真實感,常常表現出偏重形式,寫實更容易追求感官刺激。
京劇藝術中寫意的藝術表達方式,是以主觀表現為出發點的。用千變萬化的藝術形式描繪出人、事、物在人們心中的投影,以意達形。京劇音樂的表現方式也是經過主觀的提煉乃至改造,用程式化的表現方式來表達人物心理和描述大千世界。表演手法上不求形似,但見神韻,音樂的表現上不求絢麗美妙,但求傳達者深沉的內涵。
西方藝術表現手法總是趨向于認識外在世界的規律形式。而追求形式的美首先是滿足感官上的東西。因此,西方音樂總是竭力強調滿足視聽之美。西方藝術的這種導向外部形象世界的美學致思方式,使得西方藝術更注重外在客觀世界的捕捉。
如京劇表演中的“趟馬”的表現手法就是寫意的,寫意具有較高的藝術性、想象性,注重內容的表達。而歌劇《阿依達》中的“凱旋進行曲”這一段的表現手法就是用寫實的,它更注重宏大的場面、真實的場景,以此來滿足觀眾的感官需求。
在當今社會,傳統音樂的發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如優秀的民族民間音樂,在社會上因社會關注度弱,市場小,觀眾少,資金有限,文藝工作者青黃不接,沒有傳人等諸多問題,它的發展舉步維艱。
但這需要音樂工作者和教育者不懈的努力,提倡和傳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創作有正能量的音樂作品。在新創作的音樂作品中也有很多是具有正能量的,如歌唱祖國的《祝福祖國》《永恒的愛戀》;歌唱人民公仆的《公仆贊》;歌唱父母的歌曲《父親》《母親》;歌唱老師的歌曲《老師,我想你》;勵志的歌曲《從頭再來》等一些歌曲都傳遞著正能量,鼓舞著人心。
四、音樂創作和音樂教育應該有正確的導向
音樂創作從傳統音樂中汲取營養,學習先人的創作經驗,以古圣先賢的教導為指導思想,進行音樂作品的創作。
文藝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要把握好正確的方向。通俗易懂的音樂,不能低俗諂媚,單純感官娛樂只能滿足暫時的欲望,不能得到精神快樂。
音樂創作要創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與時俱進、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好的音樂作品能夠啟迪思想、滋潤心靈、陶冶人的性情,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低俗、空虛等不良情緒。音樂工作者要具備正確的價值觀,給人們創造出崇高、偉大、美好的形象,使人們正確地對待美善丑惡,潛移默化地啟迪人們的心靈。要把正能量作為音樂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文化觀。
我們要通過音樂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通過音樂,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
【參考文獻】
[1]李純一.孔子的音樂思想[J].音樂研究,1958(05).
[2]賀賓.傳統戲曲社會教化功能作用機理探微[J].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1).
[3]朱東黎.試論音樂的社會教育功能[J].東方藝術,2005
(10).
[4]王淑芝.音樂的社會功能淺析[J].戲劇文學,2003(10).
[5]常金倉著.周代禮俗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6]孫榮春.《禮記》美育思想探析[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06).
[7]張浩.芻議流行音樂的教化功能及其異化[J].中國音樂學,2006(03).
責任編輯: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