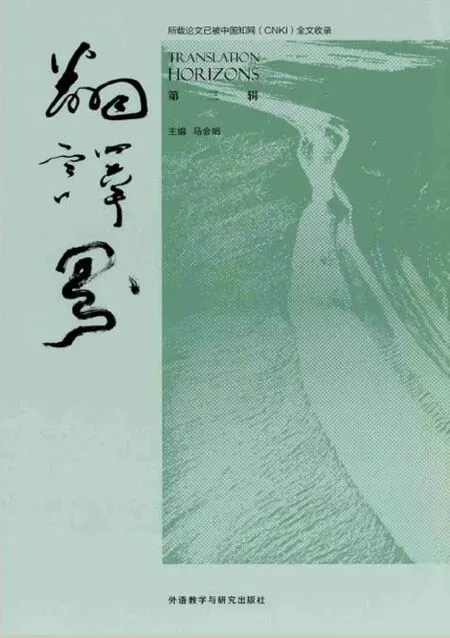非職業口譯:回顧與前瞻
王炎強
復旦大學
非職業口譯:回顧與前瞻
王炎強
復旦大學
非職業口譯在翻譯市場上非常活躍,占據口譯行業半壁江山,應該得到研究者更多的關注。然而“非職業口譯”的概念是在口譯走向職業化道路后才被提出,非職業口譯常常作為職業譯者翻譯能力研究中的對比參照物。“非職業口譯”概念需要更加細化,非職業口譯與職業口譯的關系需要進一步厘清。本文試圖通過文獻梳理,探究非職業口譯的概念及發展,并嘗試對非職業口譯進行分類,探討其特征及其對口譯教學的啟示。
非職業口譯;自然翻譯;天然翻譯;口譯教學
1.引言
只要不同語言背景的人進行交流,就離不開口譯的橋梁作用。精通雙語的人或多或少有過口譯經歷,包括幫助親友、單位同事或領導進行涉外交際等志愿者語言服務。上述口譯活動的參與主體具備一定雙語能力但沒有經過正規口譯培訓,通常臨時擔任口譯任務,很少獲得甚至沒有任何經濟報酬。與職業口譯相比,這類口譯活動是“非職業”或“業余”口譯,有時也被稱為志愿者口譯(volunteer interpreting)或臨時口譯(ad hoc interpreting)等。通常情況下,非職業譯員單獨從事口譯任務,幾乎沒有得到職業譯員群體的承認,其作為譯員的社會身份認知度較低。歷史上從事口譯工作的譯員大多是非職業的,從精通雙語到“自然翻譯”再到口譯實踐,逐漸在實踐中獲取口譯技能。直至今天,沒有經過正規職業訓練的非職業譯員在跨語言、跨文化交際活動中依然活躍。在社會經濟領域以及學校、社區、企業、醫院、法庭、教堂、媒體及商場等場合都可見他們的身影。構成了口譯研究的新領域、新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本文試圖探究非職業口譯的概念及發展,并嘗試給非職業口譯下定義并進行分類,在此基礎上探討其與職業口譯的異同,以及對口譯教學的啟示。
2.文獻回顧
近年來一些翻譯市場調查結果表明,非職業譯者在翻譯市場上依舊非常活躍,在翻譯行業占據半壁江山(王恩冕,2004;潘珺、孫志祥、王紅華,2009)。然而非職業口譯并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關注。已有的非職業口譯研究基本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主要針對雙語兒童日常生活及學生教育中的口譯現象,突出兒童自然形成的翻譯能力。哈里斯(Harris)強調了語言及翻譯能力的與生俱來,認為雙語者的翻譯能力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都與自然本能相關,雙語者的年齡越小,翻譯能力發展的潛力越大(1977:97)。安吉萊莉(Angeleli,2011)的雙語兒童實證研究也證實,從兒童期開始展現出的翻譯能力經過長期不斷實踐可以保持并提高。一些在幼年有過翻譯實踐的雙語兒童長大后,仍然能夠保持較強的翻譯能力,并持續提供翻譯服務。
第二類從實證角度考察了成人非職業口譯活動。通過分析口譯錄音撰寫記錄,對源語和目標語進行對比,發現非職業譯員對口譯職業規范的偏離,例如對醫療和精神健康場合的口譯質量評估(Lang, 1975; Price, 1975;Launer, 1978; Marcos, 1979)。更多的非職業口譯研究聚焦于公共機構及社區等口譯場合中的臨時口譯或志愿者口譯,通過案例話語分析,從社會學話語權力、參與立足點等角度剖析非職業譯員的角色問題。例如雅斯克萊寧(J??skel?inen, 2010)研究了電視主持人擔任非職業口譯的角色問題。主持人既是主要發言人同時也是交際中的譯員,其身份角色的界限在這種場合下不再清晰。主持人在訪談交流中的翻譯通常會過濾掉一些自認為沒有必要談到的話語和信息,造成訪談嘉賓對翻譯的不信任。塞利格森(Berk-Shligson, 1990)分析了審訊過程中警察擔任口譯的情況,這種雙重角色讓譯員不再中立,以口譯為媒介的交際因此朝有利警方的方向進行。
第三類非職業口譯研究關注口譯學生及新手譯員,將其作為口譯職業能力發展研究中職業譯員的對照組,通過實證研究比較職業譯員和學生譯員在口譯質量及口譯能力方面的差異(徐海銘、柴明颎,2008)。
隨著社區口譯研究的蓬勃發展,非職業口譯研究領域近年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國際知名翻譯期刊《譯者》(The Translator)2012年出版了以非職業翻譯為主題的專輯,其中幾篇論文聚焦不同學科背景下非職業口譯,提升了學界對非職業口譯的關注,改變過去口譯研究領域對這一現象的忽視與偏見,在非職業口譯研究方面具有開拓意義。2015年出版的《勞特里奇口譯手冊》(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專門用一章的篇幅介紹非職業口譯,回顧了過往研究、詳述了非職業口譯的研究方法及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說是目前學界對非職業口譯研究較為全面的綜述(Martinez-Gomez, 2015)。在2016年最新出版的《口譯研究概論》第二版(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2nd edition)中,波契哈克(P?chhacker,2016)提出口譯及口譯研究的最新趨勢,其中之一就是非職業口譯的發展及相關研究。
可見口譯學界已經開始關注非職業口譯現象。但目前現有的研究中并沒有見到相對完整的非職業口譯定義,也沒有非職業口譯特點、類型及職業地位等的詳細論述。
3.非職業口譯的概念與類型
哈里斯(Harris, 1977)和圖里(Toury, 1980)相繼提出“自然翻譯”(natural translation)和“天然翻譯”(native translation)兩個概念。“自然翻譯”指未經過翻譯專業訓練的雙語者在日常生活中從事翻譯工作。這一實踐現象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證明雙語者能夠自然獲得一定的翻譯能力;而“天然翻譯”是指雙語者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會無意識地發展出一定的翻譯能力。哈里斯的“自然翻譯”概念強調語言及翻譯能力與生俱來,認為雙語者翻譯能力的形成和發展都與自然本能相關。而圖里的“天然翻譯”則強調個人與環境相結合的作用, 認為自然翻譯能力是雙語者在翻譯實踐過程中無意識習得。通過對比兩種語言的異同,激活跨語言轉換能力,最終形成翻譯能力。不管是自然具備的翻譯能力還是在實踐中習得的翻譯能力,其共同點就是沒有經過專門翻譯培訓而掌握了一定的翻譯能力,能夠從事臨時或志愿的翻譯工作。哈里斯的“自然翻譯”和圖里的“天然翻譯”是非職業翻譯的主要來源。
近現代翻譯職業培訓的蓬勃發展建立在如下假設基礎之上:接受過正式培訓的職業譯者能夠發展起特殊的專家能力,從而將其與自然翻譯或天然翻譯相區別。翻譯專家能力成了翻譯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然而,迄今為止認知學研究發現并沒有為口筆譯活動的職業性提供有利證明。曾文中(Tseng Joseph, 1992)在口譯職業化的研究中提到,目前很多人并不認為翻譯所需的專業知識或技能是職業譯者獨有的,翻譯能力所需的系統知識與技巧并非像其他專業一樣,僅僅由該專業從業人士專享,翻譯不具有專業規定意義上的排他性。這可能是翻譯職業化最大的障礙之一。曾文中認為雙語者自然形成的翻譯能力與職業培訓后獲得的翻譯能力并存,二者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因此很難在職業口譯與非職業口譯中間劃出清晰的邊界。盡管有研究表明持續提供優質口譯的專家能力主要通過設計良好的練習獲得,但也有證據表明,即使是受過正式培訓的譯員,有時會過度依賴常規的問題處理方式,無法實現超水平發揮。另一方面,有些沒有翻譯經驗的雙語者在從事一些需要非常規居間手段的復雜翻譯任務時卻能有意想不到的高水平表現(J??skel?inen, 2010: 214)。如果考慮到譯員的社會認知度以及客戶通過支付報酬對翻譯服務給予承認,對 “自然譯者”與“受訓譯者”的區分則會變得更加困難。
非職業譯者在翻譯市場上的活躍參與是不爭事實。時至今日,不少翻譯工作仍是由幾乎沒有接受過職業翻譯培訓的臨時譯員或志愿者擔任。翻譯贊助人選擇職業譯員還是非職業譯員時,通常會權衡二者的優劣。對于項目預算緊張,對翻譯要求不高的主辦方來說,費用較低或免費的非職業譯員更受歡迎。有些翻譯場合時效性強,機構內部的雙語職員常常成了首選,如急診醫療口譯常常由醫務工作者和患者家屬擔任。職業翻譯的優勢被使用后者的便利性替代。有些情況卻相反,交際方使用非職業譯者正是出于對翻譯質量的要求,例如在某些專業領域,如高技術與高度保密性行業,往往需要譯者對該專業非常熟悉;或對譯者職業道德要求高,需要內部職員提供口譯服務。另外,交際場合的正式與否也是選擇職業還是非職業譯者需要考量的因素。翻譯場合越正式,主辦方越傾向于聘請職業譯員。當然,最終決定使用職業譯者還是非職業譯者往往要平衡上述各因素。
非職業口譯是一種口譯現象,非職業譯員是非職業口譯工作狀態下的主體。非職業口譯通常具備以下一個或幾個特點:
(1) 由未經正規翻譯專業教育、缺乏翻譯職業能力、不以口譯為業、通常有其他職業但偶爾或臨時從事特定領域口譯活動的工作者所進行的語言居間(mediation)交際活動;
(2) 有可能接受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的報酬或免費工作;
(3) 沒有得到職業譯員共同體的認可;
(4) 沒有職業證書或能力資格認定。
非職業口譯范圍廣、類型多,在專業能力、服務方式、口譯場合以及口譯報酬等方面千差萬別,研究時很難用統一的概念涵蓋所有類別的非職業口譯。為了便于研究,筆者認為有必要將目前翻譯市場上活躍的非職業譯員進行分類。
首先是自然雙語者,即哈里斯所謂的“自然翻譯”,如雙語兒童或二代移民為周圍親戚朋友提供口譯服務。還有生活在邊境區域或者是因父母各操一種語言而與生俱來的雙語者為身邊人提供口譯服務。這些自然譯者精通兩種語言,天生具備一定的翻譯能力,在一般陪同、日常事務處理以及家庭生活中可以勝任語言居間工作。然而如果涉及具體的專業領域,他們的工作語言能力和專業知識就略顯不足,很難應對專業領域的居間交際。
第二類非職業口譯是臨時擔任口譯的機構工作者。例如,醫生、護士等醫護人員為病人提供的語言居間服務;學者、教師志愿為課堂講座等交流承擔口譯任務;或外交官臨時為兩國官員的交流提供口譯便利等。這類非職業譯員通過自學和工作中的翻譯實踐掌握翻譯能力和技巧,在特定文化環境下獲得翻譯技巧并有機會在實踐中不斷提高。
第三類是新手譯員或正在接受口譯培訓的學員。他們經過正規翻譯培訓,具備一定的口譯技巧及口譯能力,能夠快速學習相關領域的知識并有能力承擔一些難度不大的口譯任務。但由于缺乏職業實踐經驗,背景知識不全面等因素,翻譯時易受制于翻譯規范,按部就班,缺乏靈活性。因為口譯學習者不完全具備職業素養,也可以劃入非職業口譯的范疇。
最后,某些從事跨文化交際的人員也是非職業譯員的一類。很多跨語言、跨文化交際的工作是由雙語或雙文化者擔任。無論其具體工作內容是提供額外信息,指導還是顧問,都離不開語言翻譯活動,因此部分跨文化居間者的實踐與口譯工作存在交集。由于這些交際活動無法達到職業口譯所規定的標準和要求,這類口譯活動也可劃入非職業口譯的范疇。
4.非職業口譯的特點與地位
翻譯能力或“翻譯專家能力”(expertise)并非區分非職業譯者與職業譯者的必要條件。但一般而言,接受專門訓練的職業譯員能勝任多領域、多場合、不同形式的口譯任務,包括交替傳譯、同聲傳譯、視譯和耳語等。國際口譯員協會(AIIC)對職業會議譯員的要求是:能夠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內容口頭譯出,包括正式或非正式會議中的翻譯,職業會議譯員既能做交傳也能做同傳,無論原語多么長或多么復雜,他們都能夠勝任。1相比之下,非職業譯員通常僅能從事自己熟悉和擅長領域的翻譯工作。因此職業譯員的綜合口譯能力強于非職業譯員,更可能具備口譯專家能力。職業與非職業譯員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翻譯能力的差異。正式會議場合要求譯員不僅要有優秀的雙語翻譯能力,還要具備高壓下工作的素質以及靈活應對能力。穆罕默德扎德(Mahmoodzadeh, 1992)等人的研究表明職業譯員具備處變不驚的能力,能夠時刻保持冷靜,沉著應對各種壓力環境。因此正式場合通常要求譯員具備較強的職業能力。另外,正式大會通常使用同聲傳譯,而同聲傳譯需要相當長時間的專業培訓才能練就,并非普通雙語者或有過交傳經驗的非職業譯者能夠勝任。非職業譯者一般只能擔任交替傳譯任務。在非正式場合下的口譯多數為聯絡口譯、社區口譯或者簡單的交替傳譯。
其次,翻譯經驗的差距。口譯專業能力的發展呈現出階段化的特點(劉和平,2011: 37)。口譯能力并非隨時間的延續而自然提升,需要不斷的刻意練習才能從一個階段提升到更高階段(Ericsson et al, 1993: 364)。成為口譯領域的老手需要至少六到十年的工作經驗,而要成為口譯專家則需要更長時間。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招聘譯員通常要求至少200天以上的會議口譯經驗,2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翻譯實踐經驗對翻譯專業能力形成的重要性。一般來說,國際組織工作的譯員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特定領域較為熟悉并積累了廣泛的相關知識,口譯工作經驗豐富。活躍的自由職業譯員承接各領域、各類型的口譯活動,同樣積累了豐富的多領域知識及從業經驗。而臨時從事口譯任務或是志愿者口譯等活動的非職業譯員無論在翻譯領域的廣度上還是翻譯工作的頻率上都無法與職業譯員相比,口譯經驗與職業譯員差距較大。
此外,二者在翻譯職業規范與道德遵守上存在差異。鮑川運談及口譯職業化時提到,口譯職業化需要滿足的首要條件是有相當一部分譯員將口譯工作作為主要生活來源。這類譯員應該形成一個較大的群體,但要所有譯員都以口譯為生也不可能,市場上做兼職口譯的人也不在少數。在這種情況下,口譯職業化的第二個條件尤其重要,即譯員應具有職業素養,遵守職業規范,掌握職業技能,如果具備了這些,應該能稱為職業或專業口譯(鮑川運,2007:51)。
職業道德行為的養成,離不開知識學習和技能提高。專業理論知識與專業技能是形成職業信念和職業道德行為的前提和基礎。非職業譯員沒有接受過正規口譯培訓,翻譯準確度和原語忠實度都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另外非職業譯員沒有接受過口譯職業規范學習,職業規范意識不強,對誤譯、漏譯容忍度較高。此外,職業道德行為的養成離不開社會實踐,社會實踐是職業道德行為養成的根本途徑,也是職業規范內化的重要渠道。非職業譯員實踐時間相對較少,經驗積累不足,缺乏強化口譯職業規范的機會。職業證書或能力資格認定可以作為認定專家能力的依據,也是對譯員職業資質的認可。
從社會學角度看,非職業譯員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參與交際程度高于一般職業譯員。如果說職業譯員有時會糾結于到底應該“在場”還是“隱身”,非職業譯員由于口譯工作的臨時性及缺乏職業規范教育,翻譯中常常或多或少地貢獻自己的話語,擁有部分文本所有權,表現出較為明顯的 “在場”。克納普(Knapp-Potthoff & Knapp, 1987)對比了法庭口譯與非正式法律咨詢場合的口譯,發現交際場合的正式與否對譯員表現有決定性影響。如果口譯場合正式,譯員更傾向于隱身,人們也期望譯員的表現更像“傳遞信息的管道媒介”,決不能扮演“真正的第三方”的角色;而交際場合不正式,特別是參加交際人數較少,或僅包括不懂對方語言的雙方當事人再加上譯員,這種情況下譯員通常表現出更強的自主性。非職業口譯主要在非正式場合使用,這也會導致非職業譯員參與度較高。從權力關系角度來看,非職業譯員的社會地位有可能低于、等于或高于發言人。一般來說,非職業譯員自身的社會地位越高,對翻譯過程,甚至發言過程的控制力就越明顯。不少非職業譯員是交際所涉及領域的專家或機構內部知情人士,對溝通過程具有一定的控制力。非職業口譯的社會地位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待。一方面,隨著口譯職業化的發展,職業培訓和考試認證成了進入口譯職業的必要條件和主要途徑。非職業口譯的存在常常被認為擾亂了市場秩序,造成口譯標準參差不齊等問題。口譯職業化的發展降低了體制外非職業譯員的地位。特別是那些從事層次不高、難度不大的聯絡口譯或社區口譯的譯員。他們除了具備雙語能力之外,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和社會資源較少。從事的翻譯工作大多是陪同親友或者擔任志愿者口譯等規模較小的口譯活動。此外,這類譯員服務的對象社會地位不高,這也間接影響了主流社會對非職業譯員的評價。不少非職業口譯報酬低,或是免費提供口譯服務,較低的經濟待遇也阻礙了其社會地位的提升。
另一方面,高校教師、科研專家、政府外事官員等機構內部職員擔任非職業譯員時往往擁有雙重身份,既是臨時交際的語言中介又是實際參與交際的代表。譯員身份對于他們來說只是臨時的,而真正被認可的社會地位源于機構權威及專業知識。譯員身份只處在從屬地位,好的口譯表現能提升其原本的職業身份地位,而反過來,即使沒有翻譯好,也不會對其身份地位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
5.非職業口譯對口譯教學的啟示
目前,翻譯職業教育大規模鋪開,翻譯教學模式不斷創新。從翻譯能力發展的角度看,非職業翻譯研究給翻譯教學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念。事實上,從“自然翻譯”和“天然翻譯”現象可以看出,翻譯認知能力的獲得不一定完全依賴正規翻譯學習。這一事實可以成為翻譯教學改革的驅動因素。無論是翻譯專業本科(BTI)還是翻譯專業碩士(MTI),學生入學以前都已具備一定的口筆譯能力。因此教學上“應該放棄傳統上規定性及以產品為中心的教學法,轉而采用以學生為中心、基于翻譯需求及以過程為中心的教學法”(Gile, 1994: 110)。教師一方面指導學生從訓練初期就有意識地投入各類真實翻譯項目,認識翻譯規范,提高翻譯能力;另一方面鼓勵學生通過積極參與真實翻譯項目構建知識和能力體系。
非職業譯員豐富的專業背景知識可以轉換成為翻譯能力,彌補非職業譯員在翻譯能力和翻譯經驗方面的不足。這對口譯教學頗具啟發。教學中鼓勵學生提高語言文化知識儲備,掌握全面譯前準備能力,擴充所需背景知識。新手譯員和口譯學習者缺乏口譯實踐經驗,了解交際背景知識有利于增強口譯信心,彌補口譯技巧和經驗的不足,有助于快速提升整體口譯能力。
最后,從人才培養模式角度看,非職業口譯讓我們看到“天然翻譯”和“自然翻譯”在翻譯能力方面的潛質。如果能夠給他們提供一些定制化的培訓,加強翻譯技巧和翻譯倫理方面的認知,可為口譯職業市場提供多元化的人才,加快口譯職業化進程。翻譯專業碩士項目設置之初強調學生進入碩士階段學習前應有翻譯相關工作經驗,鼓勵有翻譯實踐的雙語從業者參加翻譯碩士學習,意在使其通過正規學習提升翻譯能力,強化翻譯技巧,提高翻譯倫理意識,實現從非職業譯員向職業譯員的轉變。
6.結語
非職業口譯研究方興未艾,目前研究方法主要從認知和社會學視角對非職業口譯現象進行描述。未來可以在語料庫基礎上開展更多職業譯員和非職業譯員對比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開展“模擬回顧”研究,讓非職業譯員在觀看自己的翻譯活動錄像時評價自己的翻譯表現并回憶當時的想法、感覺和角色認知,深入了解影響非職業譯員的社會文化因素。職業譯員與非職業譯員的對比研究無疑有助于深入理解口譯的內涵與外延,為口譯研究提供更多新視角。
隨著移民人數的增加以及英語的普及,未來會有更多的雙語、雙文化者活躍在各領域。即使只有10%的雙語者在學習和實踐中從事臨時翻譯活動,其絕對數量也會非常大。口譯研究必須重視口譯實踐的另外半壁江山。
注釋
1. AIIC.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iic.net. April 23, 2012. Accessed February 1, 2017. <http://aiic.net/p/4003>.
2. UN. “Language Careers”. Un.org. Accessed February 1, 2017. <https://languagecareers.un.org/content/interpreters>.
Angelelli, C. (2004). Revisiting the interpreter’s role: A study of conference,court, and medical interpreters in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Angelelii, C. (2011). Expanding the abilities of bilingual youngsters: Ca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help? In Maria Jesus Blasco Mayor & Maria Amparo Imenez Ivars (Eds.), Interpreting Naturally—A tribute to Brian Harris (pp.103-122).Bern: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Berk-Seligson, S. (1990). The Bilingual courtroom: 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ricssion, K., Krapmpe, R. & Tesch-R?mer, C. (1993).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3),363-406.
Gile, D. (1994 ). The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in translation training. In Dollerup,C. and Lindegaard, A. (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2: Insights,aims, visions (pp. 107-11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arris, B. (1977).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translation. Working Papers on Bilingualism, 12, 96-116.
J??skel?inen, R. (2010). Are all professionals experts? De fi nitions of expertise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evidence in process studies. In Shreve, G. M. &Angelone, E. (Eds.),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pp.213–22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Kiraly, D. (2003). From teacher-centered to learning-centered classrooms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Control, chaos or collaboration. In Pym, A. Fallada, C.Biau, J.R. & Orenstein, J. (Eds.), Innovation and E-learning in translator training: Reports on online symposia (pp. 7-31). Tarragona: Universitat Rovira Virgili.
Knapp-Potthoff, A. & Knapp, K. (1987). The man (or woman) in the middle:Discoursal aspects of non-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In Knapp, K. & Enninger,W. (Eds.), Analyz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181–211). The Hague:Mouton.
Lang, R. (1975). Orderlies as interpreters in Papua New Guinea. Papua New Guinea Medical Journal, 18(3), 172-177.
Launer, J. (1978). Taking medical histories through interpreters: Practice in a Nigerian outpatient departmen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77), 934-935.
Mahmoodzadeh, K. (1992).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In Dollerup, C. & Loddegaard, A. (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Training, talent, and experience (pp.231-2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Martinez-Gomez, A. (2015). Non-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In Mikkelson , H. &Jourdenais R. (Eds.) ,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preting (pp.417-431).New York: Routledge.
Marcos, LR. (1979). Effects of interpreters on the evaluation of psychopathology in non-English-speaking pati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6), 171-174.
Meyer, Bernd, Apfelbaum, Birgit, P?chhacker, Franz, Bischoff & Alexandre. (2001).Analysing interprete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health sciences. In Louise Brunette,Georges Bastin, Isabelle Hemlin & Heather Clarke (Eds.), The critical link 3: 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pp.67-79). Amsterdam/Philadelpia: John Benjamins.
P?chhacker, F. (2016).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2n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rice, J. (1975). Foreign language interpreting in psychiatric practic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9, 263-367.
Toury, G. (2001).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Tseng, J. (1992). Interpreting as an emerging profession in Taiwan: A sociological model (Masters thesis).
鮑川運.(2007).口譯的職業化.中國翻譯,(1),50-51.
劉和平.(2011).翻譯能力發展的階段性及其教學法研究. 中國翻譯,(1),37-45.
潘琚、孫志祥、王紅華.(2009).口譯的職業化與職業化發展——上海及江蘇地區口譯現狀調查研究.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6),81-101.
王恩冕.(2004).“口譯在中國”調查報告.中國翻譯,(2),57-60.
徐海銘、柴明颎.(2008).漢英交替傳譯活動中譯員筆記困難及其原因的實證研究——以國際會議職業受訓譯員和非職業譯員為例.外語學刊,(1),122-127.
(責任編輯 邵雪萍)
王炎強,博士、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口譯理論與實踐、口譯教學研究。
作者電子郵箱:yanqiangw@fudan.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