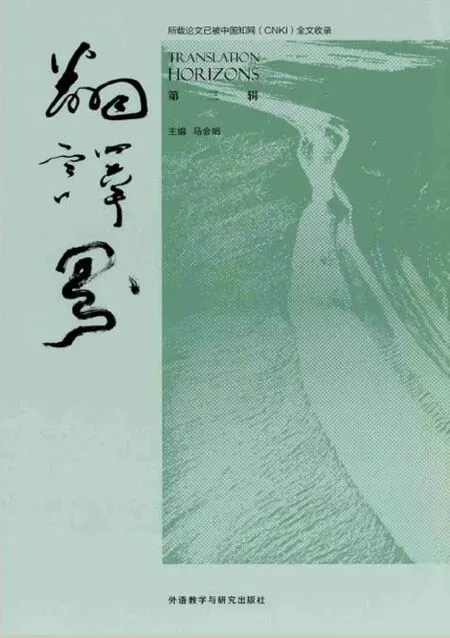漢語詩歌在英國的譯介*
張智中
天津師范大學
漢語詩歌在英國的譯介*
張智中
天津師范大學
自18世紀以來,漢語詩歌被陸續譯介到英國。早期的譯者,主要是長期旅居中國的英國傳教士和外交官,英譯唐詩的影響,迅速擴展到英國的文藝界。兩個多世紀以來,漢詩英譯在英國產生了一些頗具影響力的翻譯家,如理雅各、翟理斯、韋利等,他們成為漢詩英譯的代表人物。二戰之后成長起來的漢學家和翻譯家,如華茲生、斯奈德、宇文所安等,都是美國人,漢詩英譯的中心也相應地由英國轉移到了美國。本文探討漢語詩歌在英國譯介的歷史狀況,重點分析漢詩英譯代表人物的翻譯,并展望漢詩英譯的未來。
漢詩英譯;英國;翻譯家
1.漢詩英譯在英國的發軔
在中國文學中,詩歌占據要津;中國文學的英譯,也從詩歌開始。關于漢詩英譯在英國的早期情況,學術界有不同的論述。吳伏生先生說:“雖然英國從17世紀起便與中國有經濟往來,但與歐洲天主教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相比,英國對中國文化的翻譯和介紹要晚得多。”(吳伏生,2012:1)他接著說,最早翻譯介紹漢詩的英國人,是坡西主教(Bishop Thomas Percy, 1729-1811),他于1761年出版了《好逑傳:一部引人入勝的歷史》(Hau Kiou Choaan, The Pleasing History),參照其他英文和葡萄牙文譯本完成,書中收錄有《詩經》的選譯。(吳伏生,2012:2)但是,根據朱徽(2009:4)的觀點,從16世紀以來,英國就一直在翻譯和介紹中國古典詩歌。查理德·普藤漢(Richard Puttenham, 1520-1601)在《英文詩藝》(The Arte of English Poesie, 1589)中討論英文格律的時候,譯介了中國古詩。這是我們迄今見到的漢詩英譯的最早記錄。顯然,關于英國最早的漢詩英譯,兩個學者的觀點,相差了近兩個世紀。
不過,他們的一個共識是:“英國傳教士和外交官在漢詩英譯方面做出了具開拓性的歷史貢獻”(朱徽,2009:1)。長期旅居中國的英國傳教士和外交官,開啟了唐詩英譯的先機,并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他們的譯文瑕瑜互見,遠未達到完美的境界。一經發軔,英譯唐詩的影響,便迅速擴展到英國的文化藝術界。(江嵐,2009:295)吳伏生認為,維斯頓(Stephen Weston, 1747-1830)是漢詩英譯的先行者之一,但他不太懂漢語,譯文中出現不少的錯誤。不過,“在唐詩西傳的起步階段,更值得肯定的,是這些漢學家們付出的努力所具有的歷史價值”(江嵐,2009:82)。18世紀歐洲人所知道的漢語詩歌,不是被中國人所推崇的陶淵明、李白、杜甫等詩人的杰作,而是當時在位的乾隆皇帝的詩篇。(吳伏生,2012:3)這正說明了當時的英國人,對中國詩歌何其缺乏了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除了《詩經》之外,漢詩被翻譯成英語的,都不是中國詩歌的代表作。直到1887年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帕克(E. H. Parker)翻譯了一些李白和杜甫的詩,1888年漢學家愛德金斯(Joseph Edkins)翻譯了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李白等人的詩,才標志著英國人對漢詩的興趣,不再局限于《詩經》和里巷歌謠。(吳伏生,2012:18)
2.漢詩英譯在英國的延伸與發展
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在華多年,漢語功底較深,著述頗豐。他對中國詩歌的認識,可以說是代表了英國當時的最高水平。(吳伏生,2012:9)1870年,戴維斯出版《漢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一書,介紹中國詩歌的總體情況,揭開了唐詩向英語世界傳播的大幕。(江嵐,2009:8)“從19世紀末開始,一百多年來,唐詩的譯介和研究在英語的文化語境中,走過了一條由隨意、零散、寬泛到系統化、專門化的道路。”(江嵐,2009:295)“此后,唐詩的譯介得到了一些熱愛中國古典文學的英國漢學家們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關注……逐步搭建起唐詩英譯由零散、隨意向系統、專注的方向發展過渡的橋梁。”(江嵐,2009:8)“這些漢學家們都是唐詩西傳先行者,他們對唐詩作品,對唐代詩人及其所秉承的文化傳統的了解和介紹,以及他們自身絕非泛泛的英文詩歌創作功底,使唐詩的篇章在他們的譯筆之下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也使得李白、杜甫、陳子昂、張九齡等著名唐代詩人,先于唐詩這個詩學整體而被英語世界所認知和了解。”(江嵐,2009:82)
于是,在英國的漢詩英譯界,出現了理雅各、翟理斯、戴維斯,他們被并稱為“19世紀英國漢學的三大代表人物”(江嵐,2009:8)。進入20世紀后,“1916年,英國第一個涉及中國研究的專門機構‘東方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成立,標志著英國的漢學研究有了重大發展”(江嵐,2009:8)。這時,漢詩英譯在英國的高潮,也就到來了。這時,從事漢詩英譯的英國人逐漸增多。在戴維斯的基礎之上,繼往開來,將漢詩英譯乃至漢學研究帶進英國學術殿堂和文化主流的,便是理雅各和翟理斯。(吳伏生,2012:17)一個多世紀以來,英國譯者的漢詩英譯持續進行,范圍逐漸擴大,數量逐漸增多,質量不斷提高。
“20世紀20年代以前,唐詩譯介及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還處在起步的階段。”(江嵐,2009:14)這一階段唐詩英譯的特點,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譯介者主要由傳教士和外交官出身的早期漢學家組成。他們多在中國長期生活,精通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對唐詩及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的認識。第二,漢詩英譯的歷史進程由寬泛到專門,由隨意到系統。翟理斯為唐詩西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唐詩英譯由零散、隨意發展到系統、專注的過渡階段的代表。第三,唐詩的影響,向漢學研究領域以外傳播。在20世紀的頭20年里,唐詩已經開始從漢學研究領域向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從精英圈向民間開始傳播。第四,譯介者對東方文化抱有接近和了解的善意。這些早期漢學家的翻譯工作,不但普遍受到語言障礙的挑戰,同時也受到語言所攜帶的文化因素的制約。(江嵐,2009:14-20)
唐詩英譯起步階段在英國出版的重要文本,都很快流傳到美國,其重心從20年代初開始逐漸轉移到美國。(江嵐,2009:157)其中的一個原因在于:英國政府對于漢學研究的急功近利的態度,致使有志于傳統漢學研究而又頗有建樹的學者,紛紛轉向美國去發展。(江嵐,2009:281)唐詩英譯到了進深階段之后,重心也就從英國轉移到了美國。“他們的西方文化素養,以及由美國注重跨學科訓練的學術傳統所形成的研究方法,讓他們往往能夠將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理論應用于漢學研究。他們自身不受中國傳統思想束縛的研究立場,也使得他們關照中國傳統文化的視野更加開闊,辨析、思維的角度更加自由。”(江嵐,2009:281)不過,漢詩英譯在美國的具體情況,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討論范圍。
3.漢詩英譯在英國的幾個重要譯者
漢詩英譯在英國,數個世紀以來,產生了一些頗有影響力的翻譯家,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不太出名的譯者。例如,1925年,艾倫·李(Alan Simms Lee)在倫敦出版了《花影:中國詩譯集》(Flower Shadows: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翻譯的質量一般,所產生的影響也比較有限。(江嵐,2009:253)再如,英國劇作家、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克里弗·巴克斯(Clifford Bax, 1886-1962)先后出版過《中國詩歌20首》(Twenty Chinese Poems, 1910)和《中國詩歌25首》(Twenty Five Chinese Poems, 1912)兩本譯著。(江嵐,2009:83)這兩本單薄的小書,雖然當時頗有知名度,但卻遠不如弗萊徹、翟理斯、韋利等人名氣大。另外,1920年,翻譯家愛德華·馬瑟斯(Edward Powys Mathers, 1892-1939)出版了其編譯的《清水苑:東方情歌120首》(The Garden of Bright Waters:One Hundred and Twenty Asiatic Love Poems),書中收入阿富汗、日本、柬埔寨、緬甸、印度、中國等國家的愛情詩歌,地域跨度和年代跨度都很大。(江嵐,2009:108)更具影響力的,是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愛德金斯(Joseph Edkins, 1823-1905)、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36)、克萊默–賓(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 1872-1945)、威廉·弗萊徹(William John Bainbrigge Fletcher, 1879-1933)等,下面分而述之。
戴維斯認為,英譯漢詩時,應該用英詩中的一個音步(foot),而不是一個音節(syllable),來對應漢詩中的一個漢字。這在當時頗具創意,對后代影響較大。(吳伏生,2012:9-10)戴維斯指出,英國人對中國詩歌缺少興趣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譯者的趣味不高,他們翻譯的多是里巷歌謠,翻譯水平也差,從而導致漢詩魅力的喪失。針對這種現象,他建議譯者翻譯漢詩中的優秀作品,并放棄“逐字翻譯(verbal translation)”的方法。他認為,歐洲語言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直譯,因為它們之間有連帶關系。但漢語和英語之間差異巨大,逐字翻譯只能產生笨拙的譯文。因此,他主張以詩譯詩;同時,他也承認在不同場合下,為了不同的目的,譯者不妨采用其他的策略。(吳伏生,2012:10)那么,我們來看一下戴維斯所翻譯的杜甫的《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An Evening Shower in Spring
See how the gently falling rain
Its vernal in fl uence sweetly showers.
As through the warm and tepid eve
It silently bedews the fl owers.
Cloudy and dark th’ horizon spreads,
—Save where some boat its light is burning.But soon the landscape’s tints shall glow
All radiant, with the morn returning.
(戴維斯 譯)(吳伏生,2012:13-14)
研讀品味,只覺譯文偶行用韻,措辭形象,傳神而達意。“戴維斯最反對在譯文中羅列令譯語讀者無所適從的漢語名稱和地名,因為它們會使這些讀者生厭,并最終失去對漢詩的興趣。此處,為了避免這一點,他采用了轉換的方法,用籠統的‘landscape’(大地)來代替特殊的‘錦官城’,使譯語讀者一目了然。”(吳伏生,2012:15)顯然,戴維斯的譯詩主張與專名處理手法,與中國當代漢詩英譯專家許淵沖先生的理念,如出一轍。不同的是,戴維斯的漢詩英譯,不都采用格律韻體。另外,戴維斯將漢詩與西方詩歌進行比較,以便拉近漢詩與英語讀者之間的距離。通過戴維斯的翻譯,英國人對漢詩的誤解得以糾正,漢詩成為在他們中間產生共鳴的文學作品。(吳伏生,2012:17)
愛德金斯在中國度過了57年,從事傳教和譯著工作,最后在上海辭世。他研究興趣廣泛,對中國語言文字、文學和歷史有深厚的了解。著有《中文口語進階》(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1862)、《漢語在語言學上的定位》(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1871)、《中國漢字學習入門》(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1876)、《中國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1893)等20多部漢學研究著作。他還將古典漢語與英語詩歌進行橫向的聯系與比較,例如將李白的詩歌與華茲華斯的詩歌進行比較,這些也屬難能可貴。(江嵐,2009:66-68)漢詩英譯時,愛德金斯有時會對同一首詩,給出兩種譯文。例如李白《淥水曲》及其英譯:
淥水明秋月,南湖采白蘋。
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There where the lake is green
The autumn moon is seen
And water shields are spread
Along the tangled bed
Their leaves are snowy white
Beneath the sun’s warm light
See here the lotus grow
Making a glorious show
Floating in loveliness
And wishing to express
The thought that come to fl owers
But lacking speech like ours
The boatman rowing by
Is sad he knows not why
(愛德金斯 譯)(江嵐,2009:71-72)
譯文雖然每兩行押一韻,卻將原文的4行,譯成了英文的14行。后來,愛德金斯對此詩重新翻譯:
On the green water shines the autumn moon,
Where someone plucks white water shields.
The lotus with its enticing beauty seems ready to speak.
The boatman as he rows is grieved to the brink of despair.
(愛德金斯 譯)(江嵐,2009:73)
譯詩變成了4行,但卻沒有了尾韻。如果說改譯在字面上與簡潔上更接近漢詩的話,原譯在韻律上似乎更忠于原詩。愛德金斯對同一首漢語詩歌的不同翻譯,從一開始就說明了譯者面對漢語詩歌,在翻譯過程中的猶豫不決。而這種猶豫不決,乃是由于譯者不知該忠于原文的哪個方面所造成的。此后一百多年來,漢詩英譯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流派或風格,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英國漢學家愛德華·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36),漢文名莊延齡,是一位勤奮而多產的漢學家,著有《鴉片戰爭中國報告》(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1888),《孔子的生平、工作與學說》(The Life, Labour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us, 1897),《中國和宗教》(China and Religion, 1905)、《中國通史》(Ancient China Simpli fi ed, 1908)等著作。他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對中國歷史和宗教史的研究,也是第一位認真研究中國方言的非傳教士背景的漢學家,他的許多極有價值的方言學觀點近年開始逐漸得到學術界應有的重視。1887年間,莊延齡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雜志的《中國詩歌》欄目連續發表了數首他所翻譯的唐詩。其中,以儲光羲的《田園雜興八首》之“種桑百馀樹”的譯文質量最好,不僅語言親切,格式工整,韻律優美,也傳達出詩人與世無爭的逍遙自得。(江嵐,2009:61-64)原詩與譯詩如下:
種桑百馀樹,種黍三十畝。
衣食既有馀,時時會親友。
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
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
日暮閑園里,團團蔭榆柳。
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
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
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Rustic Content
A hundred mulberry trees I’ve got,
And thirty acres round my cot;
Of food and clothing thus enough,
A friend can share my surplus stuff.
In summer there’s my mess of rice,
In autumn seasoned wine with spice;
The wife smiles welcome in her face,
The young’uns skip about the place.
At sunset take a garden stroll,
Sit chatter on that shady knoll;
When slightly boozy, toddle home,
And doze it off in this cool room.
Where I can watch the Milky Way,
And Great Bear moving towards day;
Still there are sev’ral kegs of yest,
To-morrow we will drink the rest.
(帕克 譯)(江嵐,2009:64)
漢詩16行,譯詩16行;漢詩押韻,譯詩亦然。原詩采用白描的手法,表現詩人的田園之樂,譯詩雙行一韻,內容上雖然稍有出入,卻也保持了原詩清新樸素的語言風格,表現了詩人與世無爭的逍遙自在。
如前所述,英國早期的漢詩英譯者,以傳教士和漢學家為主。但有個別例外,英國詩人克萊默–賓,便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漢學家唐詩譯者。他的譯著,《長恨歌及其他》(The Never Ending Wrong and Other Renderings, 1902)、《宮燈的饗宴》(A Feast of Lanterns: Rendered with an Introduction, 1916)和《玉琵琶》(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 1918),都是在翟理斯等學院派譯家的英譯文本基礎上的改譯。“克萊默–賓不懂中文,只憑著對唐詩的熱愛,反復揣摩意境,取天下人同此心的情懷,把他人的譯文脫胎重寫。”(江嵐,2009:19-20)并使之更加詩意化和大眾化。
可以說,克萊默–賓是以文學創作者的身份,在英、美大力推介唐詩的第一人。他具有推介、傳播東方文化的熱忱,以及力求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善意。他從未到過中國,也不大懂漢語,他的譯作,都是在他人英文或法文譯本的基礎上的重新詮釋和改寫,只能說是“再譯”或“重譯”,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在其1908年的《詩經》譯本中,克萊默–賓說:“偉大的世界文學已經被那些純粹的學者們把持得太久了。對于他們來說,文字至高無上,而精髓則無關緊要。現在已經到了文學家站出來宣布并承擔起責任,去揭示異域文學的真實面貌及其魅力的時候了。”(江嵐,2009:85)雖然克萊默–賓表現出對翟理斯的尊敬,但他對其經院學者式的、精確有余而靈動不足的中國詩詞譯文并不認同。例如兩人對李白《靜夜思》的不同翻譯: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英譯一:
Night Thoughts
I wake, and moonbeams play around my bed,
Glittering like hoar-frost to my wandering eyes;
Up towards the glorious moon I raise my head,
Then lay me down — and thoughts of home arise.
(翟理斯 譯)(呂叔湘,2002:136)
英譯二:
Thoughts in a Tranquil Night
Athwart the bed
I watch the moonbeams cast a trail
So bright, so cold, so frail,
That for a space it gleams
Like hoar-frost on the margin of my dreams.
I raise my head, –
The splendid moon I see:
Then droop my head,
And sink to dreams of thee –
My fatherland, of thee!
(克萊默–賓 譯)(呂叔湘,2002:137)
比讀可知,翟理斯的翻譯,以4行譯4行,交叉押韻,是典型的韻律翻譯,雖然個別字詞稍有改動,但基本忠實于原文的內容。細讀克萊默–賓的翻譯,“微光如秋霜凝在夢的邊緣”(Like hoar-frost on the margin of my dreams)是相當富有浪漫氣息的添加,可惜無論是在李白原詩還是在翟理斯的譯文中,“夢”這個詞都沒有出現過。末句“祖國”這個詞又是憑空添加的,結果錯誤地將整首詩原本感慨客況蕭條、思鄉思親的秋夜旅懷轉換成迥然不同的內涵和境界。(江嵐,2009:101)
“克萊默–賓既然讀不懂原文,他重譯時便無從講求和原詩的對照,因此在譯詩的語言處理上,他的發揮余地更大,他甚至習慣于把自己的想象和情緒加入到原詩中去。在他看來,唐詩是如此浪漫,如此豐美,他只能用同樣唯美和浪漫的情調來詮釋。”克萊默–賓的“西化的唐詩”比“直譯的唐詩”更易于被普通的民眾所理解、所認可。(江嵐,2009:91-94)因為他更加注重詩性的、浪漫唯美的感染力。總之,“推動英譯唐詩走出學術界精英圈,被更廣大的英語世界范圍的讀者所喜愛和接受,是克萊默–賓對唐詩西漸最偉大、最直接的貢獻。”(江嵐,2009:108)
威廉·弗萊徹于1919年出版第一本斷代唐詩英譯專著《英譯唐詩選》(Gems of Chinese Verse);1925年,他又出版了《英譯唐詩選續集》(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兩本書,共譯出唐詩286首。“弗萊徹借此成為向英語世界專門譯介唐詩的第一人,他以對唐詩大量而較為系統的翻譯,成功地完成了唐詩譯介從零散到系統的過渡。”(江嵐,2009:9)“在弗萊徹看來,唐詩不僅給人帶來閱讀的快感,更充滿生命的啟迪……所以,他必須要把這些優美的詩篇呈現給西方的讀者,希望讀者們能夠通過他的譯筆,與唐代詩人們一起泛舟于長江之上,踏月于山寺之中,從而領略到唐詩真正的普世價值,找到生命中真正的寧靜與和諧。”(江嵐,2009:140)下面是金昌緒的《春怨》及其英譯: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A Lover’s Dream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ro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d to me.
(弗萊徹 譯)(呂叔湘,2002:136)
“不得到遼西”,英文以My lover smiled to me(我的愛人向我微笑)來譯,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在忘記字面上的“背叛”之后,若讀者仔細玩味詩語之內的含義,可以感到,譯文與原文,在詩意上正是相吻合的。“弗萊徹明快、簡練而又不失典雅的英譯唐詩風貌,得到了讀者的喜愛,其影響一直持延續至今不衰。”(江嵐,2009:152)
至于弗萊徹英譯唐詩的特色,江嵐總結如下:第一,與翟理斯的翻譯風格大體近似,都用詩體,而且都押韻。弗萊徹譯詩的閱讀對象,是普通讀者,因而更注重譯文的可讀性。第二,以韻體直譯為主。他的譯文中很少出現因韻害義的情況,他譯文的語言風格,比學術性譯文更親切,比創造性譯文更準確,這是他的譯文能在漢詩英譯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第三,直譯注重傳達原詩意。有時,他的譯文不拘泥于與原文字面上的機械對應,而是將他所理解的唐詩的詩意,用貼近英國讀者審美習慣的語句表達出來,這是弗萊徹譯文的一大特色。(江嵐,2009:142-145)
4.漢詩英譯在英國的代表性譯者
漢詩英譯在英國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理雅各、翟理斯、韋利等。下面分而述之。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可謂是西方漢學界的奠基人物之一。他所翻譯的中國文化典籍多達數十部,幾乎囊括了整個儒家與道家經典。1876年,牛津大學任命理雅各為歷史上第一位中國語言文學教授,他在此教職耕耘了20多年,直到1897年去世。這20年間,他是西方漢學界的泰斗,此間的西方漢學史,被稱為“理雅各時代”。(吳伏生,2012:21-22)
理雅各所翻譯的漢詩,主要有《詩經》(The Shi King),1871-1872年在香港出版,是《中國經典》的第四卷,也是《詩經》的第一部完整的英文譯本。理雅各的翻譯,一向以準確著稱,他的注釋之詳盡,令人敬佩。因此,他的翻譯,是學術翻譯——而非文學翻譯——的典范。(吳伏生,2012:26,29)理雅各心中的讀者,是專業的學者,而不是普通讀者,因此,他的譯文往往拖泥帶水,準確有余而生動不足。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關雎》第二節的翻譯: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Here long, 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理雅各 譯)(吳伏生,2012:35)
“上面所引的譯文不但參差不齊,而且大量運用句中標點,使其在節奏上顛簸緩慢,與原詩明快流暢的效果截然不同。”(吳伏生,2012:35)這樣一來,譯文雖然比較忠實地傳達了原文的內容,卻喪失了原文的耐品耐味的美學內涵。
“理雅各的翻譯曾被稱為‘parenthetical’(括號式),亦即‘詮釋型’翻譯。這不僅因為他為其譯文提供了大量注釋和題解,還因為他在譯文中使用了很多括號和說明性的詞語,以幫助讀者理解原詩的含義。”(吳伏生,2012:55)理雅各的《詩經》(The Shi King),于1871-1872年在香港出版約五年之后,即1876年,他又出版了韻體版的《詩經》英譯本。“當初為《中國經典》叢書翻譯《詩經》,理雅各心中的讀者是具備中文能力的學者和專家。此次他翻譯韻體《詩經》,所針對的對象是一般的‘英語讀者’(English readers)。”(吳伏生,2012:66)但是,人們喜歡的,還是他所翻譯的散體《詩經》。繼理雅各之后,英國漢學界的領銜人物是翟理斯。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當時西方漢學界的地位,不亞于理雅各。“由于他的著作涉及中國語言文化的各個方面,他的影響也相對要大得多。”(吳伏生,2012:104)翟理斯譯有《聊齋選譯》(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1880),《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4),《中詩英韻》(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1898),《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01),《中國繪畫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1905),《中國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1911),編有《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中文自學課本》(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等。
不同于理雅各,翟理斯翻譯的對象,不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專家與學者,而是那些對中國語言文化所知甚少或一無所知的普通讀者。因此,通俗性是翟理斯翻譯的主要特征。“他的漢詩翻譯,不僅數量很多,而且風格上自成一體,也常常因為不同原因為后人所追念。”“翟理斯認為,無論英譯漢還是漢譯英,譯者都應該盡量避免直譯,而是要采用在譯語中通順流暢的詞語和文體。只有這樣,才能使譯文避免佶屈聱牙、令讀者厭惡。也就是說,要對原文進行歸化,以使其易于為讀者接受。”(吳伏生,2012:107,117)顯然,翟理斯的翻譯,是歸化的韻體翻譯的典型。下面是王維《雜詩·其二》及其英譯: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Sir, from my dear old home you come,
And all its glories you can name;
Oh, tell me, —has the winter-plum
Yet blossomed o’er the window-frame?
(翟理斯 譯)(江嵐,2009:48)
“把翟理斯的英譯文本再翻譯成中文,差不多就是王維原作的白話文改寫。而且譯詩行文的風格也和原詩一樣,以不加修飾的白描記言手法,用很省凈的筆墨一氣呵成,將原詩中主人公久羈異地,忽遇相親的感情、神態、口吻都再現得十分生動,堪為唐詩英譯中的佳作。”(江嵐,2009:48)那么,我們不妨來看一下這首詩的白話文改寫之一:
先生你從故鄉到來,
一定知道故鄉的事態。
你來時可見我家的窗前,
那株冬梅花兒開沒開?
(袁遠,1992:473)
和白話文改寫之二:
您是打從故鄉那里來,
一定會知道故鄉的事。
來時我過去臥室窗前,
寒梅是否綻開了花蕾。
(鄭竹青、周雙利,1999:1344-1345)
比較可知,翟理斯的譯詩與兩種白話文改寫或曰今譯,在風格上何其相似。不過,在漢詩英譯之時,翟理斯的翻譯策略是比較靈活的。比如,“翟理斯全文翻譯了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兩首長篇名作,即《琵琶行》和《長恨歌》。所不同的是,這兩篇譯文都沒有用韻,而且在翻譯《琵琶行》時,翟理斯甚至采用了散文體。”(吳伏生,2012:149)另外,“翟理斯的漢詩翻譯不僅僅局限于古代名篇,也包括一些不見經傳以及當時發表的作品。這與他的漢學研究及翻譯中的通俗化傾向不無關聯。”(吳伏生,2012:169)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對中國及其文化存有許多偏見和誤解。翟理斯以清除這些偏見和誤解為己任,不斷強調中西文化的相通之處。他漢詩翻譯中的歸化傾向,便是糾正西方對中國妖魔化的一種策略。但是,在這當中存在著另外一種風險。翟理斯的某些翻譯不僅在形式上看不到原詩的痕跡,而且在內容上甚至成了西方文化理念的說明和體現。”(吳伏生,2012:135)例如,有時他以“God”來翻譯漢語詩歌中的“天”;有時還在其譯文中引用《圣經》中的話作為譯文的標題,這些都是出于為譯文讀者的考慮,是歸化翻譯的典型策略。
另外,1918-1922年,翟理斯與當時尚還年輕的阿瑟·韋利就漢詩翻譯展開了一場爭論。然而,“翟理斯與韋利的這場爭論并沒有使漢詩翻譯更上一層樓。雙方,尤其是翟理斯,對彼此的翻譯在細節上錙銖計較,相互指責,力圖壓倒對方,而不是就漢詩翻譯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做深入的探討。”“翟理斯常常被當作漢詩翻譯中舊式風格的典型。倒是韋利的翻譯更能迎合現代讀者的口味,并成為20世紀漢詩英譯的楷模。”(吳伏生,2012:192-193)因為翟理斯的譯文,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風格,韋利的譯文,卻是當代英語的文學風格。
韋利(Arthur D. Waley, 1889-1966)其實是翟理斯的學生。“1918年,年僅29歲的韋利出版了《漢詩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一書。這是繼翟理斯《中詩英韻》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漢詩選集。”“20世紀期間,韋利對漢詩英譯的貢獻之大、影響之深可謂無與倫比。自從1917年他的《漢詩一百七十首》問世以來,無數西方讀者便通過他那清晰流暢的翻譯來接觸和認識中國詩歌及其文化。”(吳伏生,2012:172,194)韋利的主要譯著,還有《道德經》(The Way and ItsPower, 1934)和《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1938),并著有《中國古代的三家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39)。
韋利的譯詩,主要采用直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認為通過直譯,譯者可以在譯文中再現漢詩的基本節奏,而且在韋利看來,詩歌的節奏便是詩歌的魅力所在。他反對用韻,因為在他看來,由于漢、英兩種語言之間的區別,根本無法在英語中復制出漢詩的韻律,尤其是與英詩經常換韻不同,漢詩常常通篇使用一個韻腳。另外,韋利還認為,在譯詩中使用韻腳,往往或是削弱了譯文的活力,或是傷害了譯文的直譯效果,古往今來,無一例外。(吳伏生,2012:214-216)下面是《古詩十九首》組詩中的第二首及其英譯:
青青河畔草,郁郁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Green, green,
The grass by the river-bank,
Thick, thick,
The willow trees in the garden.
Sad, sad,
The lady in the tower.
White, white,
Sitting at the casement window.
Fair, fair,
Her red-powdered face.
Small, small,
She puts out her pale hand.
Once she was a dancing-house girl,
Now she is a wandering man’s wife.
The wandering man went, but did not return.
It is hard alone to keep an empty bed.
(韋利 譯)(吳伏生,2012:230-231)
“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纖纖”,構成六組疊字。但是,“由于英語中沒有這種修辭手段,因此翻譯起來比較困難。為了在譯文中充分體現原詩的風格,韋利此處完全采用了直譯的策略。他甚至將原詩中的前六行每行分別譯成兩行,把疊字詞組單獨排列,以便突出它們的作用。韋利的漢詩翻譯一向以行文流暢著稱,這六行的翻譯卻有意給人以支離的感覺。”“所有這些都表明,在翻譯這首詩時,韋利不僅僅力圖傳達它的內容,而且還要向讀者再現它的藝術風格。為此,他不惜犧牲譯語的傳統與習慣,讓讀者向原詩靠攏。一般來說,韋利的漢詩翻譯多采用歸化原詩的策略。但是,他這首詩的譯文卻表現出了用原詩改變譯語的異化傾向,因此尤為引人注目。”(吳伏生,2012:231-232)
在其翻譯中,韋利偏愛詩風淺近,簡潔明了的詩篇,他選譯的多是這一類風格的唐詩作品。因此,在中國古代詩人當中,韋利對白居易情有獨鐘。1949年,他出版了白居易的傳記《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向西方讀者全面介紹白居易。 “韋利先后譯出白居易各體詩文總計超過200余首,白詩研究構成了韋利譯介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專門方面。”(江嵐,2009:19)“韋利選詩的標準和他自己的語言風格,決定了他譯文的淺白如話。讀他的譯詩,即使沒有原文對照,也用不著苦思冥想,馬上可以將譯文和原文聯系起來。”(江嵐,2009:115)例如白居易《舟中讀元九詩》及其英譯:
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
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
On Board Ship: Reading Yuan Chen’s Poems
I take your poems in my hand and read them beside the candle;
The poems are fi nished: the candle is low: dawn not yet come.
With sore eyes by the glittering candle still I sit in the dark,
Listening to waves that, driven by the wind, strike the prow of the ship.
(韋利 譯)(江嵐,2009:123)
“韋利的英文文本對原詩幾乎沒有做什么改動。他用英文重音來體現唐詩中的每個漢字發音效果,雖不用韻,詩句抑揚、輕重的音節處理卻很自然,文字清淡準確,尤其是將‘燈’字譯成‘蠟燭’而非英文的‘light’,十分傳神地再現了白居易當時所處的環境,襯托出他的孤獨寂寥之狀,傳達出白居易這一首平淡中見神韻的傳世名篇中,詩人心與物會,情與景合的孤清境界。”(江嵐,2009:125)再如李白的《自遣》及其英譯:
對酒不覺暝,落花盈我衣。
醉起步溪月,鳥還人亦稀。
Self-Abandonment
I sat drinking and did not notice the dusk,
Till falling petals fi lled the folds of my dress.
Drunken I rose and walked to the moonlit stream,
The birds were gone, and men also few.
(韋利 譯)(江嵐,2009:133)
小詩《自遣》,深婉而有余味;韋利的譯文,流暢、清新,而不失可愛。韋利認為,譯詩的“忠實”,不僅僅是對原詩歌字詞的翻譯,而是再現詩歌的美感。翻譯不應該加入譯者自己的想象,也不應該因湊合韻腳或其他原因而任意更改原詩的內容或損害譯文的藝術感染力。他堅持認為,傳統英語格律體詩歌的押韻規則,實際上無法再現中國詩歌的韻律。他具有獨創性的譯詩風格,擴展和豐富了唐詩在英語世界主流文化中的應用范圍和解讀方式。(江嵐,2009:111)“韋利深信自己韻律化的譯作逼肖原詩,雖不押韻,卻注重詩歌的整句頓挫和意象完整,即使譯文中出現一些小的錯誤,也不會妨礙全詩意境的完整性。”(江嵐,2009:123)以小詩《自遣》的英譯驗之,信然。“韋利對白居易和李白的研究,強有力地推動了西方唐代詩人專門研究的系統性和學術性。”(江嵐,2009:137)
另外,韋利英譯的《詩經》(The Book of Songs)不但常常為專家學者所引用,也成為西方讀者最為熟知和喜愛的譯本。(吳伏生,2012:310)“韋利的漢詩翻譯兼顧專家學者和一般讀者的需求與興趣。它不僅僅贏得了漢學界的認可,同時也把中國詩歌介紹給廣大的西方讀者。他在這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沒有人能夠與他媲美。”(吳伏生,2012:318)
作為一名勤奮多產的學者,韋利共著書40種,翻譯中、日文化著作46種,撰寫文章160余篇。(江嵐,2009:110)“1953年,韋利因介紹東方詩歌成績卓著,榮獲20世紀英聯邦國家詩歌界最高榮譽,英國女王詩歌獎(Queen’s Medal for Poetry)。”(江嵐,2009:135)“韋利以其在英、漢語言文學方面的高深造詣,用忠實流暢、力求忠實于原典的譯筆,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肯定和喜愛,成為繼翟理斯之后,在歐美漢學界推動唐詩譯介最為得力的著名漢學家。同時,韋利對所譯作品的透徹了解和見解獨到的研究,給西方讀者提供了另外一個觀照唐詩的視角;他對中國古詩譯介的高度熱情,大大增進了英語世界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推動了唐詩西傳的歷史進程。”(江嵐,2009:136)
5.漢詩英譯的前景展望
翟理斯培養了漢學家韋利,韋利又培養了下一代漢學家,如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白之(Cyril Birch);因為霍克斯和白之的翻譯,不以詩歌為主,這里暫時略而不論。“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性,使得這些漢學家們在西方語境下對唐詩的詮釋,必然帶有他們自身文化傳統的烙印。”(江嵐,2009:81-82)從戴維斯到愛德金斯,從莊延齡到克萊默–賓,從威廉·弗萊徹到理雅各,從翟理斯到韋利,概莫能外。不過,若總結漢詩英譯的方法,不過三種而已:一曰直譯,一曰意譯,一曰創譯。三種方法,也只是譯文離開原文的距離不同而已:直譯的距離最近,意譯的距離稍遠,創譯的距離最大。當然,這只是就譯文與原文的語言差異而言。與此同時,在詩意方面,說不定若采用直譯的方法,譯文與原文之間的距離,反倒最大;若采用意譯或創譯的方法,譯文與原文之間的距離,反倒最小。凡此等等,不可一定。
二戰之后成長起來的漢學家和翻譯家,如華茲生(Burton Watson),斯奈德(Garry Snyder)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都是美國人,繼續為漢詩英譯做出重大貢獻。這時,漢詩英譯的中心,也相應地由英國轉移到了美國。“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持續增強,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漢學或中國研究領域在西方再次成為熱門學科。”(江嵐,2009:299)
可以預言,未來的漢詩英譯,在英國也好,在美國也好,都會有著較好的前途。而且,人們對于翻譯的質量,也有著更高的要求。其實,漢詩英譯的譯者,幾十年來,已經出現一種新的合作方式,即中外譯者合作翻譯。當代漢詩的譯者、英國漢學家霍布恩(Brian Holton, 1949- )說:“我一直都這么認為,要想提高漢英文學翻譯的質量,唯有依靠英漢本族語譯者之間的小范圍合作。漢語不是我的母語,我永遠無法徹底理解漢語文本的微妙與深奧;反之,非英語本族的譯者,要想將此類內涵豐富的文本翻譯成富有文學價值的英語,且達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絕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協力,何患不成?”(霍布恩,2007:638)
其實,在當前的語境下,即便是獨立的譯者,也產生了一些變化。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譯者也加入了漢詩英譯的行列,打破了以往英美譯者“風景這邊獨好”的狀態。于是,在獨立譯者中,有英美的獨立譯者,也有中國的獨立譯者。獨立翻譯也好,中外合作翻譯也好,只要能出翻譯精品,就是好的翻譯。“唐詩的美學理想能夠為現代西方世界所認知和接受,并在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中,有效促進多元文化的互補、互證與相容共生。”(江嵐,2009:296)若將這段話中的“唐詩”改為“漢詩”,則話語同樣有效。未來漢詩英譯的局面,一定是英美譯者、中國譯者、中外合作譯者同生并存的,而且,這種局面將長期維持下去。
霍布恩.(2007). 駛向天堂的碼頭——楊煉長詩《同心圓》譯后記. 載于海岸(選編),中西詩歌翻譯百年論集(631-638頁).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江嵐.(2009). 唐詩西傳史論——以唐詩在英美的傳播為中心. 北京:學苑出版社.
呂叔湘.(2002). 中詩英譯比錄. 北京:中華書局.
吳伏生.(2012). 漢詩英譯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韋利、龐德. 北京:學苑出版社.
袁遠.(1992). 唐宋名詩新譯(上).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鄭竹青、周雙利.(1999). 中國歷代詩歌通典(中卷).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朱徽.(2009). 中國詩歌在英語世界——英美漢學家漢詩翻譯研究.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責任編輯 趙云龍)
* 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漢語詩歌在英語世界的譯介研究”(項目批準號:16BWW012);天津市2015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重點項目“漢詩英譯風格流派研究”(項目編碼:TJWW15-006)和2014年度國家教育部項目“倉央嘉措詩歌研究:譯介、傳播與比較”(項目批準號:14YJC740075)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張智中,天津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漢詩英譯。
作者電子郵箱:zzzpoetr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