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返與現實的勾連
——讀劉繼明的《人境》
陳若谷
歷史的回返與現實的勾連
——讀劉繼明的《人境》
陳若谷
劉繼明成書于2016年,長達50余萬字的長篇小說《人境》,厚重、凝練,精準地掃描了鄉村與城市中各個階層和行業的人群的精神面貌,聚焦當代中國面臨的各項議題,關照我們自身難以割斷的歷史根源,表達出當代知識分子對于歷史和現實正面強攻的勇氣。
《人境》講述了主人公馬垃和慕容秋近四十年的歷史,隨著二人的視角變化,小說背景也在進行著南北跨越和城鄉位移。時光漫漫,人的生存形態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移動,而代際之間也橫亙著難以逾越的鴻溝——老一輩革命者辜烽和農村基層干部大碗伯在悲嘆中離開了這個讓他們日益感到陌生和困惑的世界;曾經同行的熱血伙伴,比如慕容秋、潘小蘋和陳光則在具體的物質生活分裂中走向了南轅北轍的思想領域;年輕一代的小拐兒和唐草兒,懵懂落地,在愛和理想的缺失中承受著來自血緣至親的傷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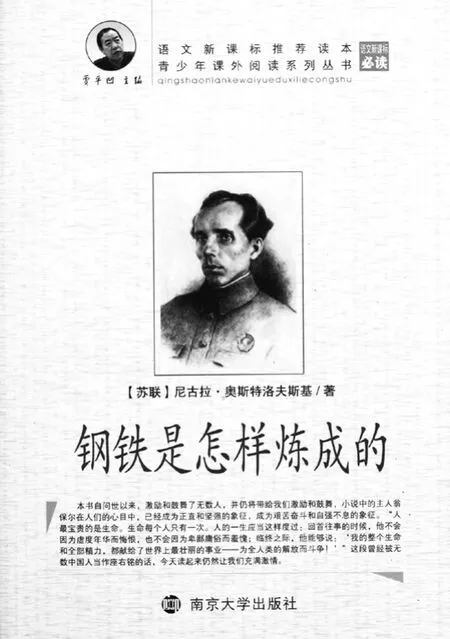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小說所描述的主要場景是農村和工廠,鄉土的精神氣質正在被空心化侵蝕,而城市的工業污染又在損毀人類的生態家園,老舊國有企業改制則釜底抽薪般地剝奪了工人群體的生存權利,也澆滅了他們最后的尊嚴。這一系列錯綜復雜的社會變遷中,真正的贏家是這群人:以辜朝陽為代表的資本買辦和他背后的跨國利益集團、革命后代投機分子丁友鵬和只手遮天的顯貴“紅二代”二公子,以及為達私利甘于茍且的學界官僚,比如W大學社會學系岳書記……在這些陰影的下面,則是被侮辱和損害的弱勢群體、被遺忘甚至嘲諷的英雄主義、被漠視和被揶揄的真誠情誼。當作者將鏡頭對準縣政府前群情激奮的示威人群和為獨立新聞網站“民生網”艱難奔走的曠西北時,他的雄心顯然是想把小說作為參與當代社會進程和公眾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徑;我們也看到作者的筆觸常在“比朝霞還要絢爛,比火焰還要璀璨”的紅花草上流連,也不吝篇幅,將小拐兒看到馬垃有力地劈波斬浪時想到自己逝去的父親而悄悄泛紅的雙眼定格在沉靜的江岸上,這種藝術能量又為這部沉重的《人境》添加了溫情,情感的充沛顯然溢出了嚴整的思想概括力,使得文本的氣韻更加豐沛,充滿了內在的張力。
一、分裂的時代和主體
主人公馬垃被母親和哥哥馬坷一路拉扯大,幼時從洞庭湖邊逃難到荊江邊的神皇洲安家,兄長在一次意外中因為秉持的集體主義信念而獻出生命后,馬垃又在沿河師范學院遇到了精神偶像逯永嘉,畢業后即投身教育事業,經歷了愛情夭折意氣消沉的馬垃即刻動身,與老師逯永嘉南下闖蕩商海。好景不長,老師的死、生意的失敗和巨大的精神幻滅,都迫使馬垃重返神皇洲,在摸索中步步開創他理想中的鄉村建設事業。作為一個同時活在歷史和社會里的人物,外部的現實聲音和深層的記憶情感常常交替著占據馬垃的內心。他帶著坐過牢的印記回到神皇洲村,無情的荊江洪水又徹底沖垮了他才開辟出來的大米、果樹等農產實業;另一些時候馬垃則是成功的,他種獼猴桃,辦“同心合作社”,通過網絡賣生態大米,組織村民抗擊洪水,引導和挽救落后青年,深受父老鄉親敬重。但這樣一個戰士般的,站立在神皇洲歷史中心的人,卻始終處于一種搖擺之中,震蕩在隱晦的邊緣和顯赫的中心之間。而隱晦的邊緣是他心里埋藏的兩個人——他的精神之父,兄長馬坷和老師逯永嘉。
馬坷是一位成長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新人”,像梁生寶和蕭長春那樣,他公而忘私,為搶救集體財產獻出了生命。具有象征意義的是,隨著馬坷的“犧牲”,那個轟轟烈烈的時代也結束了。馬垃徹底地成為了一個血緣情感和價值認同雙重意義上的孤兒。逯永嘉適時出現,他在馬垃如饑似渴接受新知的時刻扮演了一個啟蒙者的角色,他崇尚個人自由,希望在自由之境中永恒穿梭,即便懷孕了的戀人是標準的“白富美”,他也拒絕婚姻的束縛,他還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企圖以龐大的財富在現實社會中建立一個純粹“理想國”,是一個集理想主義與實干能力于一身的現代英才。他身上充滿強者的氣質,毫不掩飾人性的欲望,這樣一個“卡里斯瑪”式的人物卻隕落在事業失敗之際。馬坷和逯永嘉,一個代表了“革命中國”的激情和宏大,另一個是“發展中國”解放個性的啟蒙化身。馬垃最終也將逯永嘉的一半骨灰埋在了那片水杉林邊,與哥哥的墓挨著,“這兩個原本素不相識,而且完全不同的人,如今卻相伴在了一起”,兩個精神之父在馬垃身上遺留的印記相互交疊與沖撞,你消我漲此起彼伏地浮現,并在時代劇變的碰撞中為他編織了新的困惑。被分裂撕扯的馬垃在短暫的茫然中回到神皇洲村,因為他需要可能非常漫長的時間來消化這種激烈的辯論,也就是說,他需要在發展的整體社會空間里慢慢消化啟蒙理想和革命英雄主義的遺產。他對馬坷和逯永嘉的種種回憶也就在這個意義上進行了回返式的對話。
眼下,以歷史“連續性”為背景的現實主義文學,常常使作家在書寫中捉襟見肘。因為彼此沖突的并非僅僅是觀念,更是種種社會與政治力量。“改革”和“發展”最初是對革命的替代,二者的承諾本是相似的。在馬坷成長的時期,“勞動”作為歷史實踐在改造著勞動主體的同時,也在改造外在世界,勤奮的勞動和正直的智慧仿佛就足以撬動世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在被詢喚。而上世紀90年代的開啟,讓單獨個體的能動性越來越弱。丁友鵬、辜朝陽暢行無阻的時代,平凡人變得越來越渺小,腳踏實地幾乎成為了弱者無可奈何的選擇,老一輩人無奈地感應到人心不古,大碗伯被大水逼到河口鎮臨時安置點以后,念念不忘的是死后要葬在神皇洲,之后,他的老伙伴,那只充滿懷舊氣息的矮腳狗“‘社員’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其實,馬垃與大碗伯一樣,急切地要回到那個“業已從現實世界消失,卻完好無損地保留在他的記憶深處的世界”,這種想徹底與當代現實剝離的厭倦情緒是“革命中國”到“發展中國”的精神落差造成的,這難以化解的腫瘤,讓當下中國處在嚴重的階層分裂和價值撕裂之中。
思想界的分歧在意識形態之爭中凸顯,前后兩個“三十年”的社會價值不同,前一個是人民在艱難困苦的生產活動中奪取自主權和管理權,后一個則是普通人在日益豐富的物質發展中步步后撤和下沉,正如正直善良又年輕力壯的谷雨這樣看待自己的價值:“如果在城里,他只不過是一個比稻草還要輕的民工,跟一只螞蟻和一條狗差不多,就是死了也不會有人撩一眼……”。正是由于這種悖論和反差,才導致一度喑啞的社會主義思想重新發聲。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或許是重新梳理歷史的脈絡,重新定義現實。因此,鐵板一塊的講述不可能順利推進,我們只有通過兩種力量此起彼伏的閃現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復雜的馬垃和這個時代。《人境》講述的無疑是當代中國的故事,而當代中國本身就是分裂的——無論是階層的分裂還是道德的分裂。
二、彌合分裂的兩種路徑
《人境》文本并沒有因為社會價值的分裂而變得塊壘分明難以磨合,主人公馬垃也并沒有因為兩種思想的交鋒而長久地局促和失措。劉繼明彌合分裂的方式有兩個,首先是回歸到倫理,把一個現實難題予以道德和情感化清理,比如馬垃對于唐草兒的精神收編。逯永嘉的歷史債務竟然也是歷史的遺產,他留下的女兒唐草兒,在這個世外桃源般的果園里,逐漸抖落了舊日的陰霾,走向了健康光明的人生。馬垃還容納了可憐的小拐兒,“一個單身的中年男人和一個失怙少年搭伙的日子,漸漸變得像樣起來”,不僅如此,他們還收養了大碗伯留下的“社員”,和果園里可愛的小刺猬“大林”、“小林”和諧共處。
唐草兒覺醒的過程正與馬垃自己精神被修復的過程同構。他頗有責任意識地幫助指導小拐兒和谷雨,自掏腰包為村人組織舞龍表演,在鄉村里,舞龍舞獅子可謂一場精神盛事,“鏗鏗鏘鏘的鑼鼓聲把那些還在做夢的小孩子從熱被窩里拽了出來,連早飯都顧不上吃,就迷瞪著眼睛往鑼鼓喧天的地方奔去”,重建淳樸而熱情的文化秩序和氣氛,節慶之際,家家戶戶都請馬垃去杵糯米,這片天地最終滌蕩了馬垃曾揮之不去的“羞恥感”,修復了他的感情。由此可見即便是直面嚴峻現實的文學創作,也可以完全不失柔軟和細膩的觸角,這才是我們每個即便平凡但依舊保有真情的當代人所置身的完整的現實世界。
當然,在切實的生存和殘酷的擠壓面前,倫理又很無力。宏大的農業計劃因為荊江大水而遭受重大挫折,又因為市委領導的全局戰略而徹底胎死腹中,谷雨為了一家人的生計無法繼續追隨馬垃在理想主義大地上停留,在這個意義上,馬垃既無父又無子,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人,同時也是脫離了最貼合自我(家庭)的社會關系的人。他是好人,也是能人,但早已不是社會主義新人,更不是21世紀的新人,他就內在于我們每一個孱弱的當代人中。一個可能的真相是,在這個由資本和權力主導的時代,馬垃這樣的普通人,無法穿透口號的激情而成為歷史的真正主體。其實,當逯永嘉的理想國必須要借用紅二代和資本的力量推進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其希望之渺茫,而時代證明了這一點——最后以“二公子”為保護傘的安泰集團走私行徑敗露,卻讓鯤鵬公司當了替罪羊;再看馬垃的鄉村建設事業,它的順利推進,實際上受惠于貸款的便利和政策的靈活,更是受惠于馬垃與縣長丁友鵬的同學之誼。馬坷的生命結束于一場大火,馬垃的事業終結于一場大水,鄉村這種離自然最近的地方,恰恰蘊藏著最大的原始牽掣力,馬垃不可能樹立起坍塌的鄉村主體,也無法匡扶被資本和強權扭曲的正義,所以他只能是精神性的存在,而這一歷史性的任務還是要交給在這個結構化社會里真正有力量的人——知識分子。
“馬垃隱約看見有個人從大霧散盡后的曠野上走來,他覺得很眼熟,仿佛某個失散多年的親人和朋友。”小說從這里開始,就進入了下部,主人公換成了慕容秋,這可能是作者給出的第二條彌合社會分裂的方案,把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二者的視野相互嫁接,催生新的動力。
知識分子是社會精英,真正有生產力和話語權的頂層設計者就是政商學精英,知識分子在這組穩定的三角結構里是一方可以起到輪轉與辯證作用的力量。與想象中逯永嘉和馬坷的辯論相似的是,知識分子界有更為激烈的多元理念和思想的碰撞。在香山飯店舉行的中國社會學學會年會上,所謂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民粹派、學院派都各抒己見,毫不相讓。所以必然地,慕容秋、何為和曠西北們出場了。慕容秋是一個充滿文藝氣質的知識分子。她出生于寬容平和的高知家庭,青年時期“上山下鄉”的經歷讓她的情感寄托在了鄉村和普通人身上,返城后上了大學,從此留在高校。她善良正直,不滿庸俗的學界風氣,同情逐漸失去工廠的工人們,她規避著社會的污濁,努力保留赤誠之心,也在思考知識分子的進取價值。對于深藏在她記憶中那一對青年和少年——馬坷和馬垃的情感認同,還有對青年知識分子曠西北堅決對抗社會不公的勇敢行動的欽賞,和女兒小鹿無所畏懼的理想主義都匯聚成一種巨大的力量,使她下定決心,“不能再在散發著腐朽氣息的‘學術圈’里待下去了”,要“回到那座她曾經生活和勞動過的村莊,做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調查”。這是一個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精神蛻變,也促進了有效的知行合一。

《第八個是銅像》
慕容秋與馬垃的關系,最初的緣起是對于馬坷共同的感情羈絆,他們二者都深愛著馬坷,但是在理想主義時代結束的時刻,慕容秋離開了神皇洲,馬垃也外出求學與經商,從此再無直接牽連。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們二人都將對方的回憶拉回到眼前,兩條線索重新匯合的扭結則是那本三十年前的《青春之歌》。是《青春之歌》激活了慕容秋關于過往的記憶,促使她重新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反思,也使她認識到自己實現真正的社會價值的渠道所在。也是對于《青春之歌》和哥哥日記的重讀,讓馬垃正視“集體主義”在自己身上刻下的正面影響,這種結合其實是兩種行動的自我的相互彌合,是相互召喚的結構。沒有這種結合,就沒有他們二人的最終成熟,這個逐漸僵化和封閉的社會結構也就失去了再次敞開的可能。
作為知識分子,慕容秋關注學術發展的合理方向,而不是具體的操作范式和物質回報,在充分立足于經濟和政治認識的基礎上,她在腦海里一直企圖整合新聞學、社會學、人文學,不斷反思她所堅持的中國農村制度研究。而女兒小鹿的戀人曠西北所著的《C縣農民調查》認為“只要解除壓在廣大農民身上的重負,將分散的農戶重新組織起來,應對市場的挑戰,才是我國農業加入WTO之后的根本出路……”,對此慕容秋十分贊賞,從會場上潮水一般的掌聲里也看得出來,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持這種批判立場和人文關懷。他們需要的是邁開腿,接住人民遞來的接力棒,去面對“沉重的歷史和堅硬的現實”。
作為一個優秀的學者和規范的公民,慕容秋具有強大的行動力,她能夠連結起很多社會關系,還是青年人與這個世界的重要紐帶,她的身體力行對女兒小鹿的獨立精神和人格培養都有深遠影響,更會對自己的學生起到言傳身教的作用。可以預見,一批同樣優秀的青年人會通過慕容秋這一重要媒介貼近大地、走向社會。
三、否定的疊加與開掘
憤怒的人群因為不滿楚風集團而圍攻沿河縣政府后,各方利益如何協調,場面如何善后,其實都與馬垃無關了,他在意外挨了一記悶棍之后回到神皇洲安心寫書,開始沉心靜氣地梳理自我。在這個敘述脈絡里,第三十二章是一章空白,“此處省略9800字”就不難理解了,行文邏輯并不允許這里出現不可描述的性和暴力,卻留足了空間讓讀者去創造。實際上,馬垃在沿河騷亂后逐漸無法再直接出場,代替他行走的將是慕容秋,主人公活動空間的暫時收縮,正展現了宰制文學的現實的困境。當然,這并不影響文學表達,巨大的空缺反而是更準確的傳達。

《安娜·卡列寧娜》[俄]托爾斯泰著
此外,文中還常常運用互文的參差修辭。馬垃帶著谷雨赴長沙買稻種,在趙廣富的田里借路改水,這樣的段落里有著梁生寶和高大泉的影子,而且我們還在文中頻繁地與馬克思、毛澤東、凱恩斯等政治家、經濟學家相遇,也能看到雪萊的詩歌,叔本華哲學,《艷陽天》、《人生》、《平凡的世界》、《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八個是銅像》等文藝作品也常常出現。小說文本還重現了當年關于“潘曉來信”的精神爭論和“雷鋒精神大探討”。完全是一份一代人精神成長的營養記錄,借此我們了解了那一代人的思想來源,以及他們在精神塑形中不斷受到外界敲打和內在詰問的過程。
小說里散落如此多的文學符號,正是作者刻意把文學置于其外的象征語境中。《人境》與許多文本都形成了一種肯定的正面的互文關系,比如《平凡的世界》,其自我指涉意味是非常明顯的。在看到《安娜·卡列尼娜》里自己所欽佩的列文決心要靠自己努力讓生活變得美好的時候,“‘勤勞、純潔、集體……’他念叨著這幾個詞兒,并且把尾音落在‘集體’兩個字上,細細地咀嚼著。無論如何,作為一個已經過了四十歲的男人,應該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了。”這種偶像的正面啟示,是一大批有良知有理想的人的精神資源。
但是另一方面,馬垃在哥哥墳前仿佛聽見逯永嘉對馬坷英雄行為的嘲諷,回憶起丁友鵬在“潘曉來信”事件后對“他我之辨”振振有詞,而當時還遠不成熟的“馬垃想反駁丁友鵬的觀點,但他猶豫著,還是沉默了”,則又彰顯著否定的互文關系。這時,馬坷、逯永嘉和丁友鵬等人的話語直接跨越了時空,而形成了一個共時結構,造就一個雜亂擁擠的互文空間,眾聲喧嘩制造了多重的不確定性,這種措置的、不均衡的樣式極大地開拓了小說敘事的歷史縱深度和空間開闊度,回憶中的文本是理想的擴容器,也超越了粗暴的肯定和否定的單向度判斷。
當代中國文學如何正面講述“人”,而不是專注于剖析人的幽微陰暗甚至卑劣失格,這個問題現在幾乎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自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對“人”的書寫就開始“向內轉”、“向下走”了,更細微地呈現人性的“暗”和“狠”成為了流行,寫人性的“真”和“善”則被報之以譏誚。但是《人境》借用一個迂緩的形式重新拾起并回答了這個老問題。它告訴我們,如果在現實表意中進退維谷,借用曾被全社會分享的文學資源,重走人物畫廊,聽深谷里的回音也是一條可能的路徑。好在閱讀經驗告訴我們: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些正面人物和逝去的理想的不斷閃現,仿佛是在用許多眼睛來凝視時代的變化。“往事如駛離的大船,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正在相互告別,相互辨認。”敘事縫隙中的矛盾和停滯恰好呈現了歷史的真相,將否定疊加起來,也就在更深的意義上開掘了真正的理想主義。在否定之否定的途徑中不停回到歷史里去,清理我們的歷史債務和心靈創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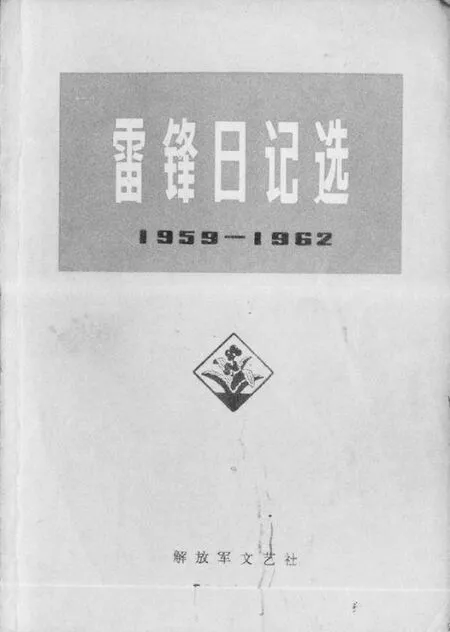
《雷鋒日記選》
借著馬垃的眼睛,我們看見了馬坷的日記。那個筆記本是馬坷1973年5月在“沿河縣農村優秀團員青年代表大會”得到的紀念品,日記結束于1975年6月6日,期間日記本里記載了他和弟弟垃子及大碗伯的親情,與慕容秋的朦朧愛情,也記載了緊張的生產建設,與知青們開展的業余文化活動。主要還是記載馬坷自己的思想動態,比如看《雷鋒日記選》,學習陳岱山和金訓華的感人事跡。馬坷的日記,語言十分稚拙,這不僅符合他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作者完全是在模仿那個時代的話語結構,所以類似于“我要勇敢、堅定、沉著,在生產勞動中起模范帶頭作用,逐步把自己鍛煉成為一個合格的共青團員”這樣的時代痕跡必然明顯。日記的體裁完全擺脫了純客觀敘事角度,為心理空間的開掘創造了便利。因此從文本里長達十幾頁的馬坷日記,我們可以看到,馬坷自己豐富的思維和情感層次,他不是固化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青年人,高尚、細膩、又自律。馬坷把他與慕容秋的對話詳細記載,還用引號區分清楚,可見其對慕容秋的傾心程度;有時也頑皮地記載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在參與荊江古道的裁直工程時突然豪情滿志、賦詩一首;還有的篇幅則完全是對于自我的克制,比如在連續記錄了幾次和慕容秋有關的日記后,1974年11月28日,馬坷記錄道:“最近是怎么了,一拿起筆就覺得有寫不完的話,難道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原因么?這樣既耽誤工作又干擾思想。以后每篇日記爭取不超過三百字。”這種自我抒情和自我抑制都是真實可信的,也是《人境》的整體文本里一個關鍵的裝置。這種直接的呈現聚焦于馬坷自我內心情緒流動,好像他的日記是一塊飛地,完全避免了時代的沉疴,作為一面曾經高高飄揚的旗幟,當它穿越了整整四十年來到早已滄海桑田的馬垃面前的時候,竟然還是那么純潔和鮮亮,這種反差著實讀來令人唏噓,難怪會讓馬垃又一次淚眼模糊。

《青春之歌》楊沫著
馬垃一直在寫一部關于個人成長和思考的書稿,他依然保持著探尋人生的熱情,在持續的回顧中不懈地塑造著主體。借著唐草兒的眼睛,作者為我們呈現了馬垃寫的那本總結自我的書。在沿河舉辦的社會學高峰論壇上他還提交了講述農村建設經驗的論文。因此,他既屬于現實,也屬于未來,是一個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生長的普通人,他仍然具有蓬勃的成長力。這也是為什么在平凡的世界里,每一個善于反思自我和懷抱真心的普通人都不能夠放棄希望的原因之所在。
四、結語
小說一次次在沖破障礙,從最開始的只能寫街巷或者山野里的“流言”和“小道”,到承載著家國事業的“文學之最上乘”,又到擰斷政治束縛,重返“純文學”家園,這一路曲折歷程,小說家實現的其實也就是選擇“睜眼看世界”或者臨水照花的自由。劉繼明當然是早早放棄那西瑟斯神話這一路的人,他的創作就是他的“精神履歷”——那是沉重的喘息與不滅的希望。
作為一個體量很大的文本,《人境》總是在巨大的視野開闔中輕易地捕獲社會的問題和矛盾,但作者又像粗中有細的魯和尚,他忘不了跑前跑后的小狗“社員”、也記錄了“洋買辦”辜朝陽在象征著父親和家國的東湖賓館沉默徘徊的側影。書里寫到的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精神遺民的氣味,像歷史的漫游者,冷眼熱腸。這種鐵骨柔情的寫法有著溫暖和磅礴夾雜的古典主義氣息。作者是被不斷注入靈魂的思想動力推著走的,一邊在接收泥沙俱下的社會信息,然后用自己的道德信念和社會理想,以冬日飲雪水的定力過濾一遍,最后從另一邊流淌出崇高的思想感情和樸實的文學質地。
在關于公平正義的方案被擱置緩行、理想主義被拋棄,發展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反思的“空洞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當下的文學不僅切斷了生活與思想的關系,也切斷了當下與過去的關聯。文學生產熱鬧地“空轉”,卻無法觸及真切的問題,而《人境》則迂緩地擴展開了文學與社會和歷史的多維互動。當下的文學是否就可以承載起時代對于文學的要求,突破“純文學”和敘事的內面化,參與到“他者”和“我們”對于自身歷史和共同體的想象?如竹內好指出的,“文學在政治中找見自己的影子,又把這影子破卻在政治里”。“無論人們怎樣善于“遺忘”,歷史和個人的真知,都會以某種令人驚奇的方式復活,并且頑強地參與到當代史的建構中來。”在這個意義上,《人境》像一個棱鏡,將文學的深湖與現實的天空相互投射、內外勾連,是屬于真正思想者的文學。

陳若谷,新疆克拉瑪依人,文學碩士,正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文學博士學位。學術研究興趣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