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蕓短篇小說集《與孔雀說話》淺談
朱寒霜
王蕓短篇小說集《與孔雀說話》淺談
朱寒霜
湖北籍南昌市文學藝術院專業女作家王蕓的小說集《與孔雀說話》,在底層敘述中,以現實中的日常生活與生存狀態為出發點,將關于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圖景向塵世的廣度和深度延伸,使之被生活碎片裹挾和撞毀的美好記憶與留存,在借助藝術依托轉存的剎那間,凸顯出意義。
這是一種精神性的文化脈動,它來自傳統與現代、古典與時下各種撞擊和糾結。亦歌亦泣的人間狂熱有《紅袍甲》、《大戲》、《空中俏》、《龍頭龍尾》、《年祭》;發自心靈的原罪或救贖有《與孔雀說話》、《鑄劍》、《木沉香》、《羋家冢》;生命的綠色與生存的含淚狀態有《墨間白》、《交出你的手》、《神仙貼》、《護城河邊的旋轉木馬》。 在俗世里,民俗風情就像一幅畫,一首歌,常駐心靈。它有著詩意的糾結,也有著俗世的無奈與宗教式的宿命。《年祭》中的主人公孟余和他的假扮女友劉思琪在俗世的年祭中表現可謂淋漓盡致;《龍頭龍尾》中陳家莊的板凳龍,將一半是鄉情、一半是尋根的俗世繪,以其難以擺脫的心理定勢,匯聚在時光的河流里。《大戲》則在一系列文化傳統與現代生活的奔流不息中,將無聲無息而又洶涌澎湃的至上藝術席卷過人生舞臺。在系列小說中,無論是戲曲,還是水墨,工藝,還是象征性的孔雀,木馬,墳冢,都是藝術對心靈的彌補與代償。
傳統文化的美感與現實生活的骨感,形成了高度的、至少是畸形的不對稱,而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起著杠桿作用的經濟基礎。不用說,這種經濟的杠桿作用對于底層的蕓蕓眾生來說,往往是絕對的,充滿憂傷的。諸如:把《紅袍甲》中的劉玉聲帶入與兒子對抗與對峙的狀態中,將其中產生的對現實的抓拍與某種秒殺性的瞬間放大,因而就成了有意味的藝術表現;再比如《木沉香》、《鑄劍》等,這些作品的內涵以其草灰蛇線、伏脈千里的意象感,把那些浮游的絲絲縷縷所裹挾的意識存在,借助文字的弦外之音而束集在一起,就有蛛絲馬跡可循了。
那么,在這樣的空間里是否適合存放我們的心靈?這就是一種文化擺渡式的有意思的無意識流動了。它并不存在答案和給予什么答案,而是以一種純客觀的、自在自為的敘事,給人活色生香的自然感發,你的視覺,你的感悟,你的理解,都是基于文本保持了清醒的質感,這樣的作品的現場感就更有作者、作品、作家的環境氛圍,在給人帶來美感的同時,也歷經了一場文化擺渡和記憶復耕,《大戲》、《龍頭龍尾》、《年祭》所存放的時空就像有層次的鱗片和有梯級的麥田一樣,冬天的風吹過一陣,春天風又吹過一陣,在春種、秋播的過程里,將記憶復耕成土壤里的文化氣息,更加有泥土的味道。
在令人沉醉的審美中,傳統底色與現代人文批判精神也滲透到深層的審視中,最終留給人的是一種消解、權衡或呼救,盡管是含蓄的、低音的、多維的。《與孔雀說話》小說集,在直面生活的傳統文化里,一些傳統文化的文脈命懸一線,需要有一種方式,來培植、復活、新生,欒其鳳、劉玉聲、空中俏的神采仿佛就是一朵朵接天荷花,十分鮮活地將一股清風帶進了我們的歷史文化視野之中。至此,作品的思想性或者說是內涵,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敏銳眼光和人文情懷。
《與孔雀說話》善于以夸張、象征、荒誕、夢境等隱語式的藝術手法勾勒底層人的生存狀態。如《護城河邊的旋轉木馬》、《神仙貼》的深刻寓意;劉玉聲、老顧等主人公身上的夢境;《神仙貼》、《羋家冢》的離奇;《鑄劍》中的中風者老孟的隱現;譚木匠臉譜式的變身,等等。在作者的筆下傳神地勾勒出一幅幅社會人生的剖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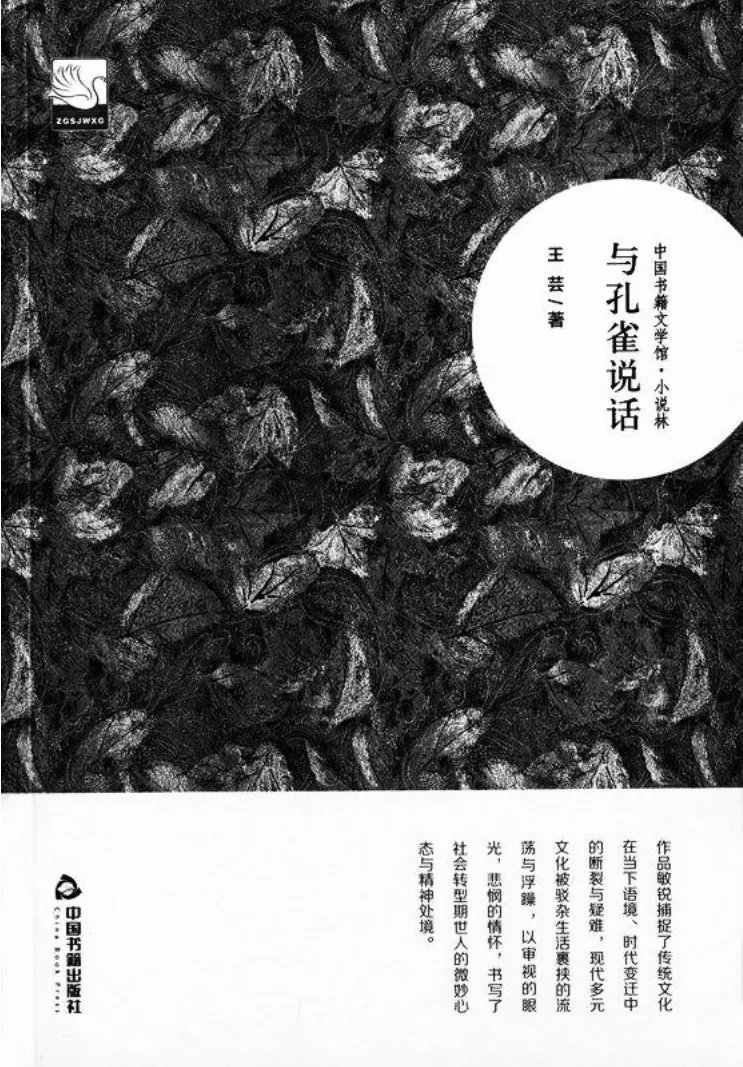
《與孔雀說話》王蕓著
荊楚文化的沃土,南昌地域的風情,以及傳統文化的的熏陶,都有著作者個人的內心體驗和價值判斷。我們不難發現,《與孔雀說話》有著不俗的藝術品質和厚重的精神內涵,取材的寬泛與生活的豐富多彩,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在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鄉情包括鄉親、親情和生活情景,都與風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沒有風土人情的鄉情是膚淺的,無根的,帶來不了感染人的情節,也帶來不了豐沃的文化氣場。劉玉聲上戲前的沐浴,欒其鳳的水袖,空中俏的飛舞,譚木匠的刨花……都是那樣栩栩如生。
《與孔雀說話》一書中的小說作品,諸如難離人間煙火、才氣橫溢而又無從施展的藝術家、傳承者,其得以存在的藝術空間越來越窄小,心靈呈現出新舊交替的浮躁與崩潰,既是個人的,也是時代與社會的。
我們可以說,《與孔雀說話》這篇小說有著統攝全集的基調:人的異化與悲涼。透過老顧孤單的身影,讓人看到人的冷漠與隔膜更甚于動物。回歸的可能,已很難找到土壤;縱然是土壤尚在,卻沒有了可以依存的植被和生態環境。其間的蒼涼與戛戛獨造顯得格外刺目與令人扼腕。
對孩子成長過程的關注,尤其是對他們的健康成長所應給予的心靈關懷著墨較多。《護城河邊的旋轉木馬》的冷峻,猶如一把手術刀,貧窮所帶來的罪與罰,讓年幼的心靈過早地背上人生的包袱而導致心靈扭曲,青子和秦阿木的刻畫入木三分,催人淚下。《墨間白》、《伸出你的手》,從需要對兒童天性保護、培養、激發、正確引導,而不是忽視和扼殺的角度切入……李準的壓抑、叛逆和反抗,西瓜的孤獨、自閉,秦阿木陷入犯罪的泥沼……這些作品在如何對待孩子的成長問題上開拓了新的視野。
有人說,美的力量絕不亞于思想的力量。讀王蕓的小說,總讓人沉浸在一種濃郁的藝術氛圍里。她以清簡的筆調,將小說中所刻畫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普通人的藝術追求和心靈世界,根植于淳樸深厚而又帶有宗教情結般的鄉土風情、民俗氣韻之中,所帶來的藝術魅力是感人至深的。
王蕓繼承了傳統的敘事手法,將純客觀的故事情節置于隱語般的語境下,從中可以找到多元的人生況味。《大戲》、《龍頭龍尾》、《年祭》幾個短篇中,在人物藏真守拙、古樸蒼涼的精神堅守中,又有著生存需求的掙扎感,將傳統的文化肢解和消解在日常的瑣碎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陌生而又熾烈的現實名利上的斤斤計較。在利益和金錢的驅動下,人物走向了異化和蛻變。在短篇《與孔雀說話》中,單拈出人的孤寂與悲涼心境:黃昏時分,老顧一個人走下山來,身后拖著一條長長的影子,在山環水繞的羊腸小路上,踽踽而行。遠天鋪排著一大片火燒云艷得燙眼。
此外,作者的語言極具張力和綿韌,寫意而又傳神。
“嘮叨、期盼、牽掛、眼淚、失望,這一年積攢下來的,都寄放在這一碗一筷里了。如果將這樣的畫面重疊在一起,中間垂落下來的,就是孟余一年虛擲的時光。”
“滑翔了幾日,空中俏再回來,被夕陽印貼在地上的身影就似了被熨斗熨過的衣裳。”
“她的抱怨就像她手上鉤圍巾的針一樣,一下接一下,一環接一環地鉤呵鉤,慢慢鋪成一大片。鉤出的圍巾上布滿了小洞,仿佛生氣的手指戳出來的。”
“青子媽媽的臉再沒辦法笑呵呵地端出來了。”
……在這樣一種有聲響的語言節奏,激活了充滿生命氣息的人生場景,走進去,讓我們的日常生活具有了審美意味,走出來,傳統文化在現實中有了煙火氣的時代悸動。這就是語言的魅力所在。
朱寒霜,女,湖北鄂州人。現供職于鄂州市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