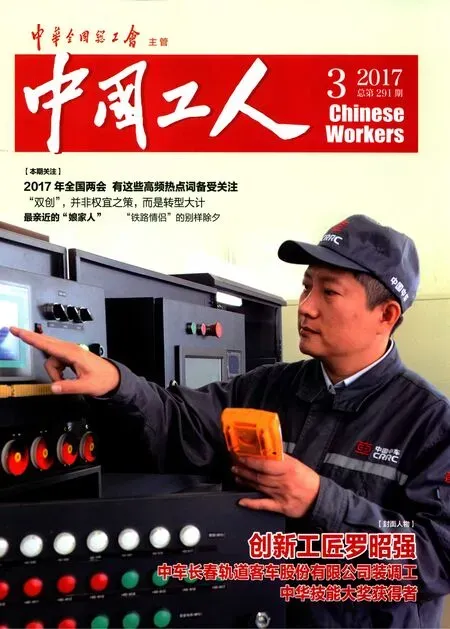追尋夢中的芳草地
——內蒙古一機集團工人畫家胡永斌及其工業油畫述評
■吳大剛
追尋夢中的芳草地
——內蒙古一機集團工人畫家胡永斌及其工業油畫述評
■吳大剛
初次看到胡永斌的油畫,尤其是反映老工業的油畫,便令人眼前一亮——那印證舊工業時代坐標的銹跡斑駁的蒸汽機火車頭、廢棄的廠房以及前沿勞動者;那濃濃的懷舊情緒,將畫作浸染得如此幽深且富于哲思,一定程度上誘導了大眾的審美意趣。用他的話說,這便是著意追尋的夢中“芳草地”。
(一)
三十幾年前,少年胡永斌回鄉養病的頭一天,就被紅漆長柜上的一卷白紙所吸引,展開一看,一副白描手繪“觀音渡海”圖赫然眼前。其細若發絲、流暢的線描,繪出觀音的慈祥神圣之態,令他驚訝不已。家里老人告訴他,此畫是“文革”期間從北京被下放勞動的一位畫家所畫。
此時,胡永斌的想法就是想畫一畫這“觀音”。便買來廉價的毛筆和白紙開始反復臨摹,畫完一看竟肖似原創,還得到老鄉們的贊賞。這讓他既惶恐又興奮,也平添了一種自信。
臨近春節,農村家家都有換“中堂畫”的習俗,往年每家“中堂畫”都掛山水花鳥畫,而這年,少年胡永斌畫的“觀音”,卻頗受鄉里的青睞,紛紛將“中堂畫”換成了 “觀音渡海”圖……
初春,恰逢縣城藝術學校美術班招生,他以第一名考中,并狂學了一個月“基礎素描”和“色彩”課。那時的他“少年不知愁滋味”,見啥畫啥:速寫、水彩……等。每天忘情地奔走在縣城和鄉村的小路上,一路的景色和鄉情,都成為筆下的“習作”。他的病也在這段自由的鄉村生活中好了起來。
半年多的潛心學畫和鄉村生活的滋養,胡永斌對繪畫已日漸癡迷,悄然融入生命的有機部分。
(二)
1982年, 16歲的胡永斌進入內蒙古第一機械制造廠(一機集團前身)成為工人。工閑時,經常跑到廠工會文化宮畫室,看畫師畫 “電影海報”。久之,文化宮老師也就默認了這個“弟子”。在老師的指導下,第一次得以較為系統的學習繪畫。剛開始主要是學“寫意山水”、“花鳥畫”技法。那時,由于文化宮經常要畫“電影海報”,較多地接觸色彩,遂產生對西畫色彩的濃厚興趣,并逐漸轉為畫西洋油畫。
上世紀80年代,社會上娛樂活動匱乏,繪畫就成了他青年時代唯一的“娛樂”。為了完成一幅“電影海報”,他吃過早餐,一頭扎進不足十平米的斗室一畫就是一天,忘記吃中午飯、顧不上喝水,常到傍晚才完成任務。此時,胡永斌除了畫“電影海報”,也臨摹了大量水彩畫和油畫。
但是隨著“學畫”的深入,他繪畫理論知識的貧乏也漸漸顯露,阻礙了學藝進程。幸而,與生俱來的謙遜和執著救贖了他。他信奉“三人行必有吾師”:一方面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主動交往當地知名畫家、同道者及美術愛好者,與其交流切磋技法;另一方面,通過專業書籍自學繪畫理論,書店甚至舊書攤都成為他經常光顧的地方。
十年磨一劍,胡永斌的繪畫理論水平顯著提升,畫技更是日趨成熟。應當說,這段學畫經歷,為他日后的藝術之旅夯實了路基。1987年,油畫作品《與風同舞》首次參加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神劍文學藝術展”居然獲優秀獎。
此時,他對繪畫已有認知:沉淀自己,耕耘不輟,是無論從藝還是為人,都要把持和遵行的一種心態和作風。
(三)
三十多年來,他依托包頭這座工業文化內涵深厚、人文景觀獨特的城市,為自己的繪畫生涯踏出了三條路徑:
路徑一:“工業油畫”。胡永斌長年與勞動者為伍,忠實記錄漸行漸遠的老工業背影,已成業態。工人出身的他,親身經歷了工廠的歷史沿革,對老工業有著深刻的記憶,對老工業題材創作一往情深,鐘情于描繪工廠的人和物,責任感促使他用畫筆忠實記錄下這漸漸淡去的畫面。
他采用寫實畫法表現工業題材,如老蒸汽機火車頭系列。細致入微地刻畫出老火車斑駁的滄桑,掩不住曾經的輝煌;虛幻的背景,敘述著遠去的記憶;隱隱的火苗、堅強有力的身軀,仿佛不甘沉默等待涅槃的憂傷。畫家用近景折射歷史漸逝的無奈與悲壯。如《塵封的記憶》、《歷史的追憶》、《昨日功臣》等蒸汽機火車頭系列。
路徑二:“風景油畫”。 胡永斌奔走于山川鄉野之間,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捕捉靈感,是他第二種藝術生活狀態。
他的風景油畫,可窺見希施金和列維坦兩位俄國風景畫家的風骨,追求光線和逼真,通過躍動的筆觸,重視情感的抒發,崇尚藝術自由與個性發展統一;注重從寫生中捕捉視覺感知,又以社會認知充實畫面的精神內涵,有深厚的故土情結。如《秋韻》、《后園》等。
路徑三:“人物油畫”, 胡永斌的油畫人物汲取了十九世紀俄國肖像油畫家尼古拉費欽的色彩明快、對比強烈的筆觸和風格,以及艾軒、羅中立人物油畫的表現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可看出正沉浸于對油畫藝術走向的體驗,以及對厚味油彩材質表現技法與奔放筆觸所形成的震撼力的感受,心無旁騖地執行著和開掘自己的藝術表達力。如《焊花情》、《四重奏》等。
(四)
縱觀胡永斌的油畫創作,明顯地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油畫影響。為了將傳統的寫實與現代主義中的抽象結合起來,他對具象的畫面進行了簡化。即用突出實物特征來完成畫面的抽象結構。


胡永斌





油畫老火車《歷史的記憶》,透過撕裂的鐵皮,看到沉寂在迷霧中的鋼鐵身軀,仿佛時間定格在那個歷史時刻,不僅表現某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更令觀者感受到那份久違的力量與沖動。作者將自己的人生信念和審美追求一并融入其中。
大幅油畫《車輪滾滾》則充滿著昂揚之氣,昭示著團結與力量,讓人頓生一種向上的激情、昂揚的精神、前行的勇氣,其獨到的審美角度和創意表現不僅給人以藝術魅力沖擊,而且激蕩神情,將我們又帶回到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值得一提的是,他運用油畫刮刀技法,抽象、粗線條地表現了勞動者那吃苦耐勞的精神狀態與場景的特質,如《四重奏》,賦予人物以歷史感和寓意幽遠的聯想,既反映出了畫家心靈深處的主觀感受,又與鑒賞者產生共鳴,以此來啟發觀者對生存狀態的反思,從中得到真、善、美的精神陶冶與心靈洗禮。
應當說,在他的畫里,寫實的技法、情緒的渲染,令充滿懷舊情結的畫面貫穿其中,使人瞬間感受到一種歷史的穿越感,給人以博大、質樸、凝重或傷懷之感,既有細致描繪,又有著粗線條的視覺沖擊。體現了畫家立足工廠、融于生活、領悟自然大象的繪畫理念。通過作品的藝術魅力來回味和觸摸歷史,是胡永斌一直追索的創作方向。毋庸置疑,“工業系列”是胡永斌油畫的最大出彩點而為畫界津津樂道。
是的,他似乎已經找到了夢中的“芳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