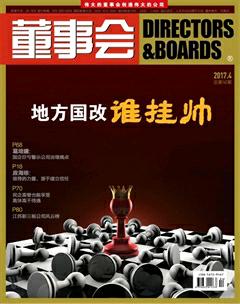險資股權治理套上“緊箍咒”
熊錦秋
即使姚振華被行業禁入,名義上不得擔任保險公司董監高、不得從事保險業務,但他還是保險公司大股東,事實上他還是在保險業混、還是在從事保險事業,保險業“行業禁入”政策,實在是徒有虛名。
前段時間,保監會對前海人壽及相關責任人作出行政處罰:對時任前海人壽董事長姚振華給予撤銷任職資格,并禁入保險業10年的處罰。這個處罰應該說比較重,然而行業禁入措施能否對規范保險公司運作等起到根本性作用,值得懷疑。
前海人壽主要存在“編制提供虛假資料,違規運用保險資金”等五方面違法事實。《保險法》第177條規定,違法違規情節嚴重的,可以禁止有關責任人員一定期限直至終身進入保險業。一般將保險市場禁入的期限劃分為3至5年、5至10年、“終身”三個檔次,如果行為惡劣的采取5至10年禁入措施,如果構成犯罪或行為特別惡劣的則被終身禁入;或許姚振華的行為屬于“行為惡劣”、但尚未到“特別惡劣”程度。
目前姚振華盡管被實施保險業禁入措施,辭去前海人壽董事長職務,但他持有寶能集團100%的股份,而寶能集團持有鉅盛華 67.4%的股份,鉅盛華又以51%的持股比例控股前海人壽,姚振華為前海人壽的實際控制人。不僅如此,此前有媒體質疑,前海人壽其余四家非控股股東,或是寶能系及姚振華的代持平臺,也即前海人壽或被姚振華100%控盤。即使前海人壽的公司治理能夠嚴格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確保公司與實控人的相對獨立性,也只能部分抹去姚振華的影子,姚振華作為前海人壽的實控人,不可能不對前海人壽的經營作出任何指示,只不過是從前臺直接指揮轉向幕后遙控而已。
審視本案,從制度源頭反思,該如何抑制或規范保險公司的過激投資等行為?
首先,要防止保險公司被某個主體單獨操控。股權是公司治理的基礎,股權監管是保險公司治理監管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以來,保監會對股權監管制度進行了系統梳理,目前已經發布《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將保險公司單一股東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低至1/3,這對完善保險公司治理應該有較大作用。不過,這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要切實貫徹“穿透式監管”原則,對保險公司出資股東,要查一查其最終資金來源,是否為自有資金,防止一些主體找“馬甲”代持、從而持有保險公司50%以上股份,由此形成單個主體對保險公司的絕對控制,這樣所有的問題都將回到原點。
其次,要完善保險公司控股股東的資格條件。《征求意見稿》將保險公司股東劃分為“財務類股東、戰略類股東、控制類股東”三個類型,其中控制類股東是指持有保險公司股權百分之二十以上。《征求意見稿》第十八條規定了成為“控制類股東”的條件,包括需要具備投資保險業的資本實力、風險管控能力和審慎投資理念,且不得“在公開市場上有不良投資行為記錄”等,筆者認為這其中一些條件缺乏剛性,比如如何判斷是否具備“審慎投資理念”?建議細化操作細則,而且應該是動態判斷,假若保險公司暴力舉牌,本身就可說明大股東可能缺乏審慎投資理念,應責成保險公司完善治理結構。要采取有效措施讓保險業姓保,防止把保險辦成富豪俱樂部。
其三,要完善目前的行業禁入制度。保險業禁入的實質內容,主要是禁入人員不得擔任保險類機構董監高或者從事保險業務。即使姚振華被行業禁入,名義上不得擔任保險公司董監高、不得從事保險業務,但他還是保險公司大股東,事實上他還是在保險業混、還是在從事保險事業,保險業“行業禁入”政策,實在是徒有虛名。
當前保險業行業禁入政策還難起實質性作用,這主要是因為目前“行業禁入”的定義仍然比較模糊,或者說其內涵或外延還太窄。目前行業禁入有兩方面禁止內容,一方面是不能擔任公司董監高,這條紅線比較剛性,約束比較有效;另一方面是不能從事保險業務,但什么是“保險業務”卻無定義,這方面就缺乏實際約束力。比如,繼續當保險公司控股股東,是否從事保險業務?
對“害群之馬”實施行業禁入,向其亮出紅牌、驅逐出場,是為了保障比賽能夠照常進行、市場能夠正常運轉。筆者認為,對“保險業務”理應作出明確定義,以增強行業禁入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威懾力。定義可以采取列舉式和概括式相結合的方式,比如將持有保險公司5%以上股份或者保險公司實際控制人,認定為從事保險業務;概括式定義則相當于兜底條款,以防止遺漏。這樣就可防止“害群之馬”流連市場對行業產生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