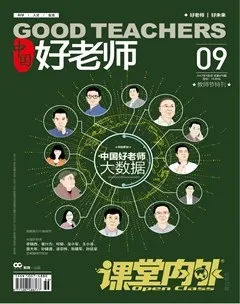留住孩子的根
37年前,歲在庚申的秋天,我年僅17歲,高中剛畢業,對教育教學還是懵懵懂懂。父親“胡攪蠻纏”逼我接替他回家當民辦教師,斬斷我跳出大山飛黃騰達的大學夢。
我有四姊妹,我是老大,三個妹妹。不怕笑話,那時我家里連買鹽都困難!讀高中時學費都是東拼西湊的,家里有了欠賬。三個妹妹在家放牛、割草。我是家里唯一一個男孩,爸爸媽媽擔心我飛走了就不回來了!兒子在,家才在,家鄉把這叫做留住根。
一個山村,半山腰里,破舊的三間草屋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石課桌石凳子,牛肋巴窗戶,干打壘的墻體,在這熟悉卻又陌生的環境里,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我猶豫不決。
“孩子,你是村里的第一個高中生,你考大學僅僅10分之差,復習一年一定沒有問題,但你一個人走得快,我們全村的孩子就飛不遠啊!我僅僅一個小學文化怎能帶好孩子?況且家里的境況確實也不允許啊!”望著爸爸近乎哀求的目光,媽媽病怏怏地在一旁的抽泣,我心軟了。
孩子們的笑聲
開學第一天,爸爸早早地催我,“去迎接孩子們吧!”我背著鋪蓋卷,帶著一周的伙食,提著沉甸甸的一箱子書,極不情愿地挪向學校。一路上,細雨霏霏,涼風習習,飄落的枯葉散布在路上,那藏在枯枝敗葉間的野菊花綻放黃燦燦的笑容,頑強地生長著,和自然抗爭。
孩子們唱著走了調的山歌,伴著晨曦,踏著雨露,嘻嘻哈哈地從四面八方飛來,穿鞋子的,打光腳的,吊著鼻子的,披頭散發的,圍著那一棵見證山村滄桑歲月、皮膚龜裂的佝僂著背的老榆樹跑來跑去。望著他們,我默默地思考:既然留下了,如何讓這一群無憂無慮的天真的“野”孩子,未來也無憂無慮呢?
我拿起了爸爸用過多年的手把已經磨光的釘錘,邁向那掛在榆樹上的銹跡斑斑的老鐘,一下一下敲在凹下去透亮的地方。鐘聲嘶啞卻渾厚,在山間飄飄渺渺地縈繞,孩子們像傍晚的羊群擠擠撞撞地涌進昏暗的教室,亂七八糟地坐著,嘰嘰喳喳地鬧騰著。
我拿著爸爸一個暑假挨家挨戶做工作動員來的新生名單,開始點名了。
堅守鄉村的精神雕塑
第一天,任務就是讓孩子們記住了自己和班里同學的學名,并用學名互相打招呼。夠折騰的一天。
晚上,伴著煤油燈淡淡的微光,朦朦朧朧盯著名單,這是一批年齡參差不齊的山里娃,大的10歲,小的6歲,共26人。家長們的疑惑在耳邊回響。“代課”“敷衍”“跑”幾個詞在我的魂靈深處橫沖直撞。躺在冰冷的床上,裹緊被子,卷曲著身子,曲肱而枕,癡望著穿透草屋的星星,眼前浮現爸爸那“毀掉”自己孩子前程無可奈何的眼神,背過身去舉手擦拭眼淚的背影,青春的我心里隱隱地痛,“布被秋宵夢覺”,“歸臥故山秋”。
山溝里傳來雞鳴犬吠,我爬了起來,深深地呼吸著山間新鮮的空氣,望著纏繞在大山的神秘,迎接新的一天。
孩子們嬉戲著,歡樂著,繞著老榆樹跑著,“野”得無拘無束。
越越來到我的面前,笑嘻嘻地從懷里掏出一枚雞蛋,“老師,這是媽媽一早起來煮的,是早上從窩里撿的!”他塞到我手里,深深地鞠了一躬,跑開了。握著這一枚還有體溫的雞蛋,我這個七尺男兒的心被悄然融化了。我的家鄉,那時一枚雞蛋也是很珍貴的,是用來換油鹽醬醋茶的唯一,我曾經因為不小心打破了鄰居一枚雞蛋而被父親狠狠地責罰。
開學第三天,校長李忠國來了,穿著一雙草鞋,一身筆挺的中山裝,戴著一頂軍帽。我知道,他是我們鄉的教育前輩,當年也是放棄多種機會,堅守鄉村,獻身教育一輩子。一陣寒暄后,校長說:“小李啊,山路難走還得走啊!我們的孩子需要你,家鄉需要你,謝謝你了!”校長語重心長地說,“天下的路千萬條,教育是一條平凡而艱辛的路,又是一條滿懷希望的路啊!”校長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好好干,走出一條自己的教育之路,也是有出息的!”臨別時,他從挎包里掏出一本包著泛黃書皮的書,遞到我的手里。走在曲曲折折山路上滿頭銀發的校長,簡直就是一座活生生的鄉村堅守精神雕塑。
送走了頑皮機靈的孩子,夕陽西下,大山被涂抹上一層玫瑰色,裊裊炊煙,聲聲鳥鳴,我心里舒坦多了。
打開李校長送我的書,是蘇霍姆林斯基的《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要進入童年這個神秘之宮的門,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變成孩子。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孩子才不會把您當成一個偶然闖入他們那個童話大門的人,當成一個守衛這個世界的看守人,一個對這個世界里面發生的一切都無所謂的看守人。”“愛孩子”是教育的全部,讀著讀著,如醍醐灌頂,腦門洞開。“校長真是用心良苦啊!”那工工整整的深思熟慮的小楷旁批,讓人油然而生敬意。
家鄉美,留住根
每天推開寢室,門口不時放有學生家長送來的野菜、瓜果、米面、菜籽油等東西。孩子們還沒有到校啊,“天上掉餡餅了!”
我那不安分的心漸漸關閉了門戶,塵封了我那一箱子沖刺高考的書籍,和孩子們一起野著,瘋著,一起分享著。在孩子們野性漫長的枝條上小心翼翼地嫁接著適合的花枝,讓他們開出屬于自己的艷麗花朵,讓他們的未來人生富于各自靚麗的色彩!
學農園地里我們一起播下種子,澆澆水,施施肥,除除草,捉捉蟲,細心呵護每一顆幼苗,守著每一個花蕾,期盼著豐收。
教室里,朗讀聲,歡笑聲,討論聲,互相鼓勵,在知識的海洋里激情地暢游,追尋著對岸的精彩風景,一天一故事,孩子們側耳傾聽,托著下巴迷瞪瞪地似懂非懂地聽著。
“孩子們,家鄉美不美呀!”我隨口一問。
“一點都不美,山高路遠吃不飽。”
“爸爸說,好好讀書,跳出這個鬼地方!”
“媽媽說,待在這里,連媳婦都娶不上!”
孩子們七嘴八舌地吼著。
“家鄉美啊!他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今天好好讀書,是為了走出大山,山外有山,外面很精彩。”
“那我們出去就不回來了。”
我心里就像被什么戳了一下,都飛走了,都不回來了,山村不就變成凋蔽的荒村了。
“孩子們,我們這里現在確實很窮,祖祖輩輩們都守著他,我們今天努力讀書,是為了明天過好日子,不錯。但不能忘了家鄉,這里是我們的根啊!”
我小心翼翼地引導著,要改變家鄉,還得靠這些土生土長的有根的娃們。
春天,我們在山的脊梁上奔跑,放肆地讓風箏高高飛起,極目遠望著山的那一邊,采摘繁花野朵,給自己編制獎勵的花環。
“孩子們,家鄉美不美?”
“美!”
脆生生的童音帶著野花的芬芳飄向遠方。
夏天,在山間小溪捉魚,逮泥鰍,豐富我們的午餐,津津有味地品嘗著勞動的愉悅和歡暢。
“孩子們,家鄉好不好?”
“好!”
毫不遲疑的回應聲伴著歡快的溪流奔向遠方。
秋天,一起欣賞著大山五彩斑斕的色彩,收獲野果,津津有味的咀嚼,享受著大山的饋贈。
“愛不愛我們的家鄉?”
“愛!”
大山的色彩多了一抹沉甸甸的亮色。
冬天,我們收集落葉標本,舉手接著雪花,釋放不知天高地厚的快活,癡迷追趕春天的腳步。
寒暑易節,孩子們長大了,衣服干凈了,沒有花臉貓了,不亂丟亂扔了,知道家鄉美了,有了未來的期望了,我也就拴住放蕩不羈的靈魂,心甘情愿地留下來了。
鄉音不改鬢毛衰
生在小山村,根在小山村,成長在小山村,寒來暑往。一待就是37載,走過了從油燈到電燈的崢嶸歲月,一守就是1 3500多天,劃過了茅屋到磚瓦房再到教學樓的滄桑年輪,我常常戲謔自己是大半生既當校長又做班主任還兼炊事員的“全能”教師。
而今,漫步山間,看見孩子們辦的養豬場,種兔場,肉牛場,山村有了帶著技術回流的致富帶頭人。信步田野,葡萄園,珍貴苗木園,梨園,那是帶著資金飛回的山村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