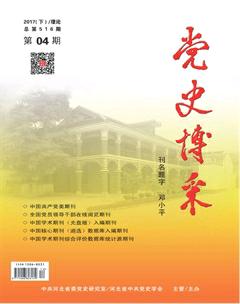論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形成過程
[摘要]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形成經歷了比較漫長的過程。可以分為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萌芽階段,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階段,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成熟階段,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進一步向前發展階段。土地革命時期之前,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出現了萌芽,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初步形成,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逐步走向了成熟。新中國建立,毛澤東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進一步向前發展。
[關鍵詞]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改革
[作者簡介]陳揚(1976-),男,漢族,湖南邵陽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學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向。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毛澤東專項資助課題《毛澤東民族宗教與統戰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6MZDYJZY06)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 A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8031(2017)04-0004-02
一、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萌芽
(一)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民族政策主張
1922年,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和革命導師列寧的直接指導下,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和列寧的有關民族理論的論述和政策實施,制定了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奮斗綱領。就是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推翻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和民族解放。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基礎上,再在西藏、回疆和蒙古地區實行民族自治,讓其成為民主自治邦,再統一聯合組成中華民族聯邦民主共和國。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就由原來的蒙古、回疆、西藏民族地區成為民主自治邦,提出了“和中國本部發生關系由各地民族自決”的方針,然后在黨三大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系列的相應的民族工作。
(二)毛澤東早期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
首先,毛澤東最初是很贊成用民主民族聯邦制的形式來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和民族關系。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關注和重視民族問題,始終把解決民族問題作為黨的奮斗目標的一個部分。當時黨的領導人提出了打倒軍閥、除列強,其實就是提出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和自由解放。
其次,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也對中國的民族問題進行了不懈地探索和研究,毛澤東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理論開始萌芽。毛澤東并沒有停留在當時的認識水平和認識階段而徘徊不前,而是繼續不畏權威、實地考察、認真研究,對我國民族問題的解決進行了十分可貴的探索和研究,毛澤東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理論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了萌芽。如1924年,毛澤東在廣州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就吸收了壯族、瑤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的積極分子和先進分子參加了學習,并且經過培養后,把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發展成為了共產黨員和黨員干部。
二、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的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開始形成
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直接指導下,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制定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在這本憲法大綱中十分明確地規定,中華蘇維埃政府承認回族、藏族、蒙古族、滿族和維吾爾族等各少數民族地區完全有自己的民族自決權,可以建立起自己民族的自治區域,也可以加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
毛澤東在不斷思考和探索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民族思想和理論也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和質的飛躍。不但由原來贊成蘇聯的聯邦制的民族解決方式,轉變為后來的民族自決的形式,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發現民族自決的方式和模式也不完全符合實踐情況,毛澤東并沒有被教條主義所束縛,而是根據實踐情況不斷進行探索和創新。通過革命斗爭和實踐,民族自決已經不再是停留在以前的口號和形式上,而且其內容也發生了相應的調整和改變。毛澤東在1934年1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爭取一切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環繞于蘇維埃的周圍,增加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壓迫少數民族得到自由與解放,是蘇維埃民族政策的出發點。”①
(二)紅軍長征時期到抗日戰爭之前這段時期的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初步形成
在長征途中,要經過云南、貴州、四川、甘肅、西藏等許多的少數民族聚集的地區。每次要經過少數民族聚集的地區時,毛澤東總是親自或者派人去考察和調查當地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和人情風俗等方面的情況,然后通過集體討論和研究,制定相應的民族政策和規定,再反復教育紅軍干部和紅軍戰士高度重視民族問題,高度重視與少數民族處理好關系的問題。教育紅軍干部和戰士要充分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要堅定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搞好與少數民族的團結,保證紅軍的順利通過和紅軍長征的最終勝利。
紅軍勝利到達陜北之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根據革命形勢發展需要,根據陜西緊鄰甘肅、寧夏回族聚集地區和蒙古族聚集的蒙古地區的實際情況,不失時機地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毛澤東主席的名義發布了對回族和蒙古族的兩個宣言,有效地防止和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為達到全面侵略中國和吞并全中國而利用“泛回教運動”、“大蒙古主義”挑撥民族關系,達到侵略和吞并全中國的陰謀和企圖。
三、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成熟
如何堅持抗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不僅僅是滿洲和蒙古地區所面臨的嚴重問題,也是中國各少數民族面對的問題,更是中華民族面臨的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中華民族面臨危亡的時刻,提出和制定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建立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主張抗日戰爭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全面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不是單純地依靠軍隊和武器進行的國民黨的片面抗戰,這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抗日民族政策的根本出發點。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審時度勢、認真研究和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抗戰的需要,對少數民族的民族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調整。
因為抗日戰爭時期的問題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全民族統一抗戰的問題,解決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中國共產黨就必須要制定適合全民族全面抗戰的實際情況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綱領,這樣就可以發動和組織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并肩戰斗,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趕出中國,實現全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解決民族抗戰和民族危亡的時刻,逐步調整了民族政策,并形成了新的民族綱領。
以后毛澤東在多次重要會議和重要報告中都提到和論述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對建立起全民族統一的抗日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對取得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重大意義。因為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陜甘寧邊區,陜甘寧邊區緊鄰蒙古地區和回族地區,都是蒙古族和回族比較聚集的區域,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決定在蒙古族、回族聚集的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41年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指導下制定了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文件就明確規定,要實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原則,建立蒙古族和回族的民族區域自治區,保證蒙古族、回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與漢族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在毛澤東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和初步的實踐,先后在陜甘寧邊區開展了一個蒙古族民族自治區和五個回族自治鄉的嘗試。這些嘗試和實踐的民族自治區域范圍比較小,規模也不大,但是民族區域自治區的建立,保障了民族區域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同漢族一樣享有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發展的權利,民族區域自治區有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權利,有發展本民族經濟文化的權利。這些民族區域自治區的建立,維護了民族的團結,動員了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參軍參戰,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充分說明了實行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理論的無比正確性,為以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政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四、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思想和政策也在實際生活中得到了認真執行和貫徹。
首先,毛澤東的關于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思想原則已經上升到法律層面。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協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溢民族主義,禁止民族間的歧視、壓迫和分裂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信仰的自由”。②《共同綱領》當時起臨時憲法的作用,《共同綱領》在法律上保障了各民族當家做主的權利,保證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共同綱領》廢除了幾千年來的民族剝削、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制度,保障各民族充分享受的權利和自由,保護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規定了新型的民族關系,開始了民族關系發展新的歷史進程。
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少數民族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幫助各少數民族實現向社會主義的跨越,這也是毛澤東民族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過程中,毛澤東十分尊重少數民族的各個階層的意愿和意見,實行逐步改革和逐步推進的方式進行,減少了民族土地改革過程中的阻力,保證了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
最后,毛澤東民族區域自治思想和政策被正確運用到處理西藏民族問題,順利解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順利實現了西藏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是我國民族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徹底的社會大變革。黨和國家為順利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依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采用了和平改革的方式。
[注釋]
①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