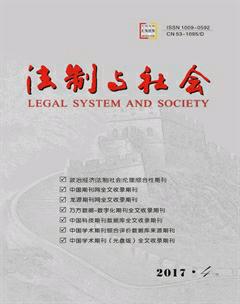民粹主義沖擊下的美國政治司法化與違憲審查
朱海文+賈御博
摘 要 現(xiàn)階段民粹主義在全球政治領(lǐng)域泛濫,美國亦不例外。而民粹主義對美國聯(lián)邦的司法分支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挑戰(zhàn)。無論是美國的政治司法化還是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違憲審查制度,都極度依賴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長久以來積累的政治權(quán)威和司法公正,而民粹主義的“反傳統(tǒng)、反體制、反權(quán)威”等特征,對于政治司法化和違憲審查制度來說無疑是致命的。可以說,在美國現(xiàn)行憲政體制下,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所代表的司法分支成為抵御民粹主義泛濫且危害美國政治社會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線,而如何保證其運用政治司法化與違憲審查制度實現(xiàn)這一目的,以及捍衛(wèi)其政治權(quán)威和司法公正是其關(guān)鍵之所在。
關(guān)鍵詞 民粹主義 政治 司法化 違憲審查 司法權(quán)威
作者簡介:朱海文,文山學院政法經(jīng)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賈御博,西北民族大學2013級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方向:憲法與行政法。
中圖分類號:D7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206
一、民粹主義思潮與美國政治
對于全球政治領(lǐng)域來說,201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民粹主義思潮在全球政治領(lǐng)域泛濫,對世界各國的政治勢力造成了嚴重的沖擊。 民粹主義在2016年中表現(xiàn)出的特點包括:在政策上,反移民、反全球化;在社會心理上,趨向于保守,重視本國的自身利益;在政治上,反傳統(tǒng),反對精英政治,反對已有的一些制度,反對政黨把持的民主選舉,傾向于強人政治;最重要的是,在理念上反對政治正確,反對自由主義。
美國亦不能置身國際民粹主義思潮沖擊之外,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就是其最好的例證。從特朗普表現(xiàn)出的政治傾向和其強人政治的特征來看, 充分體現(xiàn)出民粹主義思潮對其影響,而他的許多政策和言論也表現(xiàn)出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征,即反傳統(tǒng)、反權(quán)威、反全球化和反對移民政策,傾向于保守和內(nèi)顧。可以說,特朗普是一位典型的民粹主義總統(tǒng),但從美國憲政視角去思考,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更具憲政意義。特朗普當選總統(tǒng)一定程度上將會代表著美國政府行政分支的意志,在執(zhí)政過程中其表現(xiàn)出民粹主義的傾向,勢必與代表精英價值的國會和聯(lián)邦最高法院發(fā)生沖突,這種沖突不止是政治層面的,也包括法律層面的。
再進一步看待這個問題,行政分支與國會、司法系統(tǒng)的沖突,可能會通過政治司法化和違憲審查制度,轉(zhuǎn)化成一系列的憲法和行政法問題,這些問題的處理不僅是單純的法律問題,更代表著與民粹主義價值觀的正面沖突。一方面,民粹主義思潮的極左或者極右傾向需要以政治司法化和違憲審查予以抑制,使之不能對政治社會生活發(fā)生惡劣影響;另一方面,美國現(xiàn)階段出現(xiàn)精英與草根在價值判定上的溝通障礙,也需要通過政治司法化和違憲審查以理性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解決。
二、第一場“戰(zhàn)役”:2017年美國“旅行禁令”案
事實上,前文所述的美國行政分支與國會、司法系統(tǒng)的沖突并不是空穴來風。2017年1月27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暫停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索馬里、蘇丹以及也門等7個穆斯林國家的移民入境以及簽證發(fā)放,為期90天,還宣布在4個月內(nèi)禁止所有難民進入美國。這項“旅行禁令”在華盛頓州西區(qū)聯(lián)邦地方法院遭到挑戰(zhàn),并被詹姆斯·羅巴特(JamesRobart)法官的裁決所凍結(jié)。而在司法部上訴至聯(lián)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后,三位法官一致決定維持華盛頓州西區(qū)聯(lián)邦地方法院的裁決。這引發(fā)了以特朗普為首的行政分支與聯(lián)邦司法系統(tǒng)的沖突。在法院裁決被維持后,即使特朗普本人表示將上訴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但受制于美國的分散式違憲審查制度,其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以保證其行政令通過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司法審查。
從美國憲政視角進行分析,“旅行禁令”案有兩個焦點值得關(guān)注,即政治司法化的邊界與分散式違憲審查制度對行政權(quán)力的制約。
一方面,“旅行禁令”本身不僅僅是一個總統(tǒng)簽署的行政令,其本質(zhì)是政治政策的行政法化和外交問題,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轉(zhuǎn)變?yōu)橐粋€牽扯到具體個人法律權(quán)利的“案件”,這就為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出面對其進行違憲審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問題不審查”原則并不能排除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對“旅行禁令”的司法審查,這里就存在一個“政治邊界”的問題,政治司法化要求對該案件的審查必須排除在“政治問題”之外。原則上,“外交或國際問題”屬于“政治問題”,但顯然華盛頓州西區(qū)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和聯(lián)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并不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該禁令嚴重影響到持有美國綠卡的外國公民之出行自由權(quán)利,是一個典型的行政法問題,且該禁令由于缺乏必要的審查機制以辨認出極端主義恐怖分子,涉嫌違反憲法所規(guī)定“禁止宗教歧視”和“有限政府”的原則,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對該案件擁有管轄權(quán)。
另一方面,對以特朗普為首的行政分支來說,因“旅行禁令”與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發(fā)生的沖突是一場必輸?shù)摹皯?zhàn)役”。分散式的違憲審查制度使得對同一個有爭議的行政令在不同的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接受個案挑戰(zhàn),即使司法部上訴至聯(lián)邦最高法院,并取得有利判決,也無法阻止該禁令在其他案件中受到從別的角度發(fā)動的攻擊。 也就是說,相同的復雜訴訟程序可能會不停的出現(xiàn),導致“旅行禁令”實施的法律成本會無上限的提高,最后迫使行政分支改變“旅行禁令”中的相關(guān)規(guī)定。而實際上,司法部表示特朗普將會對“旅行禁令”進行修改以使其通過司法審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行政分支為了使該禁令得以實施,對聯(lián)邦司法系統(tǒng)的違憲審查做了必要的妥協(xié)和讓步。
本文認為,即使“旅行禁令”案在現(xiàn)階段并沒有在司法程序上真正意義的終結(jié),但鑒于美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分散式特點,“旅行禁令”的修改勢在必行,行政分支的在與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第一次沖突中獲勝的希望極其渺茫。而從美國憲政的視角來看,這次沖突還遠沒有結(jié)束。
三、民粹主義思潮對司法系統(tǒng)政治權(quán)威挑戰(zhàn)的影響
政治司法化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一項重要遺產(chǎn),它賦予法院從強形式和弱形式兩個方面保證憲法的實施,同時該案也改變了當時聯(lián)邦法院分支的弱勢地位。 但更應當注意的是,“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使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獲得了巨大的政治權(quán)威,這也保證其能夠合適且正當?shù)男惺惯`憲審查權(quán)。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從“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審判中獲得的政治權(quán)威之所以被服從和信任,且被良好遵守的一項重要原因,是其對美國憲法原則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堅持與捍衛(wèi)。而這勢必會與民粹主義思潮反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相沖突,導致其依靠對憲法原則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念之堅持與遵守而獲得的政治權(quán)威收到挑戰(zhàn)。
民粹主義思潮反自由主義傾向與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沖突,其產(chǎn)生原因是“草根”群體與“精英”群體的價值觀念與需求對話之溝通障礙所導致的。 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法官是典型的“精英”集團,并非民主選舉的結(jié)果,這也是其受到民粹主義攻擊的一個重點。事實上,美國精英政治所帶來的國內(nèi)和國際的變化并沒有給底層民眾帶來福利和改善其生活,然而民粹主義將其歸結(jié)于精英政治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念,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在具體案例上也無辜受到“牽連”,這種溝通不暢很難使法院系統(tǒng)的理念傳達到底層群眾中去,以抵御民粹主義思潮的擴散。民粹主義對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挑戰(zhàn)的思維邏輯極其簡單。其認為底層群眾生活困難,未能分享改革紅利是由于精英政治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念造成的,法院由精英集團構(gòu)成且贊同自由主義,因此民粹主義應當與法院對抗。不難看出,這套邏輯是極其混亂的,但即使是這樣非理性且毫無形式邏輯的論點卻有著大量的支持者,并且在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讓“政黨決定論” 出現(xiàn)了差錯,民主選舉的結(jié)果讓大家大跌眼鏡。同時,行政分支尊重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司法判決乃是一項上升為政治正確的憲法習慣,而特朗普統(tǒng)帥美國聯(lián)邦行政分支卻完全不顧這一憲法習慣,將會造成司法分支與行政分支在這一時期的相互關(guān)系產(chǎn)生不良影響。
同樣的思維模式也適用于行政分支與法院系統(tǒng)的沖突,但由于對自由主義價值觀念的質(zhì)疑(這種質(zhì)疑仍有很大的市場),已經(jīng)影響到美國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政治權(quán)威,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司法化與違憲審查制度的實施可能會如履薄冰,避免對民粹主義者的刺激以保證其能夠取得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shù)和其司法上的公正性與合法性。進一步講,民粹主義思潮在美國的泛濫對其精英政治的影響源于溝通機制的不通暢,這種思潮是底層民眾利益訴求的一種表達形式,但相對于精英團體,占社會絕大多數(shù)底層民眾的政治能力缺乏并不能是民主政治決策得出最佳答案,這既是民主制度的悖論,而這一不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象將從政治層面影響政治司法化和違憲審查制度的運行,并可能導致美國三權(quán)分立的平衡關(guān)系發(fā)生改變。
總之,美國行政分支因“旅行禁令”而與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發(fā)生沖突,雖不會導致在政治制度方面發(fā)生形式上的改變,但三大政治分支的政治力量對比有可能發(fā)生微妙的變化,而這一變化需要予以一定時間的關(guān)注。
四、啟示
視角回到國內(nèi),不難發(fā)現(xiàn)民粹主義思潮在我國也有泛濫的趨勢,現(xiàn)階段主要集中在輿論領(lǐng)域。憑借著網(wǎng)絡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自媒體”時代隨之到來,“人人都有麥克風”已經(jīng)成為社會現(xiàn)實,而民粹主義思潮憑借這網(wǎng)絡傳播技術(shù)的高效率,在基層群眾的認識領(lǐng)域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傳統(tǒng)的價值判斷標準和智識體系難以在“自媒體”時代起到使不同意見達到整合的作用。
我國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標準也面臨著民粹主義的挑戰(zhàn)。在轉(zhuǎn)型時期,人民法院的改革方向從實質(zhì)上講,是以公正審判、樹立司法權(quán)威為目的。而民粹主義的反權(quán)威傾向,會使人民法院的裁判受到各種各樣的質(zhì)疑,其中不乏有意義的真知灼見,但無端的指責、非理性的評價和“陰謀論”也夾雜其中,且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大肆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人民法院的判決應當從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fā),體現(xiàn)出“人民性”的特征,某種程度上亦要迎合群眾的意愿,以達到良好的社會效益和政治目的。但在民粹主義思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如何辨別民粹主義言論和人民的法律利益訴求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xiàn)實問題。事實上,與美國聯(lián)邦法院系統(tǒng)的對極端思想影響政治社會生活的制動閥作用不同,我國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更多的任務是解決司法糾紛,為經(jīng)濟建設(shè)和政治體制改革保駕護航。司法判決具有極強的專業(yè)性和形式邏輯特征,盡管與道德價值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但卻截然不同。人民法院的人員構(gòu)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相對于基層群眾而屬于精英團體,其思維體系和語言體系與“草根”團體的基層群眾大為不同,也會出現(xiàn)類似于美國式的溝通障礙,這種溝通障礙也會為民粹主義思潮的泛濫提供有利條件。
綜上,美國“旅行禁令”案的經(jīng)驗教訓告訴我們,民粹主義源于精英階層團體和“草根”團體的在價值觀念方面溝通不暢,是一種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表達。但如何將這種表達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且不會因為這種極端思想影響到政治與社會生活則是一個系統(tǒng)性的工程。本文認為,我國現(xiàn)階段也存在這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的趨勢,人民法院系統(tǒng)的司法職能難免受到其影響,那么如何將這種思潮予以引導與控制,在轉(zhuǎn)型時期幫助構(gòu)建法院系統(tǒng)權(quán)威,對司法體制改革來說十分重要,如果不能良好的處理民粹主義思潮對司法系統(tǒng)的沖擊,基層群眾因司法糾紛而產(chǎn)生的社會矛盾將會越來越多。
注釋:
季思.2016年世界政黨政治看點及前景展望.當代世界.2017(1).21-23.
孫晶.新權(quán)威主義在西方政治中“抬頭”.人民論壇.2017,1(上).24-26.
張千帆.憲法學導論——原理與應用.法律出版社.2008.184-185,176-178,162-163.
歐愛民.憲法實踐的技術(shù)路徑研究——以違憲審查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7.35-41.
李良榮、徐曉東.互聯(lián)網(wǎng)與民粹主義流行——新傳播革命系列研究之三.現(xiàn)代傳播.2012(5).2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