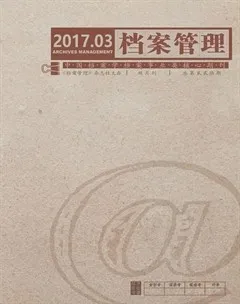試析公示性公告的文體理據及行文問題
韓雪松
摘 要:內容的確定性不是公告的文體屬性,信息確定與否不構成公告和公示的本質區別,以公告發布公示信息有充足的文體理據,黨政機關對外正式發布重要的公示事項應以公示性公告行文。公示不具備法定公文的特定效力和規范體式,不應越位侵襲公告的文體功能和行文領域,公示的“法定公文化”傾向應予以警惕。公示性公告的使用必須嚴守文體規范而不逾功能界限,黨政機關內設機構不具備對外正式發文的權限,不應越位制發公示性公告。公示性公告與公示性通告、公示性通知都是合理可行的公文種類,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定位和明確的文體邊界,三者之間是相對獨立而又彼此互補的共生關系。
關鍵詞:公示;公告;文體理據
1 公示的“名分”問題及其“法定公文化”傾向
作為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在一定范圍內公開發布信息、征求意見、接受監督的知照性事務文書,公示這一文體的發文頻次日漸繁多,所起作用日漸增強,使用范圍日漸廣泛,文體地位日漸提升。但是公示并不是法定行政公文,不在《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下文簡稱“條例”)規定的公文文體之列,還不是“黨政機關實施領導、履行職能、處理公務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規范體式的文書”,還沒有公告、通告等文體所具備的法定效力和特定格式。事實上,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利”,一些公文學者希望在公文法規的制度層面上為公示正名,使其有與自身使用頻度、文體地位相對應的“名分”。[1]這種“正名”的努力應該是出于公文處理科學化的考慮,但公示能否在未來的法定公文譜系中獲得一席之地,還有待長期觀察,且恐不樂觀。
沒有法定公文之“名”,也就不應有法定公文之“實”,公示不應以與15種法定公文“同等效力”的面貌出現在公文制發的規定性程序中,不應替代公告、通告等泛行文體在公文系統中的法定地位,不能越格以法定公文的姿態發布需要社會周知的行政事項,更不可能作為黨政機關對外正式發布公示信息的首選文體。
值得警惕的是,公示在當下的政務文書處理實踐中偏多過繁,有混亂無序之嫌,已經呈現出“法定公文化”的失序現象。有的單位拔高規格制發公示,以事務文書代替法定公文,擠占了公告的行文領域和功能區段,破壞了“條例”所構建的公文體系的穩定性。原因何在?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公示的法定文書“資質”應有而未有,問題在于“條例”在本時期的局限性,屬于公文制度不健全;公示的用途特殊不可替代,公示終會有“名”有“實”,目前只能“先上車后補票”。這種觀點缺乏理據,我們不贊成,因為用公告進行公示并非錯誤。
2 用公告進行公示的文體理據
反對用公告進行公示,第一個理由在于內容確定性方面。一般認為,公告所發布的內容具有確定性,是將已經決定的、不可變更的重要事項對外呈現,而公示所發布的內容不具有確定性,是尚未最終決定的事項,二者在內容定位上剛好抵觸,進而,對內容有“確定性”規約的公告文體不能內嵌任何公示信息。這種論斷否定公示性公告的合理性,公告不應涉及公示性內容。這值得商榷。
按照“條例”的規定,公告適用于“向國內外宣布重要事項或者法定事項”,這里并未包含對公告文體“確定性”的明確限定,沒有規定公告傳播的內容一定是凝固不變的。[2]它所宣布的“重要事項”并非僅僅是靜態的終結性的名單或統計結果,也可以指動態的過程性的措施或人事安排,因為二者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信息,都屬于黨政機關的行政事項,都在公告的合理發布范圍之中。可以說,凝固不變的數據表單是重要事項,持續推進的施政行為也可以是重要事項,不能毫無理據地把后者排除在公告的文體功能之外。舉例說,海關總署增列海關監管方式代碼,財政部實施境外旅客購物離境退稅政策,國家知識產權局開通中美優先權文件電子交換服務,以及文化部辦公廳公示第十七屆群星獎獲獎作品名單……這些都屬于國家行政機關開展特定的行政活動,在事項的性質上沒有什么不同。既然前三者能夠分別以公告的形式制發(即《海關總署關于增列海關監管方式代碼的公告》《財政部關于實施境外旅客購物離境退稅政策的公告》《國家知識產權局關于開通中美優先權文件電子交換服務的公告》),那么文化部辦公廳以公告的方式來公示獲獎名單(即《文化部辦公廳關于公示第十七屆群星獎獲獎作品名單的公告》),也自然合法依規,無可厚非。[3]雖然公示性公告所承載的公示信息在發布后還需依照反饋意見進行適當的調整,但此類公告只是針對公示階段的事項而非針對公示結束后的結果進行傳播,公示行為本身就已經作為行政事務在公告中被主動披露,并無不妥。可見,內容的確定性不是公告的文體屬性,信息凝固與否不是公告和公示的本質區別。
否定公示性公告的第二個理由是,從文體風格而論,公告的文風莊重嚴肅、大氣簡明,具有公文體系內的“貴族”品格,彰顯了權威性和公信力;相反,公示的風格平實具體、語言真誠質樸,關系著群眾的切身利益,更接地氣,因此二者差異明顯、區隔較深,不能混淆,更不能用公告來進行公示。這也很難站得住腳。公告與公示的主要區別,并不在于所發布信息重要性的高低或所使用語言權威性的強弱,而在于,是不是法定公文、有沒有法定效力。可以說,在公務文書縝密的文體系統中,公告與公示并不是共處一個層面上的文體,二者的使用環境和制發程序迥然有異,在風格上對二者所進行的比較,對于公示性公告的合法性闡釋而言沒有太大意義。公示這一動作和公示這一文體兩者并不同一,公示行為當然可以在公示文體中得以集中表現,但這一行為并非是公示文體專屬的表現內容,“適用于向國內外宣布重要事項”的公告也可以進行公示。公示性公告并不會造成公文語言的雜糅和風格的混亂,因為所有的公文語言都應莊重平實,風格皆是嚴肅質樸,語體風格問題并不構成以公告進行公示的真正障礙。作為一般事務性文書,公示絕不該以法定文書的身份擠占公示的應用空間;而當需要凸顯公示活動法定效力的時候,以公告進行公示自然是正確的文體選擇。以民政部2016年11月14日《2016年度全國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公示公告》為例,該公告公布了“2016年度全國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名單”,向民眾公示北京市東城區永定門外街道安樂林社區等1455個社區為示范社區,以公告文體來承載公示內容,而沒有把文件錯誤地寫成《民政部關于2016年度全國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名單的公示》,可謂文體選用規范合理,語體風格莊重穩妥,語言表述精當準確,是一篇典型的公示性公告。[4]
3 違規使用公示性公告的三個問題
公示性公告不是不能使用,而是不能違規使用。違規使用的情況以如下三種較為常見:一是部門內設機構用公告進行公示;二是錯用公告發布非重大的一般性公示事項;三是寫作公示性公告時未能設定充足的公示周期進而減損公示效果,下面分別予以說明。
首先,“條例”第十七條規定:“部門內設機構除辦公廳(室)外不得對外正式行文。”因此,類似于“××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人事司”“××林業局發展規劃與資金管理司”“××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人事培訓司”這類黨政機關內設機構,不具備對外正式發文的權限,不應正式對外發布公示性公告。但從公文實踐來看,這類由部門內設機構發布的公告在機關網站上并不罕見。事實上,這類內設機構如確有公示信息需要發布,應該改用公示行文。例如,廣東省教育廳高等教育處(教育廳的內設機構)為了公布“2016年度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推薦立項匯總公示表”,于2016年10月20日發布《2016年廣東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項目擬立項名單公示》,沒有越格用公告來行文,而是準確地以公示發布匯總公示表,文體選用恰當理性,行文方式準確合理。
其次,不可事無輕重都用公告進行公示,黨政機關正式對外行文時,要如實地根據所公示內容的重要程度,慎重選擇公告或通告等文體。但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通告能用來進行公示嗎?有專家撰文指出,通告的使用目的具有行政性,對行文對象具有強制性,并且所公布的內容具有具體性,所以與公示性內容拉大了距離,認為通過通告發布公示信息不妥,還是直接使用公示更為方便。我們對此并不贊同。事實上,通告本身就存在“遵守性通告”與“周知性通告”之分,所謂強制性并非適用于通告的所有類型;公示活動是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公示行為和通告文體都具有行政性,通告的使用范圍不受所謂行政性的影響。可見通告具備發布一般公示性內容的文體功能,公示性通告簡明高效、平實具體、合規可行,無需由公示來越位發揮。15種法定公文構成了科學完備的公文系統,辦文實踐應尊重“條例”的權威性,從“條例”中選用文體,而不應再在事務文書中違規借用。
公示性通告與公示性公告功能有異、互為補充。只有向國內外發布重要的公示事項時才可以公告行文,基層單位不能動輒發公告來公示,如需要在一定范圍內公布應當周知的公示事項,用公示性通告行文即可,以便做到簡明適中、文體得當。例如2016年11月17日中共深圳市寶安區委組織部發出的《寶安區關于干部選拔任用公示的通告》,系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對擬選拔任用的寶安區環保水務局局長人選進行任前公示。[5]所公示的內容屬地方性人事任免事項,限于寶安區一地,規格不算太高,范圍較為有限,沒有事關全局的宏觀意義,沒有用公告行文,可謂恰如其分。
最后,以公告進行公示,需要安排充足的公示時間,以便公眾參與和反饋。公示性公告以公告為文體外殼、以公示為行文目的,因此,所發布的公示信息是公示的主體性內容,需要按照公示活動的專業流程來處理和把握,而缺少足夠的公示時間,就等于消滅了公示活動的基本屬性。可見,公示性公告的公示周期不能違規壓縮,以致公眾無法正常監督。2014年1月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決定“實行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前公示制度”,第四十一條規定,“公示內容應當真實準確,便于監督”,強調“公示期不少于五個工作日”,而且“公示結果不影響任職的,辦理任職手續”,某一公示對象在被最終確認之前,若有單位及個人對公示內容有任何異議,都可以向公示單位及時提出。在公示性公告寫作過程中,要強調公示的民主性和科學性特征,所公示的各類事項應當鼓勵大眾參與,接受百姓監督,并設置充分合理的互動周期,以便集納民眾意見,實現公示目的。[6]以浙江省民政廳《2016年“浙江省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公示公告》為例,該公告旨在發布第六批“浙江省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名單,杭州市上城區湖濱街道的吳山路社區等155個社區名列其中,公告中寫明的公示時間為2016 年10月28日至 11月10日,公示周期為兩周,時間較為充裕,沒有以“走過場”的態度簡單敷衍,能夠完整履行條例規定的公示程序,可以及時接受民眾的反饋意見,符合公示的常規流程。[7]
4 公示性公告與公示性通知存在功能互補關系
黨政機關的公示活動可分為系統內部公示和面向社會公示兩種,二者的功能地位和行文范圍各不相同,前者是指黨政機關在其內部公示信息、接受監督,不對社會大眾征詢意見,公文接受者的數量是有限的、身份是明確的;而后者與之相反,是黨政機關向人民群眾廣泛發布公示事項,公文接受者的數量是不設限的、身份是不確定的。
從選用法定公文文體來看,黨政機關系統內部的公示活動應主要選用通知行文,其主送機關是具體、明晰的,基本是下行文,如河南省教育廳2013年7月1日所發《關于對2013年度中原名師進行公示的通知》,旨在發布《2013年中原名師擬任名單》,擬確定鶴壁市高中的周照鵬等10名教師為2013年度“河南省中原名師”并就此進行公示。該份公示性通知有確定的主送機關,即“各省轄市、省直管試點縣、重點擴權縣(市)教育局,省直有關學校”,收文單位限于河南教育系統內部,并強調了“單位提出的異議,須在異議材料上加蓋本單位公章,并寫明聯系人工作單位、通訊地址和電話”,是一份文體選用正確、公示意圖清楚、語體風格恰當的下行文。[8]
有人認為不能以通知進行公示,理由是:通知文體功能繁多,應予減負,以通知公示會導致其文體負載過大;而且公示旨在發揚民主以及強化監督,若公示內容寓于通知之中,則會拉大發文機關和人民群眾的距離,對反饋效果產生消極影響。這種看法并不全面。準確地說,通知完全可以用于公示,但不能用在所有的公示場合。“通知”具有周知性,“適用于發布、傳達要求下級機關執行和有關單位周知或者執行的事項”,可以發布供民眾周知的公示信息;但此處無論是“下級機關”還是“有關單位”,都是黨政機關、職能部門,而非社會群眾、普通百姓,因此通知在發布公示內容時應限于黨政系統、機關之間。
另一方面,黨政機關面向社會的公示活動應選用公告、通告等行文,目標讀者是社會公眾,是典型的泛行文,一般沒有主送機關,如前述《文化部辦公廳關于公示第十七屆群星獎獲獎作品名單的公告》,此文面向公眾廣泛征求意見,強調“提出異議者須提供本人真實姓名、工作單位、聯系電話等有效聯系方式,以便核查”,提出“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異議不予受理”,并列示了反饋意見所需的聯系電話、電子郵箱、通訊地址等內容,泛行文特征清楚,行文言簡而意明,未寫明主送機關,符合公告的文體定位。
我們反對在公示活動中模糊公示性公告與公示性通知文體邊界的做法,堅持認為面向社會各方面和普通民眾廣泛征詢公示意見時不能以通知行文。通知不是公告之類的泛行文,不可越位侵入公告、通告的文體領域,公示性通知與公示性公告二者彼此獨立、互不替代,但應各安其位、互為補充。
參考文獻:
[1]張宇,徐菲.給公示一個“名分”[J].秘書之友,2009(9):26~28.
[2]閻杰.公告寫作探析[J].檔案管理,2011(1):72~74.
[3]文化部辦公廳.文化部辦公廳關于公示第十七屆群星獎獲獎作品名單的公告.2016-10-23. 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3/content_5123375.htm.
[4]民政部.2016年度全國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公示公告. 2016-11-14.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611/20161100002431.shtml.
[5]中共深圳市寶安區委組織部.寶安區關于干部選拔任用公示的通告.2015-12-9.http://www.baoan.gov.cn/xxgk/xwzx/tzgg/201512/t20151209_658736.html.
[6]王安應,田更新.公示性文件該用何文種?[J].秘書,2003(10):11~13.
[7]浙江省民政廳.2016年“浙江省綜合減災示范社區”公示公告.2016-10-28.http://mzt.zj.gov.cn/il.htma=si&key=main/06&id=8aaf801557e58e5701580a521c08030b.
[8]河南省教育廳.關于對2013年度中原名師進行公示的通知.2013-7-4.http://www.haedu.gov.cn/2013/07/04/13729203375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