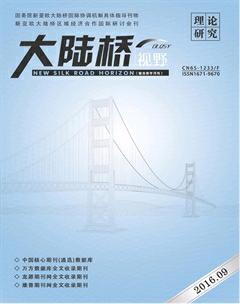從習俗型政府信任到契約型政府信任
【摘 要】習俗型政府信任中,國家以宗法組織形式為基礎擬制生成,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也有著一條割不斷的“自然臍帶”,不屬于理性建構的范疇,而是在較為穩定的生活共同體內自然而然地生成的。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契約型社會信任關系框架下,人們自覺地對自己的角色加以定位,重建相互之間本無所期待的關系,政府與公民之間在遵循規則方面存在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
【關鍵詞】習俗型;政府信任;契約型
一、習俗型政府信任
在農業社會的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強制性權力是進行社會統治的直接力量。統治者為了獲得權力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往往為自己涂上一層道德色彩,甚至努力通過道德與政治的同構去謀求統治權力的權威。為了使這種權威不至于流失,統治者必須通過強化兩個方面的社會構成來維護統治的穩定性:其一,在社會結構的各個單元內強化同質性的等級結構;其二,必須限制人口流動,即把人們穩定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等級結構的強化實際上起強化權力作用力的效果,而對人口流動的限制,一方面保證了等級結構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使人們處于一個“熟人社會”之中。既然人們生活在熟人社會之中,那么在人們之間形成一種信任關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事實上,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農業社會,由于人們祖祖輩輩生活在相對固定的區域,不僅人們的經濟生活具有很大的自然特征,而且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也建立在人們自然聯系的基礎上,具有自然性的特征。同人與自然之間那種直接的、狹隘的關系相適應,是尚未完全斬斷其自然臍帶的、以家庭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最初社會關系,而且,國家也是以宗法組織形式為基礎擬制生成的,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也有著一條割不斷的“自然臍帶”,并不屬于理性建構的范疇,而是在較為穩定的生活共同體內自然而然地生成的。把這種信任關系與近代以來理性化了的信任關系加以區別,稱之為習俗型的信任關系是比較準確的。
在哈貝馬斯從歷史哲學視角對合法化危機進行的深刻闡發中,可以對習俗型政府信任關系生成、維持和瓦解的歷程得到充分的理解。在他看來,“原始社會形態”由于人口的增長及相關的生態因素,特別是由于交換、戰爭和征服而帶來的種族間的依賴關系等,打破了按照親緣關系組織起來的社會所具有的有效的控制能力,摧毀了家庭認同和部落認同。進入“傳統社會形態”后,社會組織原則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階級統治。隨著傳統官僚制統治機器的出現,從親緣系統中分化出一個控制中心,使得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從家庭組織形式轉為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親緣系統的權力和控制的主要功能轉讓給了國家。以統治機器和法律工具為一方,以虛擬論證和道德系統為另一方,二者發生了功能分化,由它們共同提供合法性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整合可能存在的潛在的利益沖突,求助于傳統的世界觀和常規的國家倫理,后者同樣依賴于傳統且具有抵御普遍性交往形式的特征,統治秩序仍然可以得到維護。
但與傳統社會形態分配關系制度化相伴隨的是權力等級,這種等級結構與規范系統和論證系統的有效性之間存在著矛盾:前者使依靠特權占有社會財富成為一種通則,后者則不允許公開進行剝削。對于這一矛盾,雖可以用意識形態對于虛擬的有效性要求的保障暫時加以解決,卻不可能長久地被掩蓋,只能在強制性權力關系中得到控制,而由控制導致的危機不可避免。
二、契約型政府信任
在社會學意義上,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出現的社會背景是一個“熟人社會”開始瓦解,“陌生人社會”開始興起的歷史過程,工業社會的發展已經開始告別“我們大家都是熟人”的“鄉土社會”,因為“熟人”的特殊主義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阻礙。由此,“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
在這個社會中,管理型社會治理體系已不可能通過強化習俗型信任關系來獲得合法性及社會秩序,它需要新的信任機制出現,即從原本直接信任轉變為在媒介作用下的間接信任。也就是說,當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需要進行改造,這種改造的實質就是根據陌生人之間的交往需要而建立起契約型的信任關系。
如果說熟人之間的信任有其自然的基礎,那么要在陌生人之間達致信任,顯而易見,是自然因素無法完全提供的,需要找到外在中介在陌生人之間搭起信任的橋梁。這時,在社會經濟交往中,伴隨著市場化進程而被普遍運用的契約,為陌生人之間建立信任關系提供了賴以利用的媒介。當然,這種媒介轉換為一種新的信任機制的工作,是力圖獲得秩序的政府去完成的。出于謀求承認、獲得合法性的要求,政府乃至整個社會治理體系有意識地強化契約精神,將市場交換意識運用于政治社會領域,以公民對法律的遵從為基本要求,以個體的利益保證和社會的安全穩定為條件,獲取公民承認和信任。
這一過程中,在管理行政中首先產生的是契約型政府信任關系,也正是由于管理行政對契約秩序的強化,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也根據契約精神而被加以改造了,從而出現了契約型社會信任關系這一新的信任關系類型。
在西方文明歷史進程中,以西歐城市自治中市民階級的發展為基礎,契約秩序的最終結果是現代國家的浮現。在韋伯看來,存在于現代社會中的現代國家包含以下內容:其一,三權分立且行政和司法受立法制約;其二,政府依法治理;其三,權威的普遍性和約束力;其四,合法政府可以合法地動用武力。法律秩序、官僚制、強制性司法權和對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而歷史發展中,現代國家的諸方面也的確是隨著限制權力的一系列規定獲取正當性而出現的,政治社會則是這一整套規定構成“法律秩序”的唯一正式的創造者。
在宗教啟示和神圣傳統的信念煙消云散之后,建立在自然法基礎上的法律秩序正當性曾經是現代政府唯一可資利用的權威性資源。自然法觀念依賴于一種形式上的假設:如果被頒布法律的條文出于自由人的契約,或與以協議為基礎的合理秩序原則相一致,就是正當的。這種契約理論的基本原則是保障個人獲得財產、處置財產和人身的自由,它徹底否認了在家產制和封建統治下存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只要契約沒有侵犯不可剝奪的自由,法律就是正當的,因為理性告訴人們,它們與“事物的自然本性”相一致,而這種本性是人和上帝都無法更改的。正是這種源于契約理論的自然法,為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的制度設立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現實政權的合法性,也成為契約型政府信任關系確立的理論淵源。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契約型社會信任關系的確立是社會法制化的結果。它的邏輯進程是:在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之后,人們在法制的框架下自覺地對自己的角色加以定位,重建相互之間本無所期待的關系。正像齊美爾所指出的那樣,政府與公民之間在遵循規則方面存在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政府實際上向公民保證:這是我們期待你遵守的規則。如果你遵守它們,我們就會保證它們就是適用于你們行為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契約型信任關系作為一種結構性關系,可以看作未納入成文法體系中的“不成文規則”,它意味著這樣一種預設:政府與公民之間是相互獨立的交換實體,市場法則是雙方買賣的黃金律。或者說,契約型政府信任關系將市民社會中所依據的對等原則貫穿于治理領域。也如科耶夫所做的解釋,不同于平等原則的對等原則,是一種交換性的平等,是基于契約性的公正原則。在近代以來的多元利益分化的社會,建構一種調整個人利益的法律原則是必需的,這個體系并不是給予每個人以形式平等的法權,而是建立一種實質上的交換。這種法權原則在法的作用過程中,發揮著無形卻巨大的作用:它統攝了法律、契約與邏輯之間的理性主義關系。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5 年.
[2]姜占奎(臺灣):《行政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5年.
[3]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9年.
作者簡介:
孟衛軍(1972-),男,湖北武漢人,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講師,從事社會信任、就業失業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