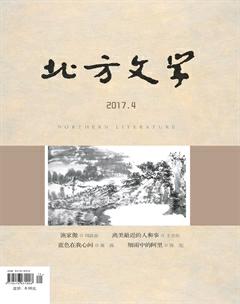竹林七賢研究文獻綜述
史繼虹
摘要:竹林七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文人團體,他們放誕、不為統治者所拘束。現在研究竹林七賢的文學成果總體上成熟,但是在一些細微的方面還有待討論。
關鍵詞:竹林七賢;文獻綜述
竹林七賢作為古代文學史中一個貢獻很大的團體現在研究成果已經比較成熟了,但是還有一些方面可以創新,下面將要討論一下對于竹林七賢的研究。現有的對于竹林七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方向。
第一、對于竹林七賢的整體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竹林七賢的命名的由來,真實性以及討論等。王曉毅在《竹林七賢散論》(《山東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中指出了不同于學術界的觀點,他認為相比于竹林七賢的聚會時間是高平陵政變后的嘉平時期更應該是說在高平陵政變的這個時間段七賢的政治行為和思想更突出的表現出來了,而竹林七賢則應該活躍了更長的時間。蘇雯在《竹林七賢研究》(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中也考證了對七賢作為竹林之游的先后順序,文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資料以及七賢的作品產生的時間得出了結論,不同的是作者認為竹林之游時間是相當短暫。之后作者通過了先天稟賦、親屬關系、同源關系、社會地位、個人遭際、成長環境、興趣愛好等等許多方面仔細的對比了竹林七賢的親疏關系。
第二、竹林七賢思想研究。行為是思想的反映,思想是行為的指導,那么什么樣的思想統領了竹林七賢呢?在魯紅平的《竹林七賢與竹林玄學》(《西北師大學報》2001年第1期)中作者在開頭提出為什么竹林七賢之間差別很大還是能夠統一交游于山林,隨后作者就給出了答案——老莊之學,這個統領于他們之間的思想讓他們不顧年齡、地域、個人習慣之間的差別,同樣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老莊之學對他們的深深的影響。老莊之學不僅是生活行為的準則,在那個政治黑暗的年代,七賢的大部分都沒能逃出政治的迫害,同樣老莊之學也是他們進入黑暗政治后的處世準則。閻秋鳳在《竹林玄風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中提出因為當時司馬氏統治時期的黑暗政權和虛偽矯飾的禮法之治,竹林名士試圖重構一種以莊學為指導的任情自然的情理關系,以“越禮任情”、“越名任心”與虛偽的政權抗衡,以放達、叛逆的行為來表達內心的悲憤和苦悶,于重情尚真中追求思想解放和人格自由,于任情自然的藝術情調中彰顯人生的意義。
第三、從竹林七賢生活行為來看酒、樂與其關系。曾春海在《竹林七賢與酒》(中州學刊2007年第1期)中具體分析竹林七賢七人各自的酒品以及對飲酒方式的不同描寫,令人驚嘆。七賢善飲,亦表現出不同的酒量、酒德與酒品。阮籍的飲酒是全身避禍,是酒遁,有時借酒公然向名教權威挑戰,亦借酒發抒率真性情。嵇康喜飲,而從道家清心寡欲立場上更反對酒色,但也認識到了飲酒怡養身心、營造生活情趣的正面價值。相較而言,劉伶的飲酒是痛飲豪飲,他是在借酒所催發出來的原始生命力,使其心靈超脫。綜之,面對政局的多變和人生的無常,通過飲酒,來提升心境以消解是非、榮辱、生死、苦樂的偏執,企求臻于與道合、逍遙自適的超世俗之至境,這是七賢及多數士人飲酒心態的普遍寫照。竹林七賢生活的正始時期一類名士以服藥、矯飾為尚,這種風尚流行上至朝堂下至貴族就猶如司馬氏統治后的畸形政權一樣,竹林七賢則是另一類名士的代表,他們放浪形骸、飲酒彈琴,用自己無聲的行為對抗著虛偽變形的儒家禮法。
第四、單獨研究阮籍、嵇康這種群體帶頭人的成果。阮籍和嵇康都是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他們流傳下來的作品在七人中比較多有一定的研究價值。阮忠在《論阮籍、嵇康詩歌的文化品格》(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中詳細分析了阮籍、嵇康在文化品格上表現出的三重品格。阮籍和嵇康的一生就是以游仙詩表達的向往神仙生活同時兼具儒家要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熱情和主導他們的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禍的老莊思想三者交織,構成阮籍、嵇康詩歌文化品格的復雜性,從而造就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諸多矛盾狀態。韓國學者崔宇錫有《魏晉四言詩研究》(巴蜀書社2006年)列有專章,他認為“其四言雖同樣抒發抑郁、傷懷之情,但大體措辭溫婉,情緒較五言《詠懷詩》平和得多,似乎仍不失‘溫柔敦厚之詩教觀念。”
總體上來說,學術界對于竹林七賢的研究已經有了較豐富的成果,要想創新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困難的,但是在一些細節方面的研究還是有可取之處的,比如山海經對于阮籍的五言詩有很大的影響,從中可以看出阮籍向往避禍的心態。竹林七賢的行為和文學作品有許多值得后人學習的地方,對中國文學史研究也有很大的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1]王曉毅.竹林七賢散論[J].山東社會科學,1991(2).
[2]蘇雯.竹林七賢研究[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3]魯紅平.竹林七賢與竹林玄學[J].西北師大學報,2001,1.
[4]閻秋鳳.竹林玄風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5]曾春海.竹林七賢與酒[J].中州學刊,2007,(1)
[6]阮忠.論阮籍、嵇康詩歌的文化品格[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9(6).
[7]崔宇錫.魏晉四言詩研究[M].巴蜀書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