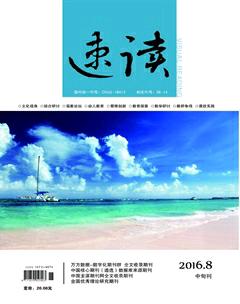《山海經》中動物的命名規律及其文化蘊意
林逸嵐
摘 要:《山海經》篇幅不大,卻包羅萬象,記載大量動物名稱。通過對動物名稱的探究,總結出鳴叫聲、外形特征、生活習性三種命名規律,發現其背后蘊含的文化意義。
關鍵詞:《山海經》; 動物;命名規律;文化意蘊
自古以來,《山海經》以“奇書”著稱。正如《西山經》所說“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書中講述的眾多鳥獸、蟲魚、草木正是其奇之所在。
《山海經》描繪的充滿人神鬼怪、奇珍異物的瑰麗世界里,關于動物的描寫尤為引人注目。書中描寫的動物種類繁多、形態各異、名字多樣。其種類大致可以分為鳥、獸、蟲、魚四類。據統計,《山海經》中描寫了117種鳥類、172種獸類、77種魚類、24種蟲類。這些對動物的記錄和刻畫,折射出先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探究這些動物的命名規律,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蘊,從而透析先民認識世界的途徑和心里特征。
一、命名規律
1.以動物之鳴聲而得名
動物之間的鳴叫聲是區別不同種類動物的重要表征,因此先民往往根據這點來為動物命名。這種命名方式在鳥類命名中尤為普遍,魚類中只有一種,而在蟲類中沒有體現。
(1)鳥類。《南山經》中寫到“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先民認為鳥的鳴叫像是在呼喊自己的名字,所以根據其鳴叫聲來為之命名。
畢方鳥的命名正是如此,《西山經》中有“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義之山,……有息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鬢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訛火。”袁珂先生將畢方鳥得名的緣由梳理的非常清楚:“實則‘畢方當是‘熚煿 一詞之音轉。《神異經· 西荒經》云:‘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煿而出,臊皆驚憚。‘爆煿即‘熚煿也。或又作‘煿熚,《集韻》曰:‘竹火聲。‘爆煿、‘熚煿,蓋無非竹木燃燒時嘈雜作聲也。音轉而為‘畢方故《淮南子》云:‘木生攀方。《廣雅》云:‘木神謂之畢方。《駢雅》云:‘畢方兆火鳥也。則‘畢方者,生于竹木之火,猶今之所謂‘火老鴉也。神話化遂為神身畢方,或‘見則其邑有訛火,或‘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又轉而為致火之妖物矣。”可見,畢方本是木、火之神,得名于竹木燃燒使的聲音,古人以為這是畢方鳥的鳴叫聲,故名之。
此外,以鳴叫聲命名的鳥類還有鴸、顒、鳧徯、?等等。
(2)獸類。《北山經》中的孟極(“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天馬(“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丩。”)、??(“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其名曰??,其鳴自丩。”)和《東山經》中的從從、狪狪、軨軨、犰狳、朱獳、精精、當康都是根據其叫聲來命名的。
2.以動物之形體特征而得名
視聽是人們感知世界最直接的方式,先民通過鳴叫聲區別和命名動物,同時也根據直觀觀察外貌特征來命名動物。
《海內經》中提到“有孔鳥”,根據袁珂先生的注釋“《爾雅》卷十三云:‘孔雀生南海,尾凡七年而后成,長六七尺,展開如車輪,金翠斐然。”,我們不難看出孔鳥因為其體型大而得名。
《西山經》中有“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可見豪彘是一種體型較大的野豬。《海內經》中的“封豚”也有大豬之意。
《東山經》中的箋魚以“其喙如箋”而得名。
3.以動物之生活習性而得名
先民對動物的觀察,不僅停留在外形感知,還在與動物爭奪生存資源的過程中對動物的行動特征、生活習性有更深的認識,進而據此為動物命名。
《中山經》中的鳴蛇以“其音如磐”得名,猿以其善于攀援得名。《西山經》中寫道“西次三山之首,曰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尾而善投,名曰舉父”。“舉”有舉起、抬起之意,“舉父”以善于舉石投人二得名。我認為,舉石投人對動物而言有夸大其力量之嫌。因此,“舉父”一名也體現了先民的力量崇拜思想。
二、文化蘊意
1.先民探索世界的嘗試
先民在為動物命名的過程,實質上是對自然界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對事物認識流于表面、對成因分析略有偏頗等世界探索的特征,鮮明地反映在動物的名稱上,成為后人追溯原始社會生活的窗口。動物的命名依據從鳴叫聲、外形等表征到生活習性、行為習慣等規律性特征的過渡,也體現了先民對世界的探索由淺入深的一個過程。
2.崇拜動物圖騰的思想
恩格斯認為,“人在自己的發展中得到其它實體的支持,但這些實體不是天使而是低級的實體,是動物,由此產生了動物崇拜。”《山海經》中對動物的大量描寫保留先民圖騰崇拜的資料。命名理據反映對動物的崇拜心理。一是人和動物形象雜糅,如人面狗身的“山獩”、人面牛身的“猰貐”、人面鳥身的“竦斯”等;二是夸大動物的力量或本領,如“舉父善投”、“巴蛇食象”等。
在物質生產方式落后、生產效率低下的原始社會,先民的生產成果極少,對自然界的生存依賴性導致了對自然界的恐懼和禁忌,久而久之,形成對自然界的依賴和崇拜。在《山海經》反映最突出的就是動物的命名。
3.“名”、“實”統一的物質觀
正如英國學者詹·喬·弗雷澤在《金枝》中說的“未開化的民族對于語言和事物不能明確區分,常以為名字和它們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間不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聯系,而是實在的物質的聯系……事實上,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作是自身極重要的部分,因而非常注意保護它。”正因為先民認為名稱是事物天然的組成部分,所以先民在為動物命名時高度尊重鳴叫聲、外形、生活習性等動物固有的物質的特征。
《山海經》作為一部最接近原始社會文明狀態的古籍,其對動物的名稱及命名依據、形態特征和功能的記錄,一定程度上還原了原始社會生活的樣貌,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幼兒時期的精神文化狀態。《山海經》除了對動物名稱進行記載外,還記載了大量地名、山水名、植物名,其命名規律和文化蘊意有待研究。
參考文獻:
[1]賈雯鶴. 《山海經》專名研究[D].四川大學,2004.
[2]袁珂譯注.山海經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趙川. 《山海經》圖騰崇拜思想[J]. 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3:18-20+24.
[5]徐非. 《山海經》神話分類及其文化意蘊探析[D].延邊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