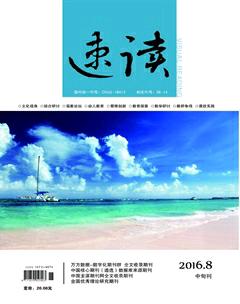批判、顛覆與束縛
摘 要:萊辛在《野草在歌唱》中真實再現了殖民統治下南部非洲的社會圖景,對白人群體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進行批判,并通過塑造黑人摩西完成了對殖民話語的顛覆。然而,作為白人殖民者后代的萊辛最終未能擺脫殖民話語的束縛。《野草在歌唱》對于殖民話語的批判、顛覆,但卻最終受制于殖民話語。
關鍵詞:批判;顛覆;束縛;野草在歌唱
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的長篇處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以一樁黑人男仆謀殺農場女主人的案件報道為開端,采用倒敘的手法重述了南部非洲白人女性瑪麗的凄涼人生。小說側重心理刻畫,在反映南部非洲“窮苦白人”潦倒的生活困境的同時,著重表現了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
由于萊辛本人女性代表作家的崇高地位以及諾獎的推動作用,萊辛的作品一直是國內文學批評界著重關注的對象。國內針對這部作品的文學批評視角多樣,涉及眾多批評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心理分析、女性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趙紀萍認為:作為反殖民書寫的典范之作,《野草在唱歌》未能超越殖民話語的限制,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與之形成共謀關系,呈現出殖民話語的隱性書寫。本文試圖從后殖民主義出發,運用文化帝國主義的相關理論,通過對黑人摩西顛覆但又保守的形象進行分析,對萊辛反殖民話語中的殖民話語進行探究。
一、萊辛對于殖民話語的批判
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提出,東方主義服務于西方的霸權統治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二元對立的表述系統使東方成為西方屬下的他者。在小說《野草在歌唱》中,萊辛通過女主人公瑪麗的視角向讀者重現了南部非洲種族隔離制度下白人與有色人種(其中尤以黑人為甚)間極端對立的社會現實。通過瑪麗的成長經歷再現了殖民話語影響下人性扭曲的過程。
作為英國殖民者的后裔,瑪麗及其父母將英國視為自己的祖國,瑪麗的父母將其他種族都視為異類。而非洲原住民則是相對其他有色人種更為惡劣、地下的種族。自幼時起,她就被母親教導要遠離原住民。彼時,“凡是在南部非洲長大的女人,從小就被叫養成這種樣子”;大人們會“悄悄地低聲用一種理所當然的聲音告訴她(她一想到這種聲音,就聯想到她的母親),原住民是怎樣地下流,會對她做出惡劣的事情來”。
種族主義思想的種子被植入了瑪麗的頭腦,但是由于當時瑪麗并未與“原住民”有很多接觸,種族和階級意識并未完全的顯露出來。種族與階級對瑪麗來說只是相當模糊的概念,以致她在第一次面對面接觸原住民時,還為迪克稱呼家里的男仆為“老畜生”而感到不快。不過,短暫的不適之后,種族主義思想在瑪麗的頭腦中隱隱顯現出來,“她有看出這只不過是一個形式問題,便竭力叫自己冷靜下來”。
在與拉斯金的談話中,萊辛曾談到:“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我們的思想是如何變化的,我們認識現實的方式是如何變化的。”萊辛筆下的瑪麗·特納也同樣經受著這樣一種思想變化的過程,殖民主義思想在她的世界觀中由幕后走向前臺。在與家中男仆、農場工人的接觸中,瑪麗思維中隱藏的殖民主義思想逐漸顯露,幼年時父母灌輸的原住民形象被強加到了她所面對的每一名原住民身上。在瑪麗的眼中,這些“他者”無一不是丑陋、狡猾而又懶惰的。據此,瑪麗對待原住民的態度極度嚴苛;面對迪克,她“幾乎帶著母性的關懷,可是他對待原住民,簡直就是個潑婦”。
瑪麗與原住民間的沖突在她接管農場上的工作時達到一個高潮。在白人農場主看來,這些原住民“不過是些野蠻人”,他們身上滿是“短處和缺陷”。白人農場主用暴力控制著農場的黑人勞工,同時試圖向這些黑人勞工灌輸白人的價值觀念。在一次面對黑人的宣講中,瑪麗手持象征著暴力的皮鞭,大肆宣揚著白人的價值觀念,她說:“白人之所以成為白人,就在于他們是以這種態度對待工作的。白人之所以要干活,只因為他們覺得干活好,因為沒有酬勞的勞動才足以證明一個人的品質。”這些深植于瑪麗意識中的論調源自于幼時她的父親對土著傭人的訓斥,她在幼時聽得夠多,“因此它們很自然地從她最早的記憶里涌現了出來”。
東方主義影響下的西方文化成為了英國殖民者鞏固自身殖民統治的幫兇,統治者向黑人宣揚白人的價值觀念,試圖以此掩蓋自身殘酷、無情的殖民掠奪的實質。小說中的白人形象無一能夠擺脫這種文化對他們的影響,種族、膚色成為了判定一個人的唯一標準。西方文化成為了與殖民主義共謀、合作的幫兇。在這套殖民話語體系下,白人對于黑人的統治、壓迫被視為是理所當然,黑人被去人格化,成為了白人統治者滿足自身利益的人力工具。小說中,瑪麗以及其他殖民者心中殘存的人性被徹底抹殺,她揮動手中的皮鞭,鞭打了不服從命令的原住民而內心卻毫無愧疚。相反,“她覺得自己好像打了一場勝仗。這一場勝仗戰勝了土人,戰勝了她自己,戰勝了她自己對土人的厭惡。”
二、萊辛對黑人形象的顛覆
然而,假如萊辛的《野草在歌唱》僅僅流于對殖民話語的批判則顯然無法支撐這部作品成為一部反殖民主義力作。《野草在歌唱》之所以能夠從眾多以殖民為主題的作品中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萊辛所創造的顛覆性的黑人摩西的形象。
黑人摩西是農場上一名黑人雇工,他的首次出場正是在瑪麗打理農場事務的時候。在繁重的勞動間,摩西用英語向瑪麗討一杯水喝,這在力圖證明自身控制力并且視英語為白人特權的瑪麗看來絕對是無法容忍的,她鞭笞了摩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摩西并未進行反擊,相反他選擇了沉默。寬容的摩西選擇了對暴行逆來順受,用沉默來對抗暴力,相比之下小說中的白人形象大多濫用武力,用暴力維護自己的威權。
其后,迪克安排摩西到家里做傭人。瑪麗試圖用惡劣的態度逼迫摩西主動離職,但摩西卻始終盡職盡責地完成了工作。他甚至會去瀏覽報紙,從宗教的視角對戰爭的合理性提出質疑,相比之下瑪麗則是一個對農場以外的生活都漠不關心的人,而小說中的其他白人男性也只對與農場相關的事務感興趣。摩西用真誠的態度,包容的心胸,善良的心性逐漸打破了瑪麗心中種族主義的藩籬。
在摩西主動提出離職時,瑪麗堅決反對,這一方面是由于擔心迪克批評她,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她對善良的摩西已經產生了依賴的情感,她已經離不開摩西了。至此瑪麗和摩西之間的關系超越了傳統的主仆關系,過去人們避而不談的白人女性與黑人男性間的曖昧關系被完完全全地擺上了臺面。此后,瑪麗和摩西的關系進一步加深了,摩西開始主動的關心瑪麗,他對瑪麗說話的語氣“仿佛是對自己同種族的女人說話”,有的時候他的“語氣很安詳,幾乎可以說很親切,很愉快,好像在逗一個孩子一樣”。)摩西和瑪麗之間的關系顛覆了殖民統治下,殖民者對白人和黑人身份、關系的嚴格界定。與此同時,瑪麗則在種族主義和摩西男性魅力的包圍下顯得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該怎樣和他相處下去”。
在瑪麗所接受的殖民主義教育中,白人和黑人始終處于對立的狀態,但是摩西的到來打破了這種穩定的關系。萊辛筆下的摩西待人寬容,為人體貼、細心,更為重要的是他的身上具備迪克所缺失的男性氣質。農場的男主人迪克固執、懦弱,自始自終懷抱著“田園牧歌”式的幻想,做事半途而廢,與農場的經營原則背道而馳。農場慘淡的經營現狀使特納夫婦的生活始終處于貧窮的陰影之下。“貧窮將他變成了‘一部沒有靈魂的機器。他們兩人的情感猶如荒漠,只有相互憐憫。”在迪克第二次生病時,瑪麗因為照料迪克而焦頭爛額,摩西主動提出為瑪麗承擔重擔;此時,瑪麗心中種族主義的高墻徹底崩塌,摩西成為了瑪麗的“保護人”,白人男主人迪克在家中的地位被黑人摩西所取代,萊辛以此完成了對殖民話語的顛覆。
三、殖民話語的束縛
萊辛在小說中通過塑造一個勤勉、善良、沉穩,同時又極具男性氣質的黑人摩西形象,并讓其取代白人男主人迪克的家庭地位而完成了對殖民話語的顛覆。以往帝國文學中野蠻、古怪、尚未開化的刻板的黑人形象被徹底打破。然而,作為西方文化傳統影響下的白人作家,萊辛在對摩西的刻畫中并未完全擺脫殖民話語的束縛。在對殖民話語進行顛覆的同時,萊辛也受到了殖民話語的束縛,無法擺脫文化帝國主義的潛在影響。
萊辛在對摩西身份建構中運用大量的西方文化要素,這在摩西登場伊始便顯露無疑。黑人摩西是特殊的,他的獨特之處最先表現在他能夠運用英語---這一殖民者的語言與農場主進行交流,而這一能力是農場上的其他黑人所通通不具備的(瑪麗在此時并不知道摩西的姓名)。在后文中,萊辛為讀者揭開了摩西的“身份之謎”:“‘他在教會當過差。他[迪克]回答說,‘我碰到過的唯一一個正派的人。”
顯然,在教堂工作的經歷使摩西成為了一名與其他黑人截然不同的人。白人為非洲這片“原始大地”帶來的基督教文明在黑人摩西身上產生了巨大影響。“摩西”這個基督教中先知的名字被安插在了這名非洲土著人的身上,而他的本名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一名黑人,摩西被賦予了其他黑人所不具有的“白人特質”,但他的獨特人格看似是其自我的真實展現,實則是西方文化影響、教化的結果。在基督教文明“洗禮”下的摩西擺脫了白人統治者所不齒的野蠻特征,在精神上向白人殖民者靠攏。他學會了用英語進行交流,閱讀報紙,進行獨立思考。他質疑戰爭,甚至逼問瑪麗:“難道耶穌認為人類互相殘殺是正當的嗎?”而這一切都是其他未受西方教化的土著黑人所做不到的。
正如《圣經·出埃及記》中先知摩西帶領被奴役的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小說中黑人摩西也試圖帶領精神上飽受折磨的瑪麗走出精神困境。小說中黑人摩西的出現拯救了極度壓抑的瑪麗,然而他所帶來的救贖毋寧說是一名黑人男性對一名白人女性的救贖,不如說是基督教文明試圖挽救一只“迷途的羔羊”。
作為一名在英國殖民文化影響下成長的作家,萊辛在批判、顛覆殖民話語的同時,最終無法抹去殖民話語施加在她身上的印記,擺脫殖民話語對她的束縛。
四、結語
在《野草在歌唱》中,萊辛以全景式的筆觸真實再現了殖民統治下南部非洲的社會圖景。萊辛將南非的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作為小說主體,通過對種族主義思想壓迫下黑人悲慘生活現狀細致入微的刻畫,塑造黑人摩西形象,以此對殖民話語進行了批判與顛覆。然而,作為西方文化傳統影響下的白人作家,萊辛在對摩西的刻畫中并未完全擺脫殖民話語的束縛。小說中摩西被賦予了溫和、善良、勤勉等其他黑人所不具有的“白人特質”。摩西的出現顛覆了以往殖民文學、后殖民文學中刻板的黑人形象。黑人摩西的獨特人格并不是是其自我的真實展現,而是是西方文化影響、教化的結果。萊辛在對殖民話語進行批評、顛覆的同時,也受到了殖民話語的束縛,從而使作品的批判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作者簡介:
李睿(1990.11~),男,湖北潛江人。云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跨文化交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