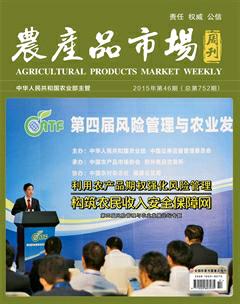來自安徽的古黟黑茶
崔建玲
您見過用茶葉做的各種器具和用茶葉建的房子嘛?聽到這個問題,估計您心里肯定有疑問,這茶葉不都是用來泡茶的嘛,怎么還能當建筑材料?
在第十三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安徽省展區,記者就見到了這一新鮮獨特的建筑方式。獨具一格的馬頭墻,馬頭翹角,墻面和馬頭高低進退錯落有致……徽派建筑風格自古就是我國建筑領域的一大流派。在農交會現場,安徽天方茶葉股份有限公司將公司生產的“古黟黑茶”,經過高溫浸泡,再通過擠壓的方式,將黑茶黏著在一起,制成一塊一塊的黑茶轉,然后用這些黑茶轉建成一座獨有特色的徽派建筑展廳。記者看到,展廳的牌子上寫著“天方茶苑”四個字,每一塊黑茶磚上,印有“古黟黑茶”的字樣。
步入天方茶苑,有一個用黑茶磚砌成的類似古代鼎的器皿,佇立在茶苑中央。安徽天方茶葉股份有限公司市場部經理李小兵告訴記者,用黑茶磚建的鼎,代表“旺” 的意思,預示著公司生意興隆。李小兵說,整個展廳的建筑和布置彰顯安徽本土的建筑風格和設計,這些建筑總共用了5000塊黑茶磚組成,整個建筑成本包括黑茶以及其他輔助材料總共花費120萬元。記者不免有些驚訝,為何花如此高價造一個只供展示的房子,李小兵說,公司主要是為了宣傳徽茶,通過農交會上展示,不僅對安徽的建筑文化有一定的宣傳作用,更重要的是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對公司生產的各種茶葉進行推廣。在現場,很多參觀者在黑茶展廳前駐足停留,有的拍照留念,有的坐下來品茶,整個展區彌漫著茶香。花費大成本制作的黑茶磚建筑,用一次不會太浪費吧?看到記者的疑惑,李小兵說,這個建筑不只利用一次,而是在參加其他展會的時候,他們也會用這些黑茶磚布置展廳。那么,這些黑茶轉在經過多年之后不能用了怎么辦?李小兵說,公司在生產黑茶轉的過程中采用環保理念,幾年后如果這些黑茶轉不能用時,便歸入農田,增加土地的肥力。
說起安徽的黑茶,其背后還有一段關于黑茶成長的故事。李小兵介紹道,古徽州的黑茶,因產于安徽,也稱為“安茶”。大約200多年前,在徽商的努力下,遠銷廣東、香港及東南亞,深受消費者歡迎。后因市場逐漸萎縮而停產。后來,安徽農業大學茶葉系教授詹羅九先生生前念念不忘古老的安茶,為圓一位已故老茶人的心愿,再現安茶輝煌,專采黟縣、祁門一帶老樅茶樹鮮葉,遵古法生產安茶,成功“復活”了安茶。黑茶具有色澤烏黑、湯色紅潤、陳而不霉的特點。
據記者了解,安徽天方茶葉股份有限公司經過18年的努力,目前開發的產品有五大系列,分別為:雪里青綠茶、祁毫紅茶、黑茶、富硒茶和慢點食品(茶食)。公司在全國擁有13家分子公司。
就像安徽天方茶葉通過用茶葉制作徽派建筑等創新方式宣傳本企業或本地區的特色農產品一樣,如今,各市場主體不惜花費高成本、花大力氣,為的就是將當地名副其實的好產品推向全國乃至國外的大市場。而對于他們來說,這些花費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