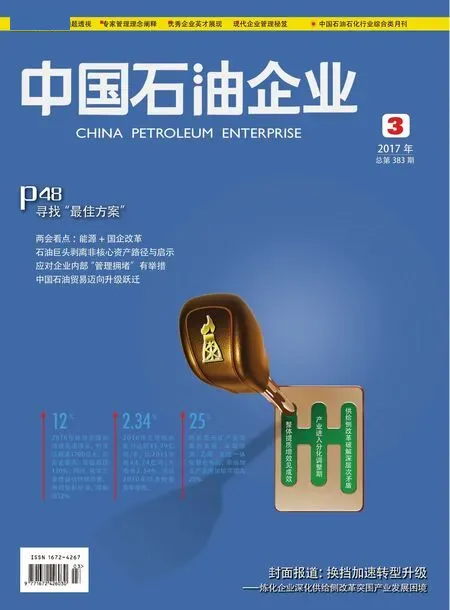中國人的詩心真的還沒有死
中國人的詩心真的還沒有死
丁酉新年伊始,中央電視臺推出《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很值得一看。剛開始我沒看到,我是在第四場比賽時偶然看到了,立刻被吸引住,便又找到回放,補齊了前三場。全部“詩詞”比賽,我覺得棒極了,真是詩絮飄飄、余味悠長。
這檔名為《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的節(jié)目,在1月29日播出后,引起全社會廣泛關(guān)注。央視數(shù)據(jù)顯示,這個節(jié)目全部10期累計收看觀眾達到11.63億人次,收視率極為可觀。他們用“久旱逢甘”贊譽這檔節(jié)目,將之稱為“綜藝節(jié)目中的一股清流”。尤其是16歲上海女孩武亦姝折桂后,這位曾在比賽現(xiàn)場脫口而出《豳風·七月》詩句的姑娘,成為了媒體的寵兒。對此,中央民族大學蒙曼教授是這樣評價她的—武亦姝不是“滿足了一切對古代才女的想象”,而是滿足了我們對女兒的一切想象。她有中國古典的女性美,女孩是蘊藉的,內(nèi)秀又不招搖,又很謙遜,很溫柔,也有女孩特有的機靈勁,我覺得她應(yīng)該是滿足人們這樣一種想象。什么叫國民閨女?國民閨女應(yīng)該是這個樣子。如果自己家有這么一個姑娘,你想想父母多開心啊!
中國古典詩詞,真的是世界范圍內(nèi)絕無僅有的一種文學樣式,同時又是我們民族從古至今“留存了下來”的代代相傳、潛移默化的文化營養(yǎng)。
為什么“留存了下來”?就是因為“詩教”一向承擔著重要作用。《禮記·經(jīng)解》引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儒家觀點認為,在詩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諸多教化方式中,詩教之于一個人品格的養(yǎng)成、心性的熏陶意義非凡。所謂“溫柔敦厚”,即不驕不躁,不溫不火,謙和厚道,儒雅大度的人格品性和思維方式。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耳熟能詳,幼兒能誦,字字簡單,音韻流轉(zhuǎn),一“曉”一“鳥”一“風雨”一“花落”,自然之雅趣,生命之意味,皆在其間。古人見花落淚,聞鳥驚心,并非哀怨矯情,而是由于心靈自在安寧,萬物于心中經(jīng)過,都可留下“人格品性”的痕跡,亦可由此感知自我。
“感知”還不就是“受教”?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白老先生把生活“打扮”成一個詩情畫意的世界,推開窗,鳥語花香,小舟蕩漾,多么讓人熱愛自然啊?!
“童叟兩無欺,相嬉享天趣。爾要做雄鷹,吾甘當雛雞。登山子引路,游船翁搖楫。輕撫黑發(fā)長,笑揪白須稀。”中國石油原黨組書記、總經(jīng)理陳耕的這首《祖孫樂》,也把生活表現(xiàn)得和工作一樣的精彩,爺爺孫子撓癢揪須、樂趣無窮,多么讓人熱愛生活啊?!我沒想到老領(lǐng)導陳耕還會寫詩,《人民日報》刊登過他的詩,還有作家在《工人日報》和《中國石油報》上撰文評論他的詩作。看了他的詩作,你就會從他的心態(tài)、品行和情操中悟出做事、做官、做人的“關(guān)系”了。前輩學者錢穆先生在論述中國古詩時曾經(jīng)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古人曾說‘詩言志’,此是說詩是講我們心里的東西的。”在這里,對于“詩言志”的“志”,錢穆先生做了最好的解釋,而不囿于傳統(tǒng)和現(xiàn)時慣用的那種宏大的指向,強調(diào)的是“心里的東西”。
誠然,我在拊掌《中國詩詞大會》的同時,也還有另外的想法:如今電視里的娛樂節(jié)目,幾乎都被搞笑的小品、相聲和娛樂化的相親、養(yǎng)身、做飯節(jié)目“占據(jù)”了。《中國詩詞大會》的出現(xiàn),讓人們在泛濫的娛樂節(jié)目中看到那一點難得的文化的影子,尤其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美麗的疏影橫斜。但這還遠遠不夠,文化復興不是要搞文化復古,不是要做古人的翻版,其詞眼在于一個“興”字。今天這個時代,“興”的意涵可以理解為“興旺”和“創(chuàng)新”,詩詞背誦當然值得做,但如果止于對背誦的贊嘆,未免失之淺薄了!
《中國詩詞大會》的確是個成功的節(jié)目。看了這個詩詞大會,看了這一個個出口成詩的新人,我高興地感覺到,中國人的詩心真的沒有死啊,它永遠活在中國這塊富有詩情畫意的大地上!